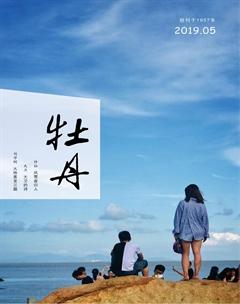絕望的個人和熱鬧的集體狂歡
胡紅英
大家守在電視機前,一邊看春晚一邊在網上吐槽節目,不過是幾年前的生活,現在已感覺過去很久。春晚亦非古已有之,人們不再都守著春晚過年,實也體現了人類生活方式的持續變化,娛樂方式的日漸多樣化,未必需理解為“年味”不再。取代春晚成為春節期間網絡最熱門話題的則是賀歲片——由關注片段化的免費晚會節目,到關注個半鐘以上情節連貫、有一定思考深度的付費電影,或許也可看作是網民娛樂生活的一種全方位升級。在2019年春節的賀歲片中,“喜劇之王”周星馳的《新喜劇之王》和號稱開啟了中國電影“科幻元年”改編自劉慈欣同名小說的科幻片《流浪地球》在網絡上引發了諸多討論。這兩部電影作為90年代以來中國賀歲片史上最經典和最新的類型片,在情節內容、價值取向上,也構成了非常有趣的彼此照映,展示了當下中國的生活方式和觀念狀況。
首先,《新喜劇之王》顯在地講述了一個陳舊的故事,或者說一個已然落后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故事——一個關于卑微的個人如何歷盡艱難終于獲得成功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關于灰姑娘如何憑借內在美贏過徒具外在美的花瓶美女的故事。這樣的故事直到20世紀終結仍然為人們熟知并相信,千百年來經口耳相傳或書寫穿梭于人們的生活,就如同古代上流社會反復聆聽為數不多的昆曲、京劇曲目,不管聽幾次,每到會心之處,一樣會喚起對應的感情。可以說,這樣一個陳舊的故事,它來源于一個繼承自前現代并為現代社會所接納的故事結構。我們可以想象,正因為現代與前現代之間分享了大量相同或類似的故事結構,社會的現代轉型完成后,才能依舊呈現出對前現代社會延續的一面。
當然,一個陳舊的故事,要在當下出場,它還需要在其陳舊的故事結構中填充今天的生活內容,使其看上去像一個今天的故事。這又如當下流行的清宮戲,它里面的價值取向、情感觀念、情節框架實際上是頗為現代的,只不過它在此現代的故事結構中填充了清朝的生活內容,而使它像一個清代的故事。我們在《新喜劇之王》中可以看到諸多當下生活的標簽式場景,如廣場舞、群眾演員、網上視頻傳播、騎電動車送外賣,等等。這是周星馳作為導演很可貴的一點,他始終在關注我們當下的生活——尤其是其中的普通大眾的生活。這與周星馳身為一個直接從生活、拍戲中學習,而非經由學院理論教育成長起來的導演身份是一致的,他不善于借助理論去結構一個架空現實生活內容的故事,而只能直接由當下現實生活中挖掘故事內容,他的不足促成了他的電影與當下生活密切關聯的特點和長處。
然而,受制于陳舊的故事結構,盡管電影情節由這些穿著當下生活外套的場景排列,《新喜劇之王》講述的仍然是一個陳舊的故事。且不說一個大齡灰姑娘的逆襲在今天已難令人相信,劇中的富二代李洋因沉迷于電影,混在群眾演員中跑龍套,并因為如夢同樣的對表演的熱愛而愛上如夢,卻被如夢拒絕,在今天也基本上是一個不可能的故事:富二代如果喜歡演戲,選擇自己投資自己當主角,請來別的著名演員演配角,才符合我們今天資本當道的現實邏輯;李洋如此癡心于一位大齡且失敗的女青年,也不符合今天富二代的情場游戲規則。而如夢,面對富二代的癡心表白,卻對她連結婚基金都要她一起攢的男朋友癡心不悔,在發覺男朋友是騙子后傷心欲絕,這般單純、被動,也屬今日熟稔大女主劇情的女青年中的異數。因此,作為90年代末期經典喜劇《喜劇之王》后續之作的《新喜劇之王》在今年春節檔票房和口碑差強人意,實際上跟它不能喚起當下大多數觀眾的共情有很大的關系。
這部電影講述的人物故事在當下顯得如此異類,以致于不能助周星馳創造又一個票房神話,但我們能夠認為電影中的人物便不存在于當下了嗎?在筆者看來,這正是這部電影的亮點所在:它講述的是一些保留了昔日情懷的人在當下絕望掙扎的故事。這樣的人,自然也包括周星馳自己。在2013年上映的《大話西游之降魔篇》中,周星馳重新采用《大話西游之大圣娶親》的主題曲《一生所愛》作為主題曲,當時已引發了一番對周星馳的懷舊情結的討論。《新喜劇之王》則讓如夢和李洋重演了《喜劇之王》中張柏芝飾演的柳飄飄和周星馳飾演的尹天仇的經典對話(尹天仇:“不上班行不行?”柳飄飄:“不上班你養我?”尹天仇:“我養你啊。”柳飄飄:“你先照顧好你自己吧,傻瓜。”)。電影上映之際,周星馳還找來張柏芝一起在電視節目中重演了那一經典畫面。無論是“一生所愛”還是“我養你”,在今天看來都格外深情。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導演有意借助昔日的經典橋段喚起觀眾的懷舊心理,從而獲得又一次的票房成功。但是,周星馳在電影故事之外表現出的懷舊式深情,與《新喜劇之王》中李洋對如夢、如夢對查理的感情明顯是一致的。如夢和李洋執迷于表演本身的演員之夢,在今天看來,也顯得過分地純粹和理想主義。當這樣的深情、純粹和理想主義集結于今天某個人物的身上,他/她會有怎樣的現實遭遇呢?可以說,周星馳通過《新喜劇之王》中的如夢和與她類似的小人物的掙扎,進行了一次很現實主義的寫照,電影最后讓如夢暴得大名,不過就像魯迅先生在革命者墳頭上加上一圈白花致敬罷了,畢竟對于此般個體絕望和掙扎是必然的,終于能夠熬出頭卻非所有人物都能企及的命運——甚至連周星馳本人,都無法通過這樣的人物故事在今年春節檔為自己創造又一個票房神話。
相對于《新喜劇之王》某種程度的遇冷,《流浪地球》則是今年春節檔絕對的票房贏家,并且得到了諸多網民的追捧——因對豆瓣網友給《流浪地球》的打分不滿意,《流浪地球》的粉絲甚至開展了對豆瓣APP打一星的抗議之舉——事實上,豆瓣給《流浪地球》的打分,遠高于《新喜劇之王》,但為《新喜劇之王》辯護的網民以個人為單位,且數量甚微。顯而易見,接近五十億票房的《流浪地球》為人們帶來了一次線上(網絡)線下(觀影)的集體狂歡。有趣的是,與《流浪地球》作為一個熱點事件為人們帶來熱鬧的集體狂歡相對應,電影也正好講述了一個關于人們如何一起面對共同的災難的故事——以一個共同的災難之名,把個體逐個征集,進而打破國家界限,集體面對同一的人類困境。在這部電影中,理想是集體的理想,個人是集體中的個人,個人和外界之間的壁壘取消了,只要放棄對狹隘的自我的執迷,個人就能融入到外界的共同目標之中,分享共同的理想和激情。我們也可看到,在《流浪地球》中,分享了共同的戰勝災難的理想主義激情的人物,其精神面貌與《新喜劇之王》中的人物截然不同,他們堅定而又不畏懼犧牲,偉岸而又不失溫情,充滿了浩然正氣。
除了共同的戰勝災難的理想和激情,《流浪地球》中花了較大氣力渲染的是家庭成員間的濃厚親情。家庭亦可謂一個小集體,電影中的主要人物也是由吳京飾演的劉培強一家擔綱,這個家庭的成員,在電影中同樣分擔和分享了他們家庭內部共有的苦難和溫情。也即是說,電影的主要人物,在電影中首先是一個家庭中的成員,他們是帶著保護家庭成員的情感沖動去融入到外界共同的拯救地球的理想行動之中。因此,《流浪地球》中實際上并不存在脫離了某個現實共同體的個體,他們首先是作為家庭成員的個體,其次是作為拯救地球的人類的一份子,片中疏離于集體較為強調個人利益的人物——如混血兒Tim,在電影中構成為被嘲諷和揶揄的對象,最終也只能通過融入共同的拯救行動中完成華麗轉身。
從《流浪地球》作為春節檔票房和口碑雙贏家的地位,我們大概可以窺見,這部電影中的價值觀念和情感邏輯是更為當今的大眾所認可的,它喚起了更為普遍的共情。它以人類的共同災難為名,展現了一種基于集體主義的理想主義,從而也使諸多網民自發構成一個為之吶喊、助威的粉絲團體,在電影之外分享其中的集體式的熱鬧和激情。《流浪地球》作為一部本以浩大的場面為主要表現對象的科幻題材片,這樣的集體狂歡式熱鬧倒也與之相稱。此外,它大概也借重了近些年中國社會對婚姻、家庭問題的重視——從江蘇衛視2010年推出《非誠勿擾》相親節目始,“相親”由一個有點曖昧和尷尬的詞匯,甚或已成為當下人們日常生活中最常脫口而出的詞匯之一,而由相親及親子、夫妻檔綜藝節目,個人不管此前具有如何多樣的身份于其間實際上完成了一次角色的重新設定——個人是婚姻中的個人、是家庭中的個人,它甚而成為當下社會人們最看重的身份。對家庭的重視乃中國傳統風習,但《流浪地球》中的情感邏輯和價值觀念能夠獲得廣泛而無條件的認同,不能不說還是依仗了當下社會某種程度上經由種種綜藝節目所建構的對婚姻、家庭問題的看重。
誠然,《流浪地球》中的故事實際上也不出20世紀經典的英雄故事框架,它在今天再次喚起人們的普遍共情,表明了集體主義的號召力并無全然由資本邏輯消彌,而與20世紀初及中葉以疏離于家庭情感喚起英雄主義激情不同,這次它反而是借重了家庭情感積蓄的能量。由《流浪地球》所揭開的這一層時代面紗,再來看《新喜劇之王》不討好,其中因由似乎便不那么令人費解了。不難發現,《新喜劇之王》的主人公如夢的個性特征,與《流浪地球》中的人物的個性特征,正好恰恰相反——如夢最突出的個性,無疑是對父母構成的家庭生活的疏離,懷抱著一種源于自身熱愛的理想主義激情,欲求抵達個人的夢想生活,而《流浪地球》的主人公則高度看重家庭情感,將自己的意義和價值全然歸屬于家庭,進而帶著這份對家庭的愛獻身于拯救地球的集體理想之中。這么恰好相反的個性,這么恰好相反的觀眾認同度,不能不使人認為,《新喜劇之王》中主人公所背負的那一份疏離于家庭的個體的理想主義激情,在當下不太能獲得大眾的共鳴,正是它不討好的根本原因;電影的處境所展示的這一份個人主義理想激情在當下觀眾中的不討好,卻也正好暗示了劇中如夢們所面對的時代生活,以及他們何以在當下只能以一種絕望的姿態朝向理想奮斗——畢竟在20世紀初,疏離家庭情感、離家出走追求個人理想的青年,也一度擁有斗志昂揚的姿態。
可見,《新喜劇之王》和《流浪地球》在春節檔的討好與不討好,事實上受制于其通過情節內容所展示的價值立場與當下的時代生活之間的關聯性。兩部電影的不同境遇和其所展示的價值觀念告訴我們,在家庭已成為普遍認同的生存倚賴的今天,個體的理想主義是不那么討好的,其理想激情促使個人生活處于絕望的掙扎狀態,透露了個體精神和主體性在當下的處境;相比之下,當個人將自己視為家庭中的成員,將個人的意義和價值歸屬于家庭和集體,則可在分享家庭、集體的能量和激情中,更樂觀、堅定地展現自身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