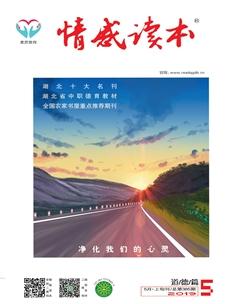一個人心里的巨流河
小艾
張大飛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曇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綻放;迅速闔上,落地。那般燦爛潔凈,那般無以言說的高貴。
山的隘口,他回頭看她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迅速占領了東三省,北平、天津到處都是流亡的東北學生,16歲的張大飛也在其中。極端困頓中,在報國寺附近游蕩的他看到國立中山中學招生的布告,便報了名。
齊邦媛的父親是國立中山中學創始人,她的家成了東北學生共同的家。張大飛也來了,他父親曾是沈陽縣警察局長,因接濟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澆汽油燒死,一家人四散逃亡。
那天,在溫暖的火爐邊,齊邦媛看到18歲的張大飛用自尊忍住號啕,敘述家破人亡的故事。那一幕,12歲的她終身難忘。此后,每個星期六,她都期盼著他那憂郁溫和的笑容。
一次,大家一起去爬山。下山時,體弱多病的齊邦媛落在最后,天已經暗了,山風吹著尖銳的哨音,寒冷和恐懼中,她開始哭泣。這時,她看到張大飛在山的隘口回頭看她。他返回來,用棉大衣裹住她,把她牽下山。
齊邦媛的父母給了張大飛久違的家庭溫暖,他稱他們“爸爸媽媽”。可不久,蘆溝橋的戰火就隔斷了小屋里的緣分,張大飛報名上軍校,改名“大飛”。臨行,他送給齊邦媛一本《圣經》,扉頁上,他題了詞:“……祝福你那可愛的前途光明,使你永遠活在快樂的園里。”從那天起,她走到哪里,這本書就跟到哪里。
山河破碎,齊邦媛隨中山中學一起轉移。在湖南湘鄉落腳時,她收到張大飛的信,他已考入空軍官校,時刻準備報效國家。1938年,顛沛流離一年后,中山中學到達四川,齊邦媛進入南開中學。家人一直聯系不上,張大飛給她寫信如寫家書,感動之余,她每信必復。
畢業后,他已經駕駛驅逐機了,還參加了重慶上空的保衛戰。一個在云端身經百戰,一個在學校埋首讀書,他們誠摯、純潔地分享成長經驗。她給他抄課本上的憂國文章,也有“多情得要命”的散文詩。他說,她的信是“他唯一的家書,最大的安慰”。
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
因為表現出色,張大飛被派往美國,一年后,回國加入了陳納德的“飛虎隊”,與美國志愿軍并肩作戰。去云南報到前,他來看齊邦媛。坐在寂靜無人的嘉陵江岸,他們暢談許久,沒有一句關乎情愛。“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英雄,是我那樣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褻瀆的巨大形象'。”
張大飛走后,她開始惦念他,從報紙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隊幾乎每戰必勝,她為他驕傲。通信仍在繼續,上高中后,沉浸在詩詞中的她給他抄詩、詞,選課本,他幾乎和她同步修完孟志蓀老師的課。他說這是他“靈魂又一重安慰”。
齊邦媛高中畢業前夕,張大飛趁著部隊在重慶換機趕去看她。一起走在操場上,他突然站定,說:“你怎么一年就長這么大,這么好看了呢。”第一次聽到他的贊美,她心潮起伏。戰友的吉普車還等在校門口,她送他往外走,驟雨突然落下,他拉她到屋檐下,把她裹進他的軍用雨衣里。隔著軍裝,她聽到他心跳如鼓。只片刻,他松手說:“我必須走了。”
不久,齊邦媛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前往樂山。踏進女生宿舍報到時,門房取出一封信說:“人還沒來,信就先到。”淺藍色的航空信寄自云南蒙自,他惦念她獨自去學校的路程,不言相思,卻盡是相思。“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訊處,等你到了樂山來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每個星期,他的信都會來,傾吐思念:“我無法飛到大佛腳下三江交匯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愛你,多么想你!”
她也想念他。她關心戰報,在地圖上追蹤他的腳步。她想轉去西南聯大外文系,因為他在昆明。然而,他的態度卻突然變了,在信中不再說感情的話,只說“所有學習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斷”。他受傷了,對死亡有了近距離的認識。理智告訴他,這些年來他們走著完全不同的路,他升空作戰關注生死存亡,而她在詩書之間走向光明,他不能害了她。
暑假回家后,齊邦媛收到張大飛的信,口氣是兄長式的,堅決不贊成她轉學昆明,“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戰爭勝利”。
他的飛機,撞上了月亮
因為英文聯考全校第一,在朱光潛勸告下,齊邦媛轉入武漢大學外文系。全神貫注在雪萊的詩中,齊邦媛幾乎忘記了戰爭的威脅,《哀歌》中的“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陰”是她苦悶心情的共鳴。她為情所困。
可張大飛的信許久沒來了。1945年6月,齊邦媛收到哥哥齊振一的信。信里,哥哥附了張大飛的信:“振一:你收到此信時,我已經死了。感謝你這些年來給我的友誼,也請你原諒我對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請你委婉勸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回到重慶的家,書桌上,放著一個深綠色的軍郵袋,里面是八年來她寫給他的所有信件。在抗戰的歷程中,兩個在戰火中摸索成長的心靈,“一個找到了戰斗救國的槍座,一個找到了文學的航路”。郵包里,有一封筆跡陌生的信:“張大飛隊長已于5月18日在河南上空殉職。這一包信,他移防時都隨身帶著,兩個月前他交給我,說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來,請我按這個地址寄給你。”
信封中,還附有一封紙張褪色、折了多次的汗漬斑斑的信,那是她高二時寫給他的,是封純粹的文藝青年的信:“你說那天夜里回航,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飛機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
他真的撞上了月亮,留給她無盡的痛苦。她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他和一位中學老師結婚了,“我很為他高興,在他為國捐軀之前享受了短暫的家庭溫暖。”
1945年8月,張大飛殉國三個月后,日本投降。淚水中,齊邦媛想起惠特曼的詩《啊,船長!我的船長!》:“啊,船長!我的船長!可怕的航程已抵達終點……可是,啊,痛心!鮮紅的血滴落,我的船長在甲板上躺下,冰冷并且死亡。”
她把他深埋心底:“他不是我的兄長,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鐘情卻從未傾訴。想到他,除了一種超越個人的對戰死者的追悼,我心中還有無法言說的復雜沉痛與虧欠,談到他的任何輕佻語言都是一種褻瀆。”
抗戰勝利后,父親回到南京工作,暑假齊邦媛去了南京。雨中,她一個人走在街頭尋找舊居,走到一個街口時,突然看到一條布帶橫掛在一座禮拜堂前,上面寫著大字:紀念張大飛殉國周年。“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劍刺入我的眼,進入我的心,是他引領我來此禮拜,在上帝的圣堂見證他的存在和死亡嗎?”
1947年,齊邦媛去了臺灣,走上教育路途,為著他所祝福的“可愛的前途光明”,她兩度赴美進修,不僅將西方文學引介到臺灣,還將臺灣文學推介至西方世界,被稱為“臺灣文學的守護天使”。
1993年,已是著名學者的齊邦媛回來了。在南京,她去了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謝絕了老同學的陪同,獨自找到那塊編號M的碑。碑上刻著二十個名字,其中一欄寫著:“張大飛上尉,遼寧營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職。”
81歲時,齊邦媛撰寫《巨流河》,歷時四年,完成了這部史詩般的自傳。她和張大飛的故事感動了無數讀者,有導演想將其拍成電影,被她婉拒,她不愿“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為一部熱鬧的電影”。
“張大飛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曇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綻放;迅速闔上,落地。那般燦爛潔凈,那般無以言說的高貴。”漫長的一生,她時時感受到他的祝福。如今,她實現了他所期盼的“可愛的前途光明”,他的靈魂,足以欣慰。
李明摘自《莫愁·智慧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