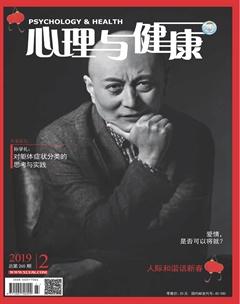“不存在”之人
邱天
假如人們眼中所見都被記錄在案——最近在美國上映的小成本科幻電影《匿名者》就幻想了這樣的未來。在這個奧威爾式的未來中,每個人一出生就戴上了視覺信息收集裝置“心靈之眼”。它幫助人們即時地讀取包括廣告、身份等在內的各種信息,使得行人一覽無余;同時也將每個人的所見記錄儲存在云端數據庫中,當政府部門有需要時可以隨時調用。然而警察歐文在追查連環殺人案時發現了一名危及整個系統的“匿名者”,此人黑客技術高超,抹消了所有個人信息,也抹消了被他人目擊的記錄。這名“不存在”之人來無影去無蹤,讓歐文大吃苦頭。隨著案情發展,歐文逐漸了解了“匿名者”,警察與嫌犯間產生了暖昧的引力,他的內心也愈發糾結于世界和自我。最終,歐文查出了真兇,但“匿名者”依然拒絕生活于世界的視線之下,離開歐文消失于虛空。
這部影片通過“匿名者”的法外之徒形象,傳遞出一個終極的問題:存在,究竟應該如何定義?乍看之下,“匿名者”從全世界的記憶影像中消失,沒有一個人能夠留下她的數據,沒有一個人能夠重復地觀察和確認她。從大眾的角度來看,完全可以斷言“此人并不存在。”那么,“匿名者”為什么要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呢?也許她會這樣回答:盡管在人們眼中我不存在,我仍然可以發現自己,可以認識自己,可以不為他人的眼睛而活著。存在主義告訴我們,恐懼來源于發現自己誰也不是,內在一無所有。那么,真正的存在,在于自我意義的再發現和再創造。由此觀之,“匿名者”真真切切地存在著。她做出了選擇,創造著自己;逃離了外在世界的尖銳目光,進而走向內部的自我。
也許你會質疑,這樣的選擇是否充滿了孤獨色彩。孤獨感是人類生活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當我們認識到除了自我的肯定之外,無法依賴任何他人,孤獨感就產生了。但也正因如此,我們通過審視自己的內心,感知分離,從而獲得力量。賦予生活意義,決定生活方式的人,必須是我們自己。在影片中,“匿名者”除了和雇主偶爾的接觸,幾乎沒有人際交流。她想必也是孤獨的,但卻并未因此感到恐慌。她有著強大的自我認同感,承擔著存在的勇氣,決定自己的生活。正是這種孤獨中的勇氣,做出背離外界選擇的力量,深深地吸引了作為外界監視者的警察歐文,讓他背叛了自己的職業,去探索“匿名者”的內心,甚至去愛上她。
人本主義療法大師羅杰斯提醒,我們被“有價值的條件”束縛著,這正是困擾人們的核心因素之一。人們根據自己的行為標準來決定是否給予某個個體關懷與尊重,此時這種標準就成為了“有價值的條件”,使得個體漸漸放棄自我的內部評估,被迫以外在的價值規范去決定自己。而那些從童年起就感受到的視線,對于“匿名者”來說不正如同繁多的價值條件嗎?因此,她選擇了斬斷它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有些類似現實中心理咨詢師的行動:他們提供給來訪者無條件的積極關注,不論何時都溫暖地尊重與接納,同樣讓來訪者不再被“有價值的條件”所束縛,成為真實的自己。擺脫了“偽裝”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任自己,對經驗保持開放,繼續自我內在的成長。
但從心理學的角度質疑,“匿名者”的所為皆是具有適應性的嗎?人類終究是社會性動物,人際關系,社會交流幾乎不可避免。我們總是希望能夠在他人心中占據重要地位。不論“匿名者”的決定是多么富有勇氣,她終究未曾正視過這種社會性需求,而是選擇了回避。哪怕與警察歐文心靈相通,也放棄了更進一步的機會,最終消失于歐文的視線中,繼續著置身“世外”的生活。這正是咨詢師與“匿名者”的區別所在:心理咨詢的目的是幫助我們更好地生活,建立積極的人際關系,引導我們自我實現。相對地,“匿名者”完全把自己隔離于世界之外,拒絕建立任何長久的人際關系。雖然這不失為一種選擇,卻是殘酷的選擇,甚至背離了人類的本性。我們可以贊賞她做出選擇的堅定意志,贊賞她從孤獨中汲取的力量,但不會如此簡單粗暴地放棄一切關系,放棄世界所有交流的嘗試。現實中的我們努力存在著,以一種含有更多摩擦與痛苦,同時也是更加溫暖和有張力的方式。站在“匿名者”的對立面,警察歐文在執行暴力機器任務和探索自我情感中間不斷搖擺,不斷嘗試。也許我們更像歐文,盡管對無孔不入的監視機制頗有微詞,盡管糾纏于人際關系的漩渦中,但卻拼命證明自己的意義,讓真相終于大白。我們不能簡單地定義誰的存在更有意義,不過歐文走向了一條更有建設性的道路,跨過了內心的障礙。
“生活和電影的差別有時很小,行走于世,處處避不開他人的審視目光。我們卻不可能像“匿名者”一樣來一場社會性的逃亡,也不愿意把自己隔離成一座孤島。生活的選擇權畢竟在手,能夠治療、改變自己的人,只能是自己。生活的意義是“投入,的副產品,投入則是我們愿意去創造、去努力、去愛的承諾。當你愿意去投入,保就不會是“不存在”之人,也許這就是問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