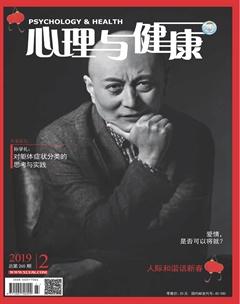我的驚恐障礙又復發了嗎?
庖丁
兩年前,姍姍在一次早高峰坐地鐵時突然感到呼吸困難、極度心慌、眩暈伴隨瀕死感。此后她不敢再坐地鐵,即使不坐地鐵也會時不時地感到頭暈、心慌、呼吸困難,甚至出門都要有人陪伴,生怕自己出現“意外”得不到救治而死掉。后來,在精神心理科,醫生給她診斷為“驚恐障礙”(焦慮癥的一種,是一類急性嚴重焦慮發作,病人在發作時常有明顯的心血管和呼吸系統癥狀,如心悸、胸悶、氣急等嚴重者可有瀕死體驗或擔心失控、發瘋或死掉等)。經過藥物治療,姍姍的病情逐漸有所恢復。但為了不讓自己出現焦慮的情緒和身體反應,她遠離了很多曾經帶給她樂趣與便捷的生活方式。
一次公司開會,會場安排在了一個昏暗叉密閉的禮堂里。會議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時候,姍姍開始感到胸悶、呼吸困難,還有點眩暈。這讓姍姍想起第一次出現急性焦慮發作的情形,“不會是焦慮癥復發了吧?”她很緊張,趕緊拉住了坐在她身邊的好友小溫的胳膊,湊到她耳邊低聲說:“我很憋悶,想出去。”小溫心領神會,隨即拉著姍姍出了禮堂。
出了禮堂,—接觸清涼的空氣,姍姍感覺呼吸順暢了許多。倒是小溫,拉著姍姍的胳膊,大口地喘著氣說:“謝天謝地總算出來了。”
姍姍很吃驚:“你怎么也會覺得呼吸困難昵?”
“廢話,那么多人……在一個……黑洞洞的屋子里啊……叉熱叉不通風……怎么可能……呼吸順暢!”小溫邊大口喘氣,邊回答著“況且……我今天還沒吃早飯昵,這都要中午了,我都快暈了!”
看著小溫夸張的樣子,姍姍感到好笑,也忘了自己的胸悶眩暈了,便打趣地說:“你這是得了焦慮癥了吧?”
“焦慮癥?要是今天我這個樣子被您老人家診斷為焦慮癥,我已經不知道得了幾百回焦慮癥了!人生在世,誰沒點焦慮啊,真是的!”
姍姍一愣,她對于自己剛才的胸悶、呼吸困難、眩暈到底是正常的反應,還是焦慮癥復發了也感到疑惑了。
要是在以往,姍姍準會把醫生給開的“急救丸”掏出來含在嘴里。這次,姍姍掏出了藥丸,卻攥在手里,遲遲沒有放進嘴里。
“喂,你盯著我看什么昵?”小溫看姍姍發愣,問道。
“哦,我是在想,我剛才是不是焦慮癥發作了。”姍姍回答到。
“你就別犯神經了,這么悶的會場,不感到憋氣才怪。我都沒覺得自己得焦慮癥,你這么淡定,怎么可能是焦慮癥?”小溫不屑地說。
姍姍仔細感受了一下,自己似乎隱約有些憋氣,但比在會場那會好多了。姍姍還是有些疑惑,自己到底是不是焦慮癥復發了昵?
其實,焦慮是人類正常的情緒反應之一,表現為內心的緊張不安、預感似乎要發生某種不幸而又難于應付的不愉快情緒體驗。在環境變化的情況下,適度的焦慮可以充分調動機體功能,提高大腦的反應速度和警覺性,具有積極的意義。而病理性焦慮,即焦慮癥的焦慮則不那么積極了。那么,如何區分正常的焦慮和病理性焦慮呢?可以簡單地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甄別:
1 正常的焦慮是有原因的,而病理性焦慮則是沒有現實基礎或者與現實威脅明顯不相稱的;
2 正常的焦慮可以隨客觀問題的解決而消失,病理性焦慮則不會;
3 正常的焦慮反應有其發生、發展、高潮、消失的過程,而病理性焦慮則持續存在。
對于姍姍來說,因為診斷過焦慮癥,她稍有不舒服就往焦慮癥上想,而對癥狀的關注可能會放大不舒服。其實,這些不舒服也可能是對環境的正常反應。這次,姍姍和小溫同時感到呼吸困難、憋悶,其實都是因為會場空氣流動性差所致,離開會場后,兩個人的癥狀有所減輕,并不是焦慮癥的焦慮反應。能夠區分正常的焦慮反應和焦慮癥的癥狀,對于恢復期的患者來說至關重要。
后來,姍姍咨詢了醫生,并在醫生的建議下開始挑戰自己,慢慢地又成了擠地鐵人流中的一員,電影院中也有了她的歡笑。
“對于像姍姍這樣的驚恐障礙患者來說,藥物治療合并心理治療是許多國家的防治指南推薦的治療方案。藥物治療可以緩解驚恐發作的概率和發作的嚴重程度,也可以降低患者的預期性焦慮、恐懼性回避等癥狀;而以認知行為治療為代表的心理治療則能改變患者的歪曲認知,降低焦慮的情緒和軀體反應,減少回避行為,且能有效降低復發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