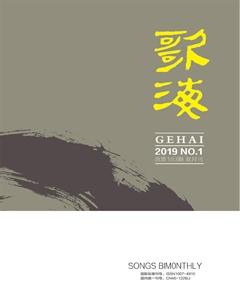現代壯劇的本體意識與審美追求
楊智 譚銀
[摘 要]21世紀以來,戲曲現代戲勢頭正勁,從現代戲角度考察戲曲現代化進程很有必要。作為地方戲曲劇種,壯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廣西戲曲,其發展在中國戲曲現代化進程中有其重要地位。以現代壯劇《我家住在銅鼓嶺》為例,從題材選擇、主題開掘和表現形式等方面來審視壯劇現代化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現代壯劇;現代戲;人的戲劇;本體意識
戲曲現代戲是指用于表現辛亥革命以后延續至今的現實生活題材的戲曲作品①,它的創作與戲曲改革緊密聯系,早在晚清“戲曲改良”就已初現端倪。但無論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用以表現民族危難、鼓舞國家救亡的時政戲劇,還是以梅蘭芳為代表的京劇時裝新戲,在晚清“戲曲改良”之后均以失敗告終。直至建國之后,戲劇界迎來生機并掀起關于戲曲現代戲的創作熱潮,傳統戲曲向現代戲曲邁進才跨入實質性的一大步;及至1958年后,以“現代劇目為綱”取代“兩條腿走路”,更是將戲曲現代戲推向一種新的創作高度與氛圍。這期間,出現了《朝陽溝》《劉巧兒》《小女婿》《祥林嫂》等一大批藝術堪與傳統戲曲媲美的戲曲現代戲。即便如此,有關戲曲現代戲與傳統戲曲分清仲伯、孰是孰非等藝術論爭一直未曾間斷。1950年代一度流行的觀點認為,戲曲特別是京劇和昆曲等能代表全國性戲曲的劇種,不適宜表現現代生活,原因是戲曲“唱、念、做、打”等藝術表現形式與反映現代生活之間存在難以解決的矛盾。這其中,梅蘭芳的“移步不換形”觀點在一定程度能代表當時老一輩戲曲工作者創作的普遍心態。但阿甲等人對此類觀點從理論層面進行了反駁,這種“反駁”到新時期乃至新世紀愈益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論證了其可行性與充分合理性。早在1988年,張庚先生在第六屆戲曲現代戲研究年會上曾提出了“現代戲已經成熟”的論斷②。這種“成熟論”觀點在第十屆廣西戲劇大型劇目展演上,再一次為現代壯劇《我家住在銅鼓嶺》所論證。不僅如此,現代壯劇《我家住在銅鼓嶺》的上演,還為壯劇發展及其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提供了可能。
一、寫真實:現代壯劇題材創作的風向標
壯劇作為廣西少數民族戲劇劇種之一,主要有北路壯劇、南路壯劇和壯師劇等類別。壯劇在其形成之時起,長期被稱為“土戲”,直至建國后才更名為壯劇。壯劇的傳統劇目比較豐富,取材范圍廣泛。這其中,有號稱十八大本的連臺戲本,如《三國演義》《說唐》《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飛龍傳》等;有取材于民間唱本的劇目,包括《柳蔭記》《八仙圖》《鸚鵡記》《杜十娘》《秦香蓮》等;還有一些生活故事小戲,如《錯配鴛鴦》《雙采蓮》《賣花嫁女》《寶花盒》等。新中國成立以后,壯劇藝術的發展步入了新的時期,劇本創作也呈現新的審美取向,在收集、整理傳統劇目的同時,出現了一些取材于民間故事和民間傳說的作品,如《寶葫蘆》《紅銅鼓》《百鳥衣》等。此外,一些壯劇現代戲也相繼編創。1958年的《水輪泵之歌》《大路上》,1970年代的《紅嶺壯歌》《雨后青山》,即屬于此類。但從整體來看,與戲曲現代戲相比,壯劇中的新編歷史劇和傳統戲在數量和質量上更勝一籌,這其中就包括近年來編創的《馮子材》《瓦氏夫人》《百鳥衣》《趕山》等新編歷史壯劇。
但是,壯劇現代戲自建國后一直備受矚目。這其中,除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因時代需要編創了一些應時之作外,新時期以來影響較大的有1982年由德保縣文藝隊演出的南路壯劇《種瓜得瓜》,1986年在第二屆廣西戲劇展上出現的由梅帥元編寫的《羽人夢》和2009年獲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重點資助劇目的《天上的戀曲》等劇目。《種瓜得瓜》主要反映的是青年馬家漢如何在王秋蘭的感召下,由“懶”向“勤”的轉變,同時也抨擊了極“左”路線對人性的扭曲。潘健是這樣評價這部壯劇的,“盡管描寫由懶變勤、由窮變富以及光棍成親的作品不斷涌現,但由于《種瓜得瓜》在人物刻畫、情節處理、語言提煉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點,所以它的藝術個性還是比較鮮明的,能給人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①。也就是說這部劇能夠從社會現實問題出發,寫出真實的現狀,帶有“問題”劇色彩,但也因為它反映的社會問題具有歷時性,所以當社會熱點一過,劇作也隨之沉寂。相比之下,改編自梅帥元小說《黑水河》的《羽人夢》,講述的是住在紅水河邊的寡婦滿妹面對再嫁等問題的思考與抉擇。寡婦再嫁等問題在當時也是一個普通創作題材,內容算不上新穎,但編導者卻以全新的觀念去處理一個傳統的倫理題材,同時擺脫人物形象以簡單化、類型化創作模式,從而賦予該劇以嶄新的現代意識與創作理念。如果說《羽人夢》注重的是從藝術表現形式上拓寬壯劇藝術的審美范疇的話,那么《天上的戀曲》則刻意表現弱勢群體生存和情感溝通之艱難,在“對健全生命的傾慕與渴望”②的同時,立足于人性關照與人文關懷,在一定程度上將壯劇現代戲朝著“立人”戲劇推進。
第十屆廣西戲劇展演大型劇目展演推出的現代壯劇《我家住在銅鼓嶺》,是廣西戲劇院新近推出的現實題材壯劇。它取材于新農村建設這一題材,反映的是廣西60年來農村發生的變化。這部戲思考的不只是貧困地區如何脫貧的問題,更是思考了如何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前提下,走進新時代、追求新生活的問題。與《我家住在銅鼓嶺》同時現身本次劇展的還有另外四部壯劇,新編歷史劇《百色起義》、傳統戲《牽云崖》和《瑤娘》,以及同樣是現代戲的《天夢》,其中《百色起義》和《牽云崖》也是由廣西戲劇院打造。一次戲劇展演有如此多的壯劇作品推出,也反映出壯劇在新世紀愈益得到重視,其獨特的藝術魅力也愈益得到認可。《我家住在銅鼓嶺》屬于時政題材的戲曲現代戲,這在新時期以來編創的壯劇中鮮有體現。究其因有二:一是既往壯劇在表現民間故事、神話傳說方面有其天然的優勢,但在表現現代生活方面存在困難;二是緊跟時政的戲劇常常因為劇作家不熟悉生活、不了解政策,同時也因為題材的想象空間受限,導致很多作品只顧一味圖解政策而流于表面。于是,在創作過程中,編劇者常常避重就輕,選擇熟悉的題材或者有較大想象空間的題材,傳統戲和新編歷史劇自然受到青睞。當然這種選擇也無不反映現代戲創編困境背后的特殊原因,即“目前所謂對現代戲創作的提倡,其真正的意思并不是一般地提倡創作現代戲,不是要劇作家們調動一切藝術手段以表達自己身處現代社會生活中的真實感受,而是在提倡某一種現代戲——即為現代歷史進程謳歌的劇目”①。這段話所要表達的并非反對現代戲,而是反對不尊重現實,不注重真實感受,一味圖解政策,只顧說教的現代戲。這種現象,在既往戲曲現代戲創作中不乏其例,壯劇也概莫能外。
相比較而言,《我家住在銅鼓嶺》則能夠深入現代生活,寫出了真實的社會人生。劇中的田桂花前往銅鼓嶺扶貧有其現實依據,她這一行為是對我國當下扶貧政策逐步得到落實并進而不斷得以推廣的一個側面反映。脫貧攻堅是我國實現小康社會的一項舉措,也是我國新農村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出現符合社會的發展規律,同時也符合人民的生活需求,但如何用戲劇的形式來寫好這一時政題材,則十分考驗編劇者的水平。《我家住在銅鼓嶺》以田桂花回鄉扶貧為主線,寫出基層干部在實際扶貧過程中的做法、遇到的困難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作為鄉文化站代副站長,田桂花同樣也需要被“扶貧”,在接到上級派發的指令時,她也出現“落后”的拒絕行為,但出于對自己故鄉的眷戀,田桂花逐漸從情感上接受了扶貧任務并以高度的熱情投身其中。劇作不僅寫出扶貧工作的任務艱巨和困難所在,如村民不配合扶貧工作、拒絕拆遷等;同時也寫出扶貧干部在工作方法上存在的問題,如蘭三的好大喜功、強硬拆遷,莫鄉長的脫離實際、違背客觀事實等。這些情節都源自于現實生活,是對現實生活中的矛盾沖突的真實反映。具體說來,田桂花要完成銅鼓嶺的扶貧工作,必然需要解決該地的三大困難,即“干群矛盾多,老少光棍多,迷信活動多”,這三大困難也構成了劇作發展的基本脈絡,全劇基本上圍繞遇難、解難展開,一環扣一環,故事情節真實可信。劇作結尾雖是大團圓結局,但觀眾并未有太多感覺生硬之嫌,其原因除了因為扶貧工作本身可圈可點外,還在于劇作中矛盾沖突的解決。這種“矛盾沖突的解決”不是依靠借助外力如上級的指示來收尾,也不是通過回避矛盾沖突來緩和,它的關鍵在于深入理解時事政策的精神要義,并結合扶貧對象的具體問題,實事求是地進行思考,提出具體解決問題方案且為現實證實其可能性,因而結局才具有可信性。這種“真實”不是劇情表面的真實,而是深入現實生活的真實;該劇也不是表層的解讀政策,而是抓住了政策的本質內核,從而既能保持劇作的形象生動而不造作,又能讓時政宣傳令人信服且得到臺下觀眾的普遍認可。這種“認可”是建立在“是否具有時代特點的社會背景和環境,矛盾沖突的展開是否有著當代社會意義以及具備人物形象的內在豐富性”②的基礎上。它實際上體現出戲劇創作的一種新的“境界”,它可以解決現代壯劇乃至廣西其他少數民族戲曲劇種都會遇到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戲曲現代戲如何贏得觀眾及走出演出市場困惑,如何創新與發展。
二、寫人的真實:現代壯劇主題開掘的不二圭臬
戲曲現代戲作為戲曲的眾多題材之一,與現代戲曲屬于既相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概念。具體到戲劇創作,二者在發展過程中同樣面臨現代化的問題。因為戲曲現代戲的特殊地位,它對于實現中國戲曲現代化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在一定程度可謂戲曲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是“檢驗戲曲現代化成敗的試金石”③。《我家住在銅鼓嶺》在這方面作了有益嘗試,是一部既有“戲曲現代戲”創作特征又具“現代戲曲”精神內核的成功劇作。所謂現代戲曲,呂效平在《論“現代戲曲”》中指出,“現代戲曲,就其文體形式而言, 是中國戲曲與歐洲傳統戲劇情節樣式的結合”④。之后,他又在《再論“現代戲曲”》中明確提出,“現代戲曲”的精神本質是“人”的發現與解放,是創作的精神自由的狀態。它的精神本質源自劇作家獨立、自由的精神狀態,歸根結底是要在作品中“人”的描寫上體現出來。①至此,呂效平已將“現代戲曲”的定義及界定明確下來。本文認可并沿用他的這種提法與界定,并進而推斷、鑒別一個作品是否可稱作“現代戲曲”,需要將其置于戲曲現代化進程進行審視,其中的評判標準之一是戲劇是否寫出了真實的“人”。
何謂“人的戲劇”,胡星亮曾這樣作出解釋:“它是一種作為精神主體的人所創作的戲劇,是一種用來表現人、體現人文關懷的戲劇,也是一種與人進行情感交流、精神對話的戲劇”,“人的戲劇”在關注和描寫人上可分作“現實生存、價值原則、終極關懷”三個層面②。“現代戲劇是‘人的戲劇,它站在人道主義和人的全面解放的立場,更重視人的生存、生命和命運,更重視人的情感本體和人性深度”③。如果從以上角度進行剖析,一代戲劇大師曹禺先生早年的戲劇《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是“人的戲劇”;但是后來,他的《蛻變》《明朗的天》《膽劍篇》《王昭君》等劇作,這種“人的戲劇”色彩因素在逐漸減褪,朝著主題理念化、人物意念扁平化方面滑進。這固然有他面對時政題材缺乏把握、對政策不熟悉的原因;更有其在寫作過程中一味圖解、“跟進”的因素。正如他說,在寫作《明朗的天》時,“盡管當時我很吃力,但仍然是想去適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是硬著頭皮去寫的,但現在看來,是相當被動的,我那時也說不清楚是怎樣一種味道”④。一代戲劇大師如此,壯劇現代戲創作中這種現象也不乏其例。
建國以來,壯劇現代戲劇目品種,在廣西地方戲曲創作中不在少數。1959年為參加中國和越南邊境個寶水庫落成典禮,演出壯劇《紅銅鼓》;1964年推出壯劇現代戲《水輪泵之歌》參加自治區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1972年5月創作壯劇《紅嶺壯歌》參加自治區文藝會演;1977年根據革命故事改編的壯劇《梅峰嶺》《西山坳》參加自治區文藝會演;1978年以百色起義為題材創編的《右江怒濤》為慶祝自治區成立20周年作紀念演出;1980年改編劇目《一幅壯錦》參加自治區少數民族文藝會演;1984年又推出改編壯劇《金花銀花》等劇目。這些劇目題材集中,主題性強,均體現出鮮明的歷時性創作特征。如《紅銅鼓》一劇,改編自民間傳說,講述的是壯峒有紅銅鼓,土皇帝來犯時,擂鼓可以聚眾抵抗,土皇帝多次來犯都未得逞。而后土皇帝收買內奸,讓其蓄意破壞紅銅鼓,并伺機入侵壯峒。壯峒奮力抵抗,馱花甚至以血祭爐,待新的銅鼓鑄成后,他們齊心協力再次成功抵御了土皇帝的入侵,馱花在這場戰斗中英勇獻身。該劇情節大都圍繞壯峒抵御戰爭展開,馱花、依法等人物故事情節卻相對簡約,明顯有“見事不見人”之嫌。
現代壯劇《我家住在銅鼓嶺》則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該劇在將人物置身于矛盾沖突的同時,從矛盾沖突中寫出人物的個性化與真實性,情節內部結構采用西方沖突概念和中國傳奇概念二者相結合的方式凸現。這主要體現在,戲劇事件的核心是主人公在短時期找到幫助貧苦鄉村脫貧的方法與途徑,這在舊社會是完全不敢想的事情,而在新社會得以實現,故事情節本身具有傳奇色彩同時,對戲劇創作也帶來很大的挑戰。具體到戲劇創作,該劇圍繞“脫貧”故事情節,分別從“村頭纏村官”“保護鼓王宅”“負荊代請罪”“窮漢借獎牌”“母女各訴請”等環環相扣、密切相關的事件沖突中構建情節,每個事件都符合西方戲劇的沖突概念。所謂沖突,是指來自于人的行動,出于人的意志的沖突。從上可以看出,該劇每一場戲都設置有沖突,且這種沖突來自新舊觀念的思想矛盾,“落后”與“先進”之間的行動矛盾,在沖突層層設置、矛盾層層解決中體現人物的個性化,將人物形象“立”了起來。具體說來,田桂花前后認識的轉變源自現實生活中對扶貧工作的認識程度的變化,初次接到前往銅鼓嶺扶貧任務的她一開始是不愿意的,后來因為對故鄉的眷戀她才選擇回到故鄉,而來到故鄉后又因沒有深入基層生活而忽視了傳統文化的保護。在“保護鼓王宅”中,蘭三帶領施工隊試圖強拆鼓王宅,被田桂花攔下,面對幾百年的宅院,田桂花忍不住唱道:
“我從小,曾在這吊腳樓下避風雨,
曾在這吊腳樓上唱兒歌。
離屯后,夢里常見吊腳樓,
拆了它,幾多不舍與心酸……”
田桂花的心理在此處發生轉變,由原先的接受扶貧命令轉變為主動投身扶貧工作,并且將扶貧工作與自身的榮辱緊密聯系起來,這一轉變使得田桂花的豐滿形象也逐漸得到凸顯。而在“負荊代請罪”中,田桂花效仿古戲臺里的行為負荊請罪,對自己的十下抽打既“打”出了她的一片赤誠和真心,也“打”醒了執迷不悟的蘭三,更是打動了群眾,“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最終使干群矛盾化解。
可以說,該劇從矛盾沖突中寫“人”,寫立體的“人”,寫出“人”的復雜性,而寫人的最終目的是要寫出真實的人。通過對真實的人的描寫來關注人的自身發展現狀,關注人的生存狀態,以現代意識和理性啟蒙來燭照之,從而培養獨立、健全的人格。如果說一個現代戲要獲得生命力,除了題材要符合人們的審美習慣外,它所傳導的主題意蘊、所體現的人物形象都要能夠和當下人的精神相融匯、情感相關聯,只有與當下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相聯結時,它才能充分發揮戲劇的認知功能。現代壯劇《我家住在銅鼓嶺》的這種嘗試是成功且難能可貴的,對推進壯劇的現代化進程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三、 在繼承中發展:現代壯劇藝術價值新取向
傳統壯劇素有“土戲”之稱,這和壯劇起源于民間小戲,受民間山歌、其他戲劇種類如壯師公等祭祀儀式影響而逐漸發展起來。也正因為壯劇的“土”,擅長表現農村題材,所以《我家住在銅鼓嶺》選用的是壯劇而不是以表現“袍帶戲”見長的桂劇。傳統壯劇音樂唱腔獨樹一幟,有慢板類、中板類、快板類,音樂風格多樣,清越、悠揚有之,細膩、柔情有之,古樸、粗獷有之,在對于現代戲整體打造有著較大的發展空間。《我家住在銅鼓嶺》作為現代戲,在表現手法上明顯繼承了傳統壯劇唱腔等藝術優長,同時還汲取了廣西其他地方戲曲藝術的“營養”。如在“村頭纏村官”“保護鼓王宅”兩場戲中,可以看到彩調劇的表現手法。“村頭纏村官”主要寫村官和村民間的矛盾,通過二者對扶貧工作的態度可以看出該村脫貧道路的艱難;這其中,村民的“刁鉆”和村官的工作作風古板是其矛盾所在。《我家住在銅鼓嶺》在這一段中用歡快的曲調展現,將村民的愚昧和蘭三的蠻橫與無奈以滑稽的形式表達,使得劇目意趣盎然而明顯少了許多說教意味。“負荊代請罪”一場戲明顯化用彩調劇連臺本中的表演身段,十下的自罰打跑了與村民的隔閡,也打出了對銅鼓嶺的深情。
《我家住在銅鼓嶺》在繼承傳統壯劇藝術優長的同時,在表現手法上又銳意創新。如在“拆遷”一場戲中,無論是音樂、表演,還是道具,都是化自傳統的壯劇,而在唱詞方面則進行了明顯革新,以滿足演出的需要。“窮漢借獎牌”里韋二寶耍賴想向尤菜花借獎牌一事,“借、租、搶”都是來自于傳統壯劇,但用在此處則有明顯的現代感,同時又增加了生活意趣。這種做法,也是壯劇藝術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勢。如同廣西其他地方戲曲發展一樣,地方戲曲由傳統戲曲向現代戲曲邁進的現代化進程當中,藝術變革與創新將是一個必然展開的話題。這既有繼承傳統、汲取傳統戲曲營養要素的訴求,也有以新的舞臺審美風貌呈現現代戲劇創作元素的藝術探索。在現代壯劇《我家住在銅鼓嶺》中,“拆遷”“窮漢借獎牌”“互聯網”等場景都是傳統戲劇中未曾出現過也未曾展現過的,臆想通過既往“舊瓶裝新酒”或“移步不換形”顯然已經難以滿足壯劇自身的發展需求和當下觀眾的審美需要。這不僅僅是一個單純藝術探索問題,其揭示出的啟示意義對現代壯劇來說是整體和全方位的。正如傅瑾所說,傳統戲曲向現代戲曲邁進的過程中,無論是戰爭場面,還是平民生活,是否適宜于用戲曲表現,關鍵不在于它們與戲曲通常習見的表演程式是否有距離或有多大距離,而在于我們是否能找到合適的表達內容,為戲劇家想表達的對象找到精彩的舞臺手段,跨越生活與藝術之間的巨大鴻溝,完成從生活到戲曲表演的創造性轉換。①
王國維曾這樣定義戲曲:“戲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也。”②也即從戲曲的劇場性角度來看,戲曲具有歌舞性的特點,繼而逐漸從唱、念、做、打等方面結合各地民族風貌和審美習慣而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程式,但其歌、舞的本質一直貫徹始終。早在1997年的壯劇《歌王》中,就可看出其從舞蹈的一極對壯劇的表演藝術進行探索,在詩意中追求戲曲藝術的抒情性表達;《我家住在銅鼓嶺》則嘗試從曲的一極對壯劇表演藝術進行開掘,呈現戲曲音樂的抒情化表達。一首《我家住在銅鼓嶺》的曲子貫穿整個劇目,成為田桂花內心情感的表達,或是對故鄉的思念,或是對故鄉的留戀,或是對故鄉的自豪,聲聲傾訴她內心的情感,同時也成為換場的連接點。“我家住在銅鼓嶺,從小聽著打鼓聲。鼓聲知我苦和甜,鼓聲是我根與魂”,一方面道出田桂花與銅鼓嶺“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思;另一方面揭示田桂花堅持傳承傳統文化、發展文化產業理念的根源所在。整個劇洋溢著濃郁的“思鄉、念鄉、為鄉”的情懷,以情動人,感人至深。壯劇鑼鼓的綜合運用,使得音樂成為一種意象。例如結尾部分,壯劇中的各式鑼鼓登場,保持了樂器的本身特色,同時也營造了宏大的敘事場面。它表達的鼓聲是銅鼓嶺人的魂,而這鼓聲來自于歷代的傳承,這種文化的傳承是現代壯族人的根性所在,它是一種符號,一種精神的體現,而這種精神是與壯族人民的精神內核相一致的。無論是抒情化還是意象化,都源于戲曲審美對情韻的追求,而這種情韻的原動力又來自田桂花對故鄉的深情,因而顯得真實可信。
當下,振興地方戲曲呼聲一片,且在官方、業界、受眾三方已成共識,但“戲劇危機”陰影依然存在。如同其他地方戲劇一樣,壯劇人才流失,劇團班社萎縮、作品推陳出新難、觀眾逐漸離開劇場等現象也較為普遍。面對這些現象,有人呼吁政府扶植壯劇,也有人呼吁社會各界關注壯劇命運,還有人呼吁壯劇要自我“提氣”謀求發展創新。凡此種種,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有一點需要明確,即便壯劇外部生存條件得到改善,也并不意味著壯劇的生存危機得到根本解決。這是因為,任何地方戲劇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語言表演、音樂唱腔、舞臺表現等多種表現元素。正如廖奔所說,這首先得是表演語言靠向地方方言;其次是音樂唱腔逐漸吸收當地成分而發生地方性轉化;再次是舞臺表現方式和內容逐步趨向于當地群眾的欣賞習慣和審美趣味③。換句話說,現代戲曲作為一個整體藝術,這三者價值取向是相關聯的,相輔相成的,任何一方面的偏廢都可影響戲劇發展,導致戲劇危機。這些原則同樣適用于傳統壯劇向現代壯劇邁進的歷史發展進程,即當傳統壯劇發展的原有生態發生改變時,新的壯劇生態在逐漸形成,從傳統壯劇向現代壯劇邁進成為了一種歷史必然,在邁進的過程中勢必會推動傳統壯劇的蛻變。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審視壯劇藝術本身,思考其是否能適應當下的發展趨勢,并努力提升自身的藝術品格,是現代壯劇藝術自覺追求的一個形式體現。這種體現可能還處于由傳統壯劇審美向現代壯劇審美轉化的起步階段,但哪怕是一小步,也是一種進步。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在現代壯劇《我家住在銅鼓嶺》中看到這種自覺的藝術追求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藝術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