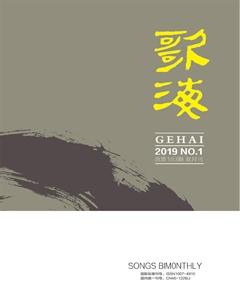兒童音樂劇《月亮上的媽媽》音樂創作闡述
顏賓
[摘 要]用兒童劇強化社會關注,用藝術手段關愛特殊的孩子群體,用美好的音樂來溫暖、感動和激勵中國留守兒童,是文藝工作者身上擔負的一種社會責任。在音樂創作上,必須摒棄簡單生硬、呆板僵化的平直化設計,讓硬道理包裹在“潤物細無聲”的“巧克力”式感染中,與兒童心理處于同一種共鳴狀態,最大限度地體現音樂在兒童劇中應該起到的作用。同時,融入多種中國傳統音樂類型,以中國式音樂講述中國故事,探索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新時期兒童戲劇道路。
[關鍵詞]兒童劇創作的責任與溫暖; 兒童劇音樂的“巧克力”感染;兒童劇音樂守正創新的中國式表達
一、用兒童音樂劇給留守兒童帶來溫暖
在2018年舉行的廣西第十屆戲劇展演中,《月亮上的媽媽》是參演的唯一一部兒童音樂劇,獲得二等獎及桂花音樂創作獎,并得到了廣大觀眾的認可。該劇在劇本定稿時,重新集結了屢獲區內外大獎的兒童音樂劇《壯壯快跑》原班人馬共同發力,筆者也像在兩年前創作《壯壯快跑》時一樣,再次以作曲和現場樂團指揮的身份完成了全劇音樂創作。
《月亮上的媽媽》是一部關于中國留守兒童生活的原創音樂劇。那么,我們為什么要創作這樣一種題材的音樂劇呢?
我們都知道,“兒童是國家的未來”,但是在當下中國,留守兒童現象仍然作為一種令人牽掛的疼痛存在著。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農村的不滿十六周歲未成年人,他們一般與上輩親人生活在一起,而那些年邁體衰的臨時監護人本身都可能還需要別人來照顧,對孩子的學習和身心發育自然很難關愛到位,從而造成留守兒童在生活上缺乏細致呵護,在行動上缺乏有效約束,繼而出現性格孤僻、情緒低落、行為散漫等問題。據權威部門統計,現階段中國有6000多萬留守兒童和3000多萬處于流動狀態的未成年人,人數約占全國近4億未成年人總數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說,每四個兒童當中,就有一個處于留守或流動狀態。
如何使留守兒童擁有正常的心理、情緒和生活,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已經成為一個讓我們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對此,黨中央和國務院一直高度重視。春風化雨,滋潤大地,習總書記在2018年1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四次會議時又一次明確指出:“要讓留守兒童,感受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顯然,一切都充滿希望。
事實上,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既需要我們按照黨和政府的相應部署推進,也需要全社會一起共同參與。從藝術工作者的角度來說,針對留守兒童創作相關的兒童音樂劇無疑是我們的一種責任,也是能直接給孩子們帶來心靈溫暖的有效方式之一。事實證明,兒童音樂劇非常契合孩子們的情感體驗,深受廣大少年兒童喜愛,它具有思想的明確性、道德的純潔性、人物性格與行為的真實性,同時又有藝術的趣味性,能夠在藝術化的舞臺呈現中從心理上親近孩子、從情感上呵護孩子、從品德上引導教育孩子。基于以上認識,筆者認為,用兒童劇強化社會關注,用藝術手段關愛特殊的孩子群體,用美好的音樂來溫暖、感動和激勵留守兒童,是我們每一個文藝工作者身上社會責任感的一種具體體現。
二、用音樂給“硬道理”裹上“巧克力”
對孩子們而言,兒童音樂劇的理想狀態應該是“好看、好聽、好玩、有參與度”,想要進入這樣的狀態,就需要劇組各主創部門緊密而默契地配合。我們必須充分注意,兒童觀眾的年齡和性格特征跟成人觀眾大不一樣,他們活潑好動,而且注意力不能持久集中,孩子們很容易在場內自行玩耍嬉戲,全然不理會臺上正在發生著什么,甚至連陪伴的家長也會玩起手機而游離于演出之外。如果在音樂配置上不能根據劇情體現出針對性處理,那不但不能打造出一部成功的兒童音樂劇,甚至會釀成一場“聲音災難”。當然,這其中原因很多,有可能是故事類型、劇情推進和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問題,但如果劇情等沒有硬傷,起重要輔助作用的“音樂”沒能真正去幫助發展劇情,讓需要表達的主題和道理通過特別設計的旋律柔軟、親和、有趣地釋放出來,并引領著孩子們跟隨劇中人物、事件一起喜怒哀愁就是一個重要原因。
筆者認為,在這個各創作部門無縫連接的戲劇流水線上,劇中音樂的創作和配置至關重要,包括聲樂部分的角色唱段和器樂部分的現場伴奏、開場及過場音樂等,都必須反復推敲,唱腔和唱段中的獨唱、對唱、齊唱、伴唱等演唱形式,跟其他表演形式一起都是發展劇情、刻畫角色性格的主要表現手段,只有相互間默契配合、相得益彰,并且讓硬道理“包裹”在好音樂這塊誘人的“巧克力”中,才能確保全劇的氣氛渲染、節奏調節與結構布局等獲得較為完美的舞臺呈現,讓孩子們自然融入其中。
在兒童音樂劇《月亮上的媽媽》音樂創作過程中,筆者深深體會到,只有摒棄簡單生硬、呆板僵化、平直化的音樂設計,讓音樂成為“潤物細無聲”的“巧克力”式引領和陪伴,與兒童心理處于同一種共鳴狀態,才能最大限度地體現音樂在兒童劇中應該起到的作用。
三、《月亮上的媽媽》音樂創作構想
《月亮上的媽媽》講述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故事,它既簡單明了又哲思深邃,貌似奇幻荒誕卻又無比真實。
故事是這樣的:在一個昔日美麗、如今荒蕪的小山村里,鄉親們都進城打工去了,只剩下留守兒童李想跟古稀之年的老木偶、老裁縫和老郵差相依為命。在日思夜想中,媽媽終于出現在李想夢里面,她告訴兒子自己并不在城里打工,而是在天上用魔毯為天下小朋友變換月亮的形狀,以月亮的陰晴圓缺傳遞孩子們和離別的爸爸媽媽的思念之情。媽媽還告訴兒子一個道理:在一切美好事物的背后,都有人在默默地奉獻著!李想把“媽媽在月亮上打工”的消息,興奮地說給老人們聽,不料三位老人一致裁定:你生病啦,在說胡話。李想倍受打擊拒絕再跟老人們交流,他仰望星空對著月亮訴說的“瘋魔言行”,戳中留守老人們的心肺痛點。他們站在孩子的角度換位思考,回憶起以苦為樂的童年生活時恍然大悟,得出“哪里有媽,哪里才是家”的暖心結論,真正理解了想象奇特、聰慧敏感的李想。為幫李想實現見到媽媽的美好愿望,老人們齊心協力開始執行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先是唱起山歌“喊月亮”,繼而爬上樓頂“摘月亮”……三位留守老人、一個留守兒童,在寂寞的鄉村里,用強勁想象和無言大愛,將善意的謊言變成了真實情景。
“不要低估孩子們對音樂的理解和感悟”是我在創作該劇時念念不忘的一個基本原則。相關調查數據表明,今天身處地球村的少年兒童已經具有很強的互聯網思維,早已不滿足于“讓我們蕩起雙槳”式的傳統兒歌,他們精力充沛的身體里跳動著強烈的現代節奏。基于這樣的判斷,我在創作中力圖讓劇中所有音樂聽起來既不乏溫軟走心的音符,又充分強調奔放熱烈的旋律和節奏,讓現場的樂隊和臺上的演員在互動互助、齊心協力的相互激勵過程中,構成一種“兒童戲劇創作共同體”。這種具有針對性的劇場“現磨音樂”,可以讓孩子們見證每一個音符的誕生過程,讓家長和孩子一起在歡樂的聆聽中體驗到別具一格又契合孩子們心里期待的“中國式兒童搖滾音樂劇”。
在創作過程中,筆者首先為該劇找到了符合劇情的節奏律動。劇中留守兒童李想的憂慮無常、空巢老人們的慈愛無奈、小母雞的詼諧搞怪、媽媽的虛無縹緲……都有各自不同的節奏律動和符合人物性格的特定旋律。比如在表現主人公李想方面,筆者用陡然轉調和節奏突變的手法來設計唱腔和情緒音樂,以此將這位留守兒童在心智和性格上的不穩定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來;又比如,在小母雞這一形象的音樂設計上,主要強調的風格是節奏明快、清新詼諧;再比如,對于老木偶、老郵差、老裁縫這三位老人,音樂形象上是根據其木偶文化、信使文化和剪紙文化的“非遺”特性,分別采用布魯斯、流行搖滾、傳統戲曲和民間曲藝等豐富多彩的音樂風格進行“陌生化混搭”,將草根傳統和現代特性有機結合起來。這樣一來,每個角色形象在各具特性的同時又保持整體的風格統一,全劇音樂憂而不傷、趣味十足、溫情明亮,釋放著無限期冀和希望。
四、用中國式音樂講述中國故事
在兒童音樂劇《月亮上的媽媽》的音樂設計中,筆者還使用了“新瓶裝老酒”的創作手法,在守正中創新,并收獲了意想不到的驚喜。
比如,在老木偶的《嫦娥奔月》唱段中,引子使用非洲“毛利戰舞”的表演方式,又巧妙融合了傳統戲曲的“叫口”,看似“復古”,卻煥發出盎然新意。又比如,筆者在劇中還大膽采用了彩調劇“趕板”的鑼鼓點和曲調,將之作為一整首曲子的過門和間奏,聽起來妙趣橫生;還比如,將民間曲藝“零零落”的呈現手段全權交給現場合唱團,根據劇情需要為主唱部分的和聲及幫腔鋪墊,出人意料卻又恰到好處。劇中很多演出場景,在搖滾樂的配器風格中,無論是手持“金錢板”邊打邊唱、載歌載舞,還是采用“三句半”幽默詼諧替代臺詞,甚至敲打著“漁鼓”讓小母雞開口唱歌等,都被證明是一種毫無違和感的視聽享受。
現場演奏的多樣化,是演員演唱豐富性的必要保障。單是現場樂隊就有現代樂器如口琴、古典吉他和電子吉他、電子琴合成器、貝斯等等;演員們和合唱團的現場演唱,加上地域性傳統“非遺”表演樣式和音樂符號的融入,極大的豐富了該劇的音樂色彩,這些元素的整合經過特殊的化學反應后,產生出無比奇妙的奇幻效果。更重要的是,如同現磨咖啡般的現磨音樂,給看戲的小觀眾們上了一堂生動活潑的音樂課,相信這些“不走尋常路”的音樂類型、樂器特色、傳統戲曲和民間曲藝元素,定能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上播下最美好的音樂種子。
筆者和全體主創人員在明確創作目標和清晰美學路徑的同時,心中不約而同地萌發出一點點“小野心”:嘗試在被安徒生、格林童話等“舶來戲劇文學”的重重包圍、眾聲喧嘩之下,蹚出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新時期兒童戲劇道路——用中國式音樂講述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