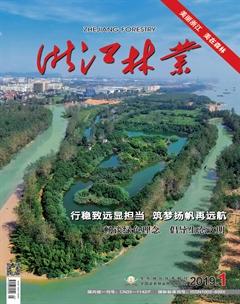蛤蟆與田雞
張海華
“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這是宋代辛棄疾的《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中的名句,當時作者被貶官而在江西閑居。那么,這里的蛙聲,會是什么蛙在鳴叫呢?
這并不是一個故意刁難人的問題。如果熟悉江南常見蛙類,這問題就非常簡單。這首詞里已經提供足夠的關于物種的信息:夏夜,在江西上饒的稻田中,蛙聲多而且響亮。符合這些條件的蛙,按照我老家浙江海寧的方言來說,主要就兩類:蛤蟆與田雞。
童年記憶:青蛙的大合唱
在浙江海寧,蛙類被分為3種:小而灰色的叫蛤蟆,大而皮膚粗糙的叫癩施(即癩蛤蟆),大而皮膚相對光潔的叫田雞。這個分類法跟寧波略有不同,在寧波話里,“癩施”泛指各種蛙,而“噴火癩施”“癩蛤蚆”或“蛤蚆癩施”才特指癩蛤蟆。
海寧處在杭嘉湖平原上,河網密布,阡陌縱橫。幼時,我家東邊不遠處就是水田。春夏時節,常在半夢半醒的清晨,聽到陣陣蛙鳴傳來。這“呱呱”的大合唱,在童年時或許還會覺得有點擾人清夢,但現在想聽也難以聽到了。
農忙時節,我們孩子也會下田幫助父母做點力所能及的事。猶記得,我拎著秧苗,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邊走邊看著一只只小蛤蟆相繼跳到水田里。等我走過,小家伙們又會慢慢回到田埂上蹲坐著,有的還會繼續鼓著腮幫子起勁“唱歌”,只見兩個白色的泡泡在它下巴一鼓一鼓的,就像我們吹泡泡糖一般,十分有趣。
那個時候,蛤蟆是水田里最多的蛙。釣蛤蟆,則是我小時候常干的一件事。這釣法極為簡單,但現在想起來未免有點殘忍。不用蚯蚓,也無需魚鉤,只要就地用手拍住一只蛤蟆,扯下它的一條后腿,用線系住,線的另一端系在竹竿上,這釣蛤蟆的工具就算是做好了。然后,拿著這簡陋的釣具,在田野里亂走,看到一只蛤蟆,就將拴在線上的蛤蟆腿在它眼前輕輕抖動,蛤蟆的眼睛對靜止的物體是無視的,但一發現眼前晃動的小東西,就會以為是昆蟲之類,立即張嘴猛撲過去。可憐這貪嘴的小家伙,直到我拎起釣竿,它還緊緊咬著不放呢!于是,隨即被我放入了塑料袋中。一個上午可以釣到很多蛤蟆,回家后,將它們全倒在養著雞鴨的院子里,那些家禽頓時飛奔過來,拼命搶食,頃刻便吃光了。不過,有一次我把這系在線上的蛤蟆腿在一個泥洞口亂晃,突然有一條蛇從洞里躥了出來,一口吞住。我的天哪,竟然釣到了一條蛇!這情景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迄今仍記得清清楚楚。
至于田雞,白天在水田里看到的概率就少很多。倒總是記得,小時候在桑樹地旁的河邊走,常有東西從茂密的草叢中躍起,“撲通!”很響的一聲,它跳入了河中。我知道,那一定是一只大田雞。可惜,每次我都只聞其聲而不見其蛙。
夜探公園,再遇童年“小伙伴”
說了這么多,辛棄疾這首詞里的謎底還沒揭開,這蛤蟆與田雞到底是什么呀?大家不要急,不是我故意賣關子,只因我是在講述童年故事,小時候的我確實叫不出它們的大名,只知道蛤蟆與田雞。不僅我們小孩子不知道,父母與老師也不知道。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它們到底叫什么呢?
直到最近幾年喜歡上夜探自然,童年的謎團才終于解開。
在國內有些地方,蛤蟆可能指好多種蛙,但在我老家,蛤蟆就是指一種蛙,即澤陸蛙;而田雞,我也是夜拍后才知道,其實分為2種,即金線側褶蛙與黑斑側褶蛙。這些蛙都是江南稻田區域的常見蛙類,且善鳴,因此辛棄疾的“聽取蛙聲一片”,所聽到的主要就是這3種蛙。當然,在不少地方,像小弧斑姬蛙、飾紋姬蛙等蛙類也會在水田中高聲鳴叫。
童年轉瞬即逝,讀書、工作……一晃20多年過去,記憶中的蛙鳴也漸漸遠去,我原本以為不會再相遇,沒想到“老夫聊發少年狂”,快40歲的時候,突然間想重新探尋青蛙的秘密世界。起初,大概是2012年前后吧,我常到寧波市區的綠島公園夜探。這個公園的前身是姚江動物園,樹木茂密,有幾個小池塘,白天經常去那里拍鳥。沒想到,在一個初夏的夜晚,剛走到園中的一個小水塘旁,就聽到陣陣響亮的蛙鳴。打著手電躡手躡腳過去,一看,可不,好幾只蛤蟆(即澤陸蛙)分散在附近,正鼓著聲囊大聲鳴叫。這些都是雄蛙,賣力鳴叫自然是為了求偶。
澤陸蛙在中國分布很廣,晝夜都出來覓食,其適應能力較強,既出現在水域內,也能在離水較遠的旱地草叢中活動,因此也是最常見到的蛙類之一。相信很多人都見到過,但未必仔細觀察過它。這是一種體長四五厘米的小蛙,背部顏色通常跟泥土差不多,以灰色或灰綠色打底,但有的多綠色或紅色斑紋,也有的個體具有貫穿背部的綠色或灰白色的中線。仔細看,澤陸蛙的背部有數行長短不一的凸起的阿拉伯數字“1”——專業的說法是“縱膚褶”。
當時的綠島公園中也有不少金線側褶蛙,白天去偶爾也能看到。有一次我去那里拍鳥,累了,坐在池塘邊休息,忽見一只金線側褶蛙從綠色的浮萍中探出一個腦袋,非常安靜,長時間保持不動。后來我慢慢站起來,打算俯身細看,它便機敏地一縮頭,潛入水中不見了。后來晚上去日湖公園,看到不少金線側褶蛙趴在睡蓮的葉子上,伺機捕食。我悄悄靠近一只蛙,它有所警覺,但不馬上逃走,而是趴低身子,與葉子完全貼合。
無論在綠島公園還是日湖公園,黑斑側褶蛙相對少一點,而且非常警覺,幾乎見人就跑。我曾經在綠島公園的池塘邊見過一只黑斑側褶蛙,它頭部朝著水面,我剛走近,它就飛身起跳,躍出1米多遠,“撲通”一聲跳入水中。這“立定跳遠”的高超本事,確實讓人佩服。童年時一直只聽見而沒見到的“田雞跳水”場景,這回終于讓我看清楚了。
草深何處聽鳴蛙
金線側褶蛙與黑斑側褶蛙這兩種蛙,最符合人們通常所說的青蛙的形象:它們的體色多以綠色為基調,體形大小中等,分布廣。黑斑側褶蛙雄蛙的叫聲很響亮,接近常用來描述蛙鳴的“呱呱”聲,同樣是為了吸引雌蛙,金線側褶蛙雄蛙似乎要害羞一些。其叫聲的音量較低,類似于小雞的“嘰嘰”聲。
兩種蛙的身體兩側各有一條隆起的皺褶,即所謂“背側褶”,故名“側褶蛙”。說起金線側褶蛙與黑斑側褶蛙的區別,有時還真讓人犯迷糊。我個人感覺,以它們的背側褶的不同來區分更為直觀一些:這兩種蛙的背側褶都很明顯,但金線側褶蛙的棕黃色背側褶(或許這便是其名字中“金線”的來源)更加粗厚,而且不均勻,即局部會顯得尤其粗厚;黑斑側褶蛙的體色極為多變,藍綠、暗綠、黃綠、灰褐等均有,背側褶相對較細而且整條的寬窄程度比較均勻,而且背側褶顏色通常跟體色一致,很多變。我在寧波所見的黑斑側褶蛙大多背部中央還有一條淡綠色的中脊線。
但為什么稱這兩種蛙為“田雞”?有人說,是因為它們的肉比雞肉更鮮嫩;也有人說,這些蛙善于在田里捕食害蟲,就像雞喜歡吃蟲一樣。但從現實來看,意識到后一個理由的人顯然少于前者。君不見,每到春夏時節,在一些菜場的外面,總有人偷偷摸摸在賣田雞。
蛤蟆與田雞都曾是江南水田、小河、池塘環境中的最常見蛙類。如今,澤陸蛙、金線側褶蛙的數量雖說比我童年時少了不少,但總體種群數量還行,但黑斑側褶蛙的生存前景就沒有這么樂觀了。由于棲息地環境被破壞(比如水田變成建設用地,還有農藥的大量使用),以及被大量捕捉食用,國內(包括浙江)的黑斑側褶蛙的種群數量在近些年可謂銳減,在野外越來越罕見。真擔心,不用多少年,這種原先最常見的蛙也會不幸成為瀕危物種。
先不論蛙類在生態鏈中的重要作用,且讓我們體會一下蛙鳴在古人筆下的詩意吧:
雨后逢行鷺,更深聽遠蛙。(唐·賈島《郊居即事》)
水滿有時觀下鷺,草深無處不鳴蛙。(宋·陸游《幽居初夏》)
怪來一夜蛙聲歇,又作東風十日寒。(宋·吳濤《絕句》)
真的太多了,舉不勝舉。
鳥鳴、蟬鳴、蛙鳴……都是寄托著鄉愁的天籟,愿它們不要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