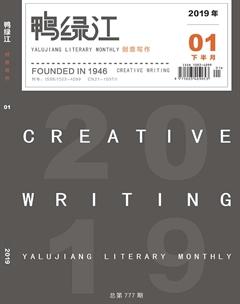與故宮對話
葉君 張詩淇
在浮躁、功利之氣彌漫的時代,為故宮修復文物不僅是一件日常工作,也是一種人生修養。這些匠人們身懷絕技,專注敬業,一件器物的修復也是一種文明的傳遞。《我在故宮修文物》以工匠之心記錄工匠精神,創意獨特、語態輕快、敘事平易、清新自然,贏得年輕觀眾的追捧,為紀錄片開辟了傳播新空間。
為什么選《我在故宮修文物》?其實我覺得有兩點非常重要,那就是它體現了紀錄片在今年發展的兩個標志:第一是新媒體傳播,第二是品牌。2005年徐歡做了一部十二集的《故宮》紀錄片,那是中國紀錄片轉型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到《故宮100》,做出那么多小體量碎片化很精致的作品,再到出現《我在故宮修文物》,把品牌做了一個延展。在這個過程中,給紀錄片留下了非常豐富的啟示。這個作品給紀錄片帶來的啟示對中國紀錄片領域非常重要。
其實這個片子最早在電視播出,收視率并不是很高。我想說的是,需要找到新的觀眾群,找到知音。以往的紀錄片不是不好,而是講話方式有點陳舊,因為紀錄片還沒有找到最準確的傳播方式。這個片子給人的啟示非常重大,我也要向年輕的團隊學習,讓紀錄片年輕起來,不能一張嘴就是五千年,很高興看到這個片子,也祝賀他們給中國紀錄片帶來的啟示。
——張同道
這部紀錄片的一個經驗是做研究,這個也是清影工作室的長項,每次做紀錄片之前,先做調研,做研究,做一個非常周密的研究報告,發現它的價值和意義。現在的紀錄片換了年輕人的視角去看世界,過去我們擔心小孩拍這些匠人,他是不是能夠很好地去溝通、共鳴和理解,但是事實證明,他們是可以的。
過去我們拍紀錄片的時候,帶著一種道德憐憫的狀態,說這些人比誰都苦,比誰都慘,其實《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創作者反而發掘了這些工匠的人生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為什么那么多孩子會作為粉絲去對著這些工匠,跟這個有特別重要的關系,這是一種表現好人好事和英雄模范等題材的很重要的觀念轉變,這可能也是《我在故宮修文物》能獲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尹鴻
張詩淇:不同于以往的故宮題材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通過拍攝對不同類別文物的修復完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講述,您是出于什么考量選取了這樣的切入口?
葉君:之前我接觸過故宮的很多東西,2011年我做了《故宮100》,又接觸了一個我國香港作者的書《我的家在紫禁城》,這個“我的家”就有一個“我”的概念。當時取這個紀錄片的名字時寫了很多題目,寫滿了一張紙,團隊就一起商量,最后確定了“我在故宮修文物”這個名字。
張詩淇:之前您提到,早在2010年,主創團隊就開始關注故宮的匠人群體,有著十萬字的田野調查報告,四個月的集中拍攝。能跟我們分享一下田野調查報告的內容嗎?這對您拍紀錄片有著何種啟發和靈感?
葉君:這個調查不是我做的,是制片人帶著學生做的。他們大概在故宮里面待了三四十天,跟著各個工藝組,什么搗糨糊的啊,在木器組做魚鰾膠的啊。我當時不在,我在做《故宮100》。我自己拍紀錄片的靈感其實都不是來自紀錄片,因為紀錄片我看得比較少。我看的都是一些雜七雜八的學科,比如《紅與黑》《水滸傳》《紅樓夢》、唐詩宋詞,我的靈感都會和這些有關聯。在這些作品中,你看到的世界重新分解,又在重新組合。
張詩淇:就《我在故宮修文物》的敘事方式來講,其實是一個比較新穎的麻花式的構建了多條故事線交叉敘事的復合結構,并且運用了一種平民的視角,您是如何制定這個敘事策略的?
葉君:其實這個敘事策略是拍完之后,剪輯時發現的。拍的時候我們跟著十幾個工藝組在拍,這個時候其實相當于挖礦,你預測這個地方有礦,就先挖,挖完之后再篩,篩完之后可能這些礦還要重新組合成合金。我們就是在重新創造的時候發現,也許用《水滸傳》的結構是最好的。當時素材有三萬多個鏡頭,剪輯對于人的閱讀理解能力要求又比較高。比如說你剪輯青銅器那部分,你要懂工藝,還要對干事的工匠賦予文學色彩,去閱讀理解他的世界,進入他的世界,看看他在意什么東西。
張詩淇:回顧《我在故宮修文物》在B站的走紅,您認為新媒體場域對于傳統文化的傳播起到什么助推作用?如何做到紀錄片在新媒體這個場域中發揮更大的傳播力和社會影響力?您認為紀錄片應該怎樣兼顧它的人文性和趣味性?
葉君:我平時喜歡看人類文明史,你把一個東西放在人類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就會覺得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問題。比如從最早的紙張到電影的出現,再從電影到電視,再從電視跨到手機,無非就是換個瓶子來裝酒。
很簡單,質量做好并且與觀眾的接受度串聯起來,就可以。人類歷史上很多東西發明出來后,最初都是小眾人才能享受到,隨著技術的推廣,越來越多的人可以接觸,這是很好的。我從來不會去想人文性、藝術性、趣味性的問題。這就好比你問足球運動員為什么躲過兩人而射門,他也說不出為什么。
張詩淇:《我在故宮修文物》從播出到現在也兩年多了,現在的您再回頭看這部作品,有什么遺憾或者認為可以更加完善的地方?您理想中的音樂效果是什么樣?
葉君:不用再回頭看,我自己剪完之后都知道有很多遺憾。像鏡頭、音樂、節奏、整體的感覺,這些全有漏洞。很多鏡頭都是不經看的。音樂最開始找人做了,做出來的實在沒法聽,后來也沒有用到片子上。有個很奇怪的現象,人家一聽說是在做故宮題材的,他就把音樂做成“荊軻刺秦王”那種感覺。
后來我一直在找音樂,想要一些現代感的音樂,這可能也和個人審美與愛好有關系。比如有一些電子音樂、游戲里面的音樂,在現代感的節奏中融入了古典的成分。比如說像敲一個大陶瓷缸的聲音,或者木質的彈撥類樂器這種感覺的音樂,你能感覺到是某種材質的樂器的彈奏,但節奏又是比較有現代感。基本上按照這種感覺去尋找的,也能夠和主題比較貼近。
張詩淇:那您覺得中國的文化產品應當怎樣走向世界?
葉君:就像足球一樣,多踢國際比賽,踢多了自然就知道該怎么做了。你看,中國足球一踢就知道世界排名才八十幾。要多參與國際交流,知道自己在世界文明的位置。但是也很難,因為現在很多人寧可不做事,也不愿意犯錯,這幾年的氣氛就是這樣的。要走向世界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張詩淇:結合您從業的經驗和感受,您能分享下自己的心路歷程嗎?您心目中優秀的紀錄片是怎樣的?
葉君:資本的風險這幾年很明顯,可能也與中國這一百多年的心態有關系,老在想彎道超車,那別人為什么不彎道超車?這就是中國的資本環境,本來應該有自然生長的空間,但人們都是在非常快地套取利潤。我曾經看過一個數據,好萊塢平均制作周期是871天,放在中國就不太可能。最近都在說,才兩年多的時間,中國影視的資本熱潮就消退了,這還只是資本和商業的環境。目光放在整個生產線上,就會發現各個位置上的人專業度都不夠,他們都來不及去專業。
之前看過一段話,其實不僅可以形容紀錄片,也同樣可以用來衡量各種內容生產。拿作家作比,四流的作家只是簡單或膚淺地圖解現實,不過供人消遣和休閑罷了,反腐敗小說、美女文學、新寫實主義等,大多在這個境界;三流的作家,透過現實已窺視到歷史和文化的影子,像莫言、賈平凹、陳忠實、余華、阿來等作家已超越這一境界,正在向人本身進軍;二流作家,直抵豐富、復雜、多維的人性,從物質層面向精神層面探索,許多小說為什么沒有生命力,就因為他們還處在時代和現實的包圍中,還沒有沖進歷史和文化內核;一流的作家,是世界級的大作家,不僅穿透現實、歷史和人性本身,而且關懷人類存在的意義,像卡夫卡、貝克特、馬爾克斯、海明威等人,無不是這種境界。就紀錄片來說,總體就是爭取做到專業性和大眾性的平衡吧。
(葉君,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導演。張詩淇,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