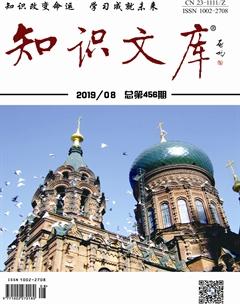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背景下高校創新型人才培養
宮琳丹 范路安 徐曉冬
十八大提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創新離不開人才的助力推動,人才輩出離不開高校的培養輸送,尤其對某些高精尖領域專業人才的供給,高校更是擔負履行著不可替代的責任和義務。源于拉丁語的“創新”包括更新、創造新東西和改變三個含義,創新人才培養模式也應不斷更新與時俱進。當前創新型人才供給遠不能滿足國家需求,因此高校應以培養科技創新型人才為目標,既要突破傳統教育觀念方法,將不合時宜地進行合理認知和糾正,又要辯證地進行繼承和發揚,不斷尋求適合我國教育國情的創新實踐教育新理念和新模式。
逾百年東西方創新教育發展史對人才培養中的“創新”一直都很重視。20世紀初的《發展經濟學》中哈佛大學熊彼特教授將“創新”理論引入社會經濟發展領域,由此創新理論被引入教育教學研究。1959年,美國心理學教育家杰羅姆·布魯納在《教育過程》中闡述了需要通過改革教學方法和重視發展學生智力,提高學生邏輯思維和獲得知識的能力,親自成為結論和規律的發現者,這體現了學生作為主體在實踐中獲得創新能力的論斷。而我國向來都將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作為教改的重要目標,對創新能力的內涵、培養的影響因素以及方法等都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實踐。如早期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第一流教育家》中提出能否把學生培養成具有“創造精神”和“開辟精神”的人才關乎國家富強和民族興亡。此后,著名創新教育的偉大實踐者、科學家和教育家錢學森更提出了“理工結合”、“教學與科研結合”、“培養出高質景、高水平的‘攻關、突破、創新型人才”和“培養‘知識要交叉融合、思維要貫通、素質要全面、能力要多維、水平要拔尖的創新人才”的人才培養模式。
傳統教育文化、理念和方式存在的某些弊端抑制了對學生的想象力、創造力的發掘,正如韓愈《師說》中的“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明確指出師傅需要向弟子傳授知識和技術并解答疑惑,而解答和傳授是應貫穿于學習和實踐兩個過程中,但我國的傳統教育更多是單向的,它更側重于知識的灌輸,而不重視或忽略實踐對知識掌握和能力提高的意義,這種“重教育、輕實踐”的不足必須要得到改進。當代大學生已不僅滿足于從書本中、課堂里和媒體上獲取知識和技能,主觀上更愿意付諸行動和親身體驗以獲得提高,這一需求是主動的和積極的,它與實現創新型人才培養目標不謀而合。
大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與很多因素相關,如自身的知識結構體系、心理素質和思維方式等,這些屬于內在因素,是內驅動力;學校創新教育教學體制、方法,學校創新教育環境、氛圍以及社會創新氛圍等,這些屬于外部因素,是影響培養大學生參與科技創新實踐興趣、提高學生的科技創新實踐能力的外驅動力和決定性因素。因此只有實現內外兼顧,內外驅動力才能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在創新教育改革中該將理論教學與實踐相結合、教學與研究相結合,在校園內形成創新教育氛圍,建設創新教育文化,同時通過調動學生的積極、主動和創造性來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創新意識,進而提升大學生的創新實踐能力。
歷史上各國對創新人才的培養方法雖不盡相同確值得我們借鑒:20世紀中期蘇聯借助法律手段將創新能力教學體系引入憲法促進人才培養。日本20世紀80年代引入創新能力教育,在各類學校中進行普及并將其列為21世紀教育的目標。美國政府則通過一系列政策扶持,如以項目資助、科技獎勵、校企聯合等方法鼓勵大學生在指導教師的引導下參與科研實踐,以激發和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德國柏林大學則在教育基層的實驗室開創了教學模式“研討班”——學生和教師共同的研討小組,教師將教學與研究相結合,除了知識傳授外,還會傳授學生研究所需的技能共同開展研究,這種教學組織方式和教學模式至今為止仍不失為一種良好有效的實踐教學范本。目前,我國政府將創新創業人才培養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制定了一系列發展方針并出臺人才培養政策,這對高校的創新人才培養無疑是難得的發展機遇。
大學校園充滿活力和挑戰,師資力量雄厚、教學資源聚集且科研氛圍濃厚,如何充分利用、整合這些優勢,全面提高大學生培養質量不僅是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迫切需要,也是推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促進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創業就業的重要舉措。高校教師要以“遵循高等教育規律”和“著力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高等教育教改與發展的宗旨為目標,不斷提高大學生創新實踐能力培養的新模式和運行機制的摸索與研究;要以適合中國國情、契合學科特點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能夠針對不同素質和特點學生因材施教、適當引導,在迎合國家以創新來驅動社會發展背景下,使高校成為創新人才輩出和創新活力迸發的搖籃和源泉。
基金項目: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背景下高校科技創新型人才培養的實踐與研究(哈爾濱工程大學教學改革研究項目,編號:JG10218Y20)
(作者單位:哈爾濱工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