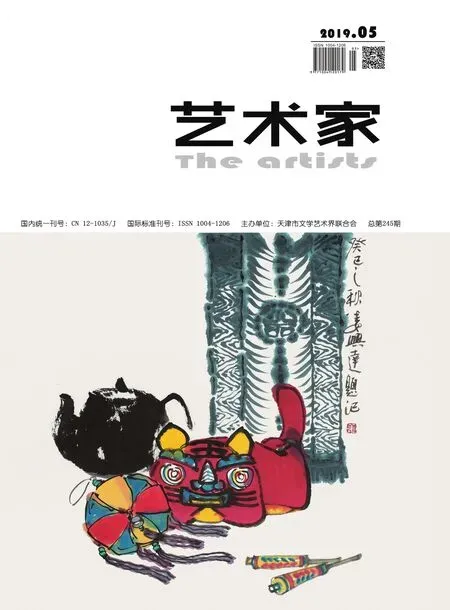微觀探視“符號”在視覺藝術創作中的發展方向
□趙津毅 長沙文化藝術展覽中心
藝術作品中的“符號”一直是欣賞者閱讀畫面的主要因素,“符號”具有時代性,與所處時代文化、經濟、科學等方面聯系密切,在科技日益發達、思想空前開放的今天,藝術創作也隨之開始了跨學科的表現方式,其所傳達的不僅僅是視覺表象的唯美形態,較以前具有更豐富的內在信息,更加耐人尋味。視覺藝術中“符號”的形式也更加多樣化,不再是形象“符號”主導畫面的時代。
隨著經濟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中國當代藝術無可避免地卷入商業浪潮,藝術創作的圈子化和精英化現象明顯,藝術家中的精英分子吸引了社會中的大量資源,其創作也為市場所接受,在為藝術創作給予經濟支持的同時,也使創作思維相對封閉。新星星藝術節是筆者參加過的展覽中印象最深刻的,它繼承了1979年星星美展的自由創新的精神,也可以說是探索性的嘗試,鼓勵青年藝術家追求材料和手法的創新,積極尋求特殊的藝術語言,倡導坦誠面對現實社會和藝術創作的關系。參展人群主要為1975年后出生的藝術家,由于對“求新”的追求與提倡,展覽作品形式相當豐富,各種新型材料媒介的勢頭顯然在展廳中蓋過傳統純顏料繪畫。但無論藝術創作手法和材料如何多樣,作品中總會有自己獨特的“符號”為其傳遞信息。筆者的參展作品是《中國建造—天壇》(見圖1)、《中國盆栽—迎客松》和《中國盆栽—文竹》,雖畫中描繪了不同的形象,但肌理及線條已貫穿在筆者的創作中,同樣的創作“符號”從不同的角度表達創作思路,而最終將合流為真善美之意識形態并傳達出當今社會的某些信息。這也是筆者通過創作對自身世界觀、人生觀和知識觀的粗略體現。在中國系列這組創作中,筆者采取繪畫與制作相結合的技法,尋求一種“新繪畫”方式的存在,創作過程的意義較以前更強,因為以注射器代替了羊毫畫筆來完成作品,這樣的作畫方式與中國傳統的勞動生產方式極為相似,一針一線、一磚一瓦,不斷積累、不斷勞作,最終才出現了復雜的勞動產物。藝術節中張增增、李娜、黃穎等年輕藝術家的作品讓筆者記憶深刻,他們在創作中弱化了對小個體形象“符號”中的“形”的表現手法,而在材料上進行探索創新,用不同的肌理“符號”和材料“符號”構建成大的景象。一次展覽不能全部反映當今視覺藝術創作的準確方向,但通過百位青年藝術家的作品,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可見一斑。
藝術創作是藝術家用特殊的語言方式對現實的描繪和精神的表達,作為視覺藝術的一部分,架上繪畫以其獨特的藝術“符號”來體現藝術家對客觀世界的態度和看法,藝術“符號”也可以是藝術家形成個人藝術風格的重要元素。對藝術家而言,創作出與時俱進、雅俗共賞的好作品無疑是藝術生涯的最高追求。優秀的作品不僅對技術方法有很高的要求,也要表現出不凡的思想深度和精神內涵。在視覺藝術中,“符號”既能給觀者愉悅和情感化的視覺沖擊,又能以傳遞信息引起共鳴。“符號”選擇的合理性與藝術創作的成功有極大聯系。具有時代可讀性、創新性和審美性的“符號”的是優秀作品出現的關鍵。筆者在創作過程中一直重視對“符號”的試探,努力尋找更加有利于表達的“符號”。從最初的小藍人系列作品注重以形象“符號”傳達信息,慢慢轉變到以肌理“符號”和線條“符號”為主的表現方式,這種轉變無疑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代藝術思潮的影響。
“符號”在創作中的合理運用和更加深刻化都與長期的歷史文化沉淀、大量的實踐創新以及飛速發展的時代有關。隨著視覺藝術呈現方式的多樣化,“符號”也以不同形式出現在視覺藝術作品中,與此同時,“符號”的抽象性、普遍性和多變性的特征展露無遺。“符號”將以更多的形式姿態出現在藝術作品中。藝術家根據自己獨特的體會和分析,將生活中某些不穩定的感性部分抽離出來,并將其以普遍可讀的“符號”形式固定在作品中,進而自然合理地闡釋自己的藝術創作觀念,幫助讀者理解和看懂其他人和事物,這充分體現了“符號”在藝術作品中的表述和理解功能、傳達功能及思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