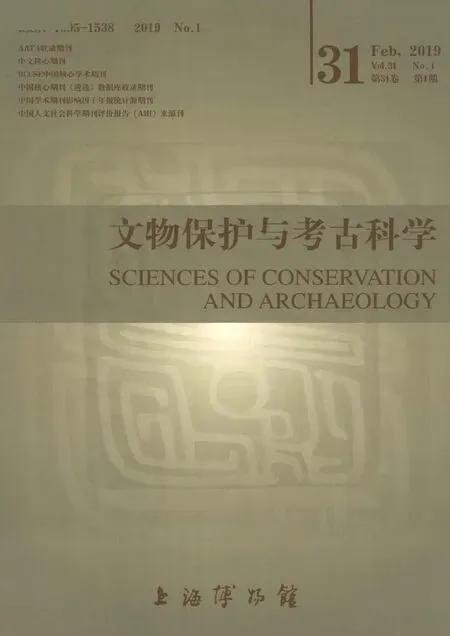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印花絹袋”的修復研究
王 菊,樓淑琦
(1.甘肅省博物館,甘肅蘭州 730050;2.中國絲綢博物館,浙江杭州 320002)
0 引言
磨嘴子漢墓群(“磨嘴子”或寫作“磨咀子”,本文統一作“磨嘴子”)位于甘肅省武威市城西南15 km處的祁連山麓、雜木河兩岸,為一高低不平的山嘴形黃土臺地,臺地最高處為荒坡。磨嘴子漢墓群從河岸直至臺地最高處,在東西約長700 m,南北寬600 m的范圍內,墓葬分布極其稠密[1]。河岸一帶,溝渠縱橫,樹木成林,土壤肥沃。很早以前就是便于人類居住、從事生產生活的好地方。因此不僅有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而且有著極其豐富的漢代墓葬。從20世紀50~90年代起,文物部門就在此進行過數次大規模的發掘,共發掘清理西漢至東漢時期墓葬近百座,出土了大批漢簡、木雕、絲、麻、草編織物等珍貴的歷史文物,一部分現藏于甘肅省博物館[2]。其中紡織品文物以蠶絲為主要原料,尺寸較小,或來自于草編盒的裝飾,或為縫紉材料,也有單獨的絹袋和絳帶。多數表面顏色保存較完好。但由于年代久遠,絲纖維出現不同程度的糟朽,從而導致其它病害的發生。因此,2015年5月,甘肅省博物館委托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中國絲綢博物館)編制相應的保護修復方案。并于2016年底開始,甘肅省博物館的修復人員赴中國絲綢博物館對這批珍貴的絲織品進行搶救性保護修復工作。其中“印花絹袋”的修復難度很有挑戰性,尤其是形制推斷和縐絲紗加固應用技術等方面的研究。
1 文物信息與病害狀況
1.1 文物信息
印花絹袋出土時被盛放于一錦緣絹繡草編盒內,此盒出自武威磨嘴子22號夫婦合葬墓,含盒身與盒蓋兩部分,蓋部拱起。盒內同時還盛繞線板、絳帶、絲線、小飾件及一些縫紉工具等,應為當時實用器具。該墓葬屬于土洞墓,就隨葬品看,不屬于上層統治階級,而只能是普通官吏或地主階級,墓主人的社會地位或可大致比擬為先秦的士[3]。
印花絹袋由三種不同顏色與材質的織物和一枚古錢幣縫制而成(圖1,錢幣隱藏于箭頭處)。在編制本絹袋的修復方案時,使用高清掃描儀,顯微放大鏡,便攜式熒光光譜儀等專業儀器,對三種織物分別進行無損檢測。從組織結構檢測分析可知,棕褐色和深藍色織物材質均為絹,淺黃色織物材質為紗。其中棕褐色為地的絹上印染有白色線狀紋飾(圖2)。對此印花工藝,推斷應是用鏤空版以毛筆刷涂顏料印成[4],對研究漢代河西地區的印染技藝提供了實證。深藍色絹上無紋飾,其中較完整的一塊基本呈三角形。其余殘存部分形狀暫且不明確,置于絹袋中間部位,與棕褐色絹和淺黃色紗縫連,紗從銅錢方孔中緊緊穿過,另一邊殘缺。
1.2 病害狀況
修復前,先在小范圍內使用加濕器霧化空氣,使絹袋變潮濕后,在織物由脆變軟的過程中方可輕輕打開疊壓在一起的織物。三種面料都已極其脆弱糟朽,碳化十分嚴重(圖3);絹袋褶皺團繞厲害,織物幾乎完全失去了彈性,機理變形,呈脆弱的樹皮狀;白色結晶顆粒等污染物較多;多處殘缺,形制模糊。因此,研究其形制,是本次修復的關鍵。
2 拆線前形制研究
盡管拆線后展開各片絹、紗,對文物的形制判斷有直接的幫助,但其風險性也不言而喻。在絹袋的基本形制、大小尺寸沒有確定的情況下,各條針線縫痕極其珍貴,輕易不敢拆卸開來。萬一丟失信息,無法恢復原狀,就等于毀了文物。因此,修復前,先查閱資料,尋找線索,反復研究,在確定其基本形制,做好線釘、量出大體尺寸、記錄關鍵信息后才可拆線。這樣修復成功率會大大提高。
2.1 絹袋下半部分形制推斷
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暫且根據初展后的形狀把絹袋分為上下兩部分。沙和銅錢構成絹袋上半部,深藍色絹和棕褐色絹相連部分為絹袋下半部。
在修復室溫度調整為21℃,RH為55% ~59%(局部空間使用加濕器)的條件下初步展平絹袋,從背面的縫痕中尋找信息,并依據幾個關鍵點對絹袋形制進行推斷。
推斷一:在棕褐色絹上發現縫有四個大小不一的三角形褶子,分別編號為①、②、③、④。四塊深藍色絹分別編號為1號、2號、3號、4號(圖4),基本都呈三角形狀。四個褶子的垂直高度不等(也許是因為手工制作較隨意),整塊棕色絹內部沒有拼接縫合的印跡(除了四個褶子外,疑似為一整塊織物),四個三角形都從外圍與褐色絹縫連。根據多年的經驗確定,這塊棕褐色絹一定是袋底,四個褶子正是袋底由平面變立體的實證。
推斷二:通過對絹袋的進一步展平,發現1、2、3、4號三角形基本都呈直角。最完整的1號還等腰,腰長約16 cm,兩腰縫釘在棕褐色織物的一整條邊上,4號三角形較完整的一邊也為16 cm長,與棕褐色織物的另一邊縫合。這一信息說明1號、4號三角形的直角頂點(也正是①和④褶子處)應該是袋底兩個邊的中點。綜合以上信息點,絹袋下半部分的形制已基本明確。即袋底應為正方形,從正方形四邊中點打褶,每一個褶子處對應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縫合(四個三角形大小是相等的),并依此推斷復制出了一個樣品(圖5)。
2.2 絹袋上半部分形制推斷
推斷一:為了較準確地推斷絹袋上半部分的形制,在修復室小范圍達到RH 60%的潮濕狀態下,把緊緊穿過銅錢的紗輕輕抽出,慢慢展開(圖6),發現紗基本呈一塊長50 cm,寬30 cm的長方形(紗穿過錢孔的褶痕與2號三角形相連處的距離為15 cm),中間有較牢固的幅邊縫合痕跡,且與2號三角形依然相連,穿過銅錢左右紗的長度基本一樣。依據1號三角形邊沿上也有明顯的紗殘留推斷(圖4),此塊紗至少與1、2號三角形底邊是縫合為一體的。
推斷二:經觀察,4號三角形邊緣處也殘存有一小段紗的痕跡(圖4),但3號三角形的斜邊已缺失,銅錢另一邊的紗本身也已十分糟朽,所以找不到3號與紗相連的跡象也是正常的。但考慮到整塊紗形狀基本呈直邊方形,依此推斷3、4號三角形底邊也是與紗的另一端相連。銅錢是順著紗的寬度穿過,并放置于中間(其左右紗的長度均等),對絹袋既有裝飾性,又便于提拿。
推斷三:依據1號三角形斜邊上一段約10 cm長的斜紋紗鑲邊推斷(圖7),此鑲邊處與其對稱的另一邊(即3號斜邊中段處,已殘)應是絹袋的兩個開口,便于主人拿取東西。因為根據出土時的同類隨葬品推斷,此絹袋并不是簡單的冥器,而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使用品。既然如此,形制推斷時,其實用性的因素就要考慮進去。
推斷四:從錢孔穿過的紗中,有一條幅邊清晰厚實(圖6),是雙層紗折邊后縫合的結果。依據這一關鍵信息進一步推斷:絹袋上半部應是雙層紗從錢孔穿過后與下半部縫連在一起的,也許不應該像圖6那樣展開成單層。
3 拆線后形制驗證
3.1 絹袋底部形制
待絹袋底部形制基本確定后,便拆開了底部與周邊三角形相連及四個折縫處的縫線,經回潮整平后發現,拆線前對絹袋底部的形制推斷完全正確。棕褐色底部呈規整的正方形,邊長為22 cm。四個褶子縫痕明顯,展開后,基本都在正方形四邊中點位置(圖8)。但因為四個褶子高度有差別,可能會導致后期縫合后的絹袋底部整體形狀不是十分規整。
3.2 三角形拼合
四個三角形雖殘缺、機理變型嚴重,但經過仔細展平后,其尺寸、形狀等卻十分一致(圖9)。驗證了絹袋下半部推斷二的合理性。根據各角上下折迭的痕跡,后期縫合時,應按2→1→4→3號的順序依次縫合即可。
3.3 雙層紗驗證
紗從錢孔中抽出后發現,殘存的紗依幅邊有雙層疊壓的痕跡。用于提拿紗的那枚圓形方孔銅錢,正面有隸書“五銖”字樣,錢孔約8 mm見方。雖然紗已極其脆弱糟朽,但依然塞滿了錢孔,較緊地穿過(圖4)。可見,古人當初縫制絹袋時,需要較多的薄紗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做了一個試驗,把寬25 cm,長30 cm的單層紗穿過錢孔,發現錢孔并沒被塞緊。而換成雙層紗后,錢孔就被塞的很緊了。這一試驗也幫助驗證了絹袋上半部形制推斷四的合理性。
4 絹袋修復
由于此絹袋糟朽十分嚴重,形制確定后,整平和縐絲紗的應用加固是修復的技術難點。
4.1 整平
經過信息采集、檢測分析、形制研究、拆線、清洗、背襯染色等一系列步驟后,便對絹袋的各部分逐一進行平整。此次平整不同于以往的平整工作,棉簽蘸水稍多,就會粘掉織物絲線;干平,又會使織物開裂、斷線。只能使用加濕器,霧化局部空氣,使織物處于半潮濕狀態,輕輕地撥開迭壓、褶皺的織物,根據印染圖案的紋理、針線縫痕等信息,進行調整、拼接。織物變形嚴重,不宜一次性平整到位,可多次修正,分步實施。待理平經緯線后壓放小磁塊約半小時,這一技術還靠經驗、耐心和手感。
4.2 縐絲紗縫合加固技術的應用
4.2.1 關于縐絲紗 考慮到絹袋下半部織物的糟朽脆弱性,不能再承受針線的穿縫力度。因此,擬采用縐絲紗進行縫合加固。其桑蠶絲紗線細度為1/13/15D,紗線捻度14 T/cm,捻向2S2Z,織物經緯密292×255根/10 cm,組織為平紋。縐絲紗是一種較為薄透的絲織物,在歐美等國的紡織品文物保護中應用較為廣泛,尤其對于脆弱絲織品的保護具有非常好的效果[5]。因其通透性很好,雖包覆在了文物上,仍能較清晰地展示紡織品,基本不影響文物的觀展效果,不失為目前較成功的一種修復紡織品文物的方法。近年來,此種織物在中國紡織品修復中的應用也日漸趨多。
4.2.2 縐絲紗的使用方法 薄透的縐絲紗使用前,先要染成與文物底色一致的顏色(圖10)。平整后,若文物背面也需要展示,如雙面繡、立體類薄透紗衣、紗囊等,就用紗直接包覆住文物;若文物背面不需要或無法展示,可選擇與文物風格一致的現代面料作為背襯,再把染好的紗覆在整平后的文物表面。紗像一張細密的網,把織物網在中間,縫針只需從文物裂縫中穿縫即可。縫合在一起的只是紗和背襯或兩層紗,文物所承受的針線穿縫幾率很小。這樣,在相對小的范圍內,把文物固定牢固,與其它鋪針、釘針等針線法比較,它對文物傷害小,安全性高。在一件文物上,可以整體都使用紗包覆,也可局部使用,主要根據文物的脆弱糟朽程度而定。
4.2.3 縐絲紗應用技術要點 目前,中國絲綢博物館對此技術的應用已比較熟練,本絹袋在應用此技術加固時,總結了以下操作要點:1)先把染好的背襯平整在臺面上,用磁塊固定,再把文物平整在背襯上,然后把事先染好平整后的縐絲紗輕輕覆在文物上,待紗的機理調整好之后,壓放磁塊,用同色雙股紗線進行縫合。2)縫合時,為了避免文物走形,先從中間向邊緣過度縫合;先縫大殘缺(無文物)處,再縫小殘缺處。3)只從裂縫處插針,把紗與背襯縫合即可,盡量不從文物上穿縫。4)隨時用針調整下面的文物,使其經平緯直,不能錯位;針距不宜過長,一般有1 mm左右。5)沒有裂紋的地方,可以根據整體情況平行橫向或縱向,以1.5~2 cm左右的行距用行針的方法進行縫合加固。6)若邊角殘缺,也應按文物形制縫釘,使文物形制完整;有針線縫痕的地方,一定沿著原來的縫跡釘一遍,以免剪裁后,紗、背襯和文物散開,走形等(圖11~12)。
4.3 剪裁、縫合、復原
待絹袋各片加固后,便沿著外邊剪裁。剪裁時,注意預留好縫頭,即使在文物缺失處,也一定要裁出形制。縫合時,之前標注的信息就尤為重要了,如:線釘、縫痕、褶印、記錄的數據、圖畫等等。考慮到絹袋上半部分的紗已糟朽殘缺嚴重,展開待其形制確定后,便把它另外保護存放,以便后期研究使用。而本絹袋上半部分擬使用與它風格相近的現代歐根紗進行復原。即把一塊長50 cm,寬30 cm的歐根紗對折成寬25 cm,長30 cm的雙層,一條25 cm的邊與1、2號三角形縫合后,把銅錢穿至中間,放進去另外縫制的支撐物(一個裝有彈力絮的方形軟包),再把另一25 cm的邊與3、4號三角形縫合即可。
4.4 修復效果
把絹袋修復后的整體效果(圖13)與修復前做對比,差異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研究復原了形制。修復前,絹袋的具體形制混亂。黃色紗也許是襯里,整體呈傳統的寶瓶形。但經展開后發現,整片紗與絹袋底部沒有粘連、縫合的痕跡,而是與藍色絹從外圍縫合,且有銅錢穿過,顯然把紗作為襯里不合常理。2)清除了病害。浮于織物表面的白色顆粒狀沉積物、沙石塵土、局部污漬等污染物被粘除,阻止了織物的劣化,增強了織物光澤度,延長了絹袋的壽命。3)矯正理順了織物變形的紋理,并應用現代新材料、新技術有效加固了糟朽脆弱的漢代織物。但依然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附著于絹袋上的歷史信息,提升了絹袋的歷史價值、觀賞價值等。4)總體來講,本絹袋的修復是成功的,對今后同類或同款織物的修復具有借鑒意義。
5 討論
目前,我國紡織品文物的保護修復還處在起步階段,修復理念存在分歧。面對一件脆弱糟朽的漢代織物,是簡單處理后繼續存放起來呢,還是借助現代科技,清除病害,加固保護呢?前者暫時對文物是安全的,但病害處理不徹底,后期會加速其劣化,縮短其壽命;觀展效果欠佳,文物價值體現不到位。正如本絹袋,若不研究復原出形制,普通觀眾只看到的是圖1或圖4的情景。但若采取措施,實施保護修復,對文物是存在很大傷害的。本絹袋在修復過程中,碳化現象就很嚴重(圖3)。但為了延長其壽命,增強其觀賞效果,最大地體現其歷史價值,本工作還是給它動了大的“手術”,觀眾才能較完整地看到兩千年前漢代河西地區人們使用的這件獨特的生活用品。
筆者認為兩種修復理念各有道理,但在工作中具體選擇哪一種,還應根據紡織品文物的糟朽程度而定。若織物太過脆弱,翻動等人為因素對其安全造成毀滅性威脅的話,就不易修復了。畢竟文物是不可再生資源。若雖有傷害,但織物所承受力度尚可的情況下,應該借助新材料、新技術、老經驗等,在試驗的前提下,有針對性、選擇性地實施修復。否則,觀眾看到的只是一堆模糊的織物,其年代再久遠又有什么意義呢?
因此,古代紡織品的修復對相關人員的技術要求很高,對文物如何做到最大的保護,最低的傷害,是文物工作者的重任,是不懈追求的目標。
6 結論
通過一系列的保護修復措施,目前,甘肅省博物館藏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這批紡織品文物均已得到了有效保護。在后期的展存過程中,還需對文物周邊環境進一步治理,尤其是要對展柜、庫房等的溫濕度、光照等進行調控,只有這樣才能讓這批珍貴文物得以長期保護。
致 謝:本次修復工作中,關于絹袋形制推斷等問題得到了中國絲綢博物館樓淑琦、王淑娟、汪自強三位老師的指導和建議;操作過程中樓老師始終在進行技術指導,甚至幾個關鍵步驟都是由樓老師親自上手解決,本工作才得以順利完成,特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