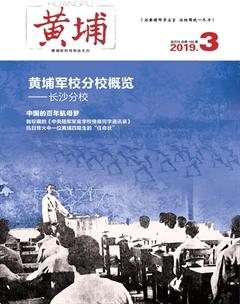我是臺灣人更是中國人(十五)
“臺獨”為迎合日本欺負阿嬤?兩岸統一臺灣才有尊嚴
鳳凰歷史:你周圍哈日的人多嗎,具體有些什么表現?
我:哈日的人當然多,我初中的時候哈日就是主流,最早從《流星花園》開始,里面模仿了很多日本的橋段,把日本的流行文化都引進來了。我覺得哈日是流行文化的喜好,比較強勢、精致的流行文化當然容易被喜歡,多數人喜歡看表面的東西。日本發展得比我們強,當然他制造出來的東西惹人喜歡。可是現在不止是哈日,還“媚日”,已經發展到如果你不認為臺灣是二次大戰戰敗的一方,你就不認同臺灣。過去再怎么搞“臺獨”也不會講這個話,但現在網絡上的留言都是這樣講,如果你認為臺灣不是戰敗國你就是中國的奴隸、走狗,這已經違反人類文明了。
最近“反課綱”的同學竟然脫口而出:慰安婦也不見得就是被迫啊。用這種話來刺痛臺灣人的阿嬤,不關心就算了你還來刺痛,怎么會“媚日”到這程度?李登輝就更鼓勵了,他說釣魚島都是日本的。以前這些話還不會堂而皇之登上主流輿論,現在都給登上了。我周遭還有朋友講,光復有什么好,如果臺灣沒有光復,我們去日本就是走國內線。現在不止哈日,已經變成“媚日”,喜歡流行文化跟已經卷進去站在對方的立場想事情是不一樣的。
初中時我在電視上看到民進黨“臺獨”理論大師林濁水替日本辯護,他說慰安婦也不見得是被迫的,我嚇一跳,“臺獨”理論大師連這種事情都要站在日本的立場來踐踏自己的阿嬤,難道就是因為臺灣要“獨立”得要靠日本撐腰嗎,所以他們對日本必須輕輕放下?我徹底看破“臺獨”的謊言,為了臺灣“獨立”卻要迎合日本欺負自己的阿嬤,兩岸統一才真的還我們尊嚴。當我們站在中華民族的舞臺上,臺灣人就有很大的發言權,臺灣就不是世界的角落而是歷史的中心。
無論中國敗壞還是富強我都是中國人
鳳凰歷史:中國大陸現在處于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但也有一些社會問題,比如腐敗、環境污染等,這些社會問題會不會影響你對大陸、對政府的好感,乃至于動搖你對中國的認同?
我:首先我對中國人的認同與對政府的好感沒有關系。一些臺灣朋友很喜歡講,大陸水準那么差,哪天大陸跟美國一樣你再來叫我們做中國人,不然誰要做。這種話我聽了也感覺心痛。我曾經看過一部大陸改革開放時拍的電影《牧馬人》,電影中朱時茂演的角色和叢珊演的女主角在對話中提到: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丑。中國它敗壞也好,富強也好,那就是我的國家,我就是中國人。如果現在國家是衰敗的、不幸的,我們就想辦法把它救起來,國家現在如果在上升,我們就共襄盛舉,這才是正確的觀念。
黃花崗的烈士們當時所處的中國比現在破敗、貧窮、落后。可是他們從來沒有說我不是中國人。現在中國大陸處于兩百年來最好的時期,當然它有很多不足,可是不能因此就說我不是中國人,而且我們要了解,大陸的問題不是落后造成的,是發展了才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這些問題。臺灣也一樣,80年代經濟開始發展,也出現了公共利益跟私人利益的拉扯,也有環境污染,只是臺灣人口系數比較低,整體規模沒有大陸這么大。我的意思是,不是要用“反華”的帽子來壓制所有不同的批評意見,但還是要警惕別有用心的人把這些問題變成“反華”的言論,我們不能上當。
西方在發展過程當中也碰到同樣的問題,倫敦以前不是霧都嗎?當年他們怎么解決這個問題?他們靠對外侵略,市場不夠了就去搶人家的資源,貨品比不過別人就貿易保護。今天的中國如果這么做,世界會允許嗎?中華民族也不是靠這來強大自己,所以我們要找另外一條路,這條路可能在世界上都沒有過,很有可能是中國人21世紀對世界文明的一個創舉。
兩岸年輕人應多做思想上的交流
鳳凰歷史:對于臺灣年輕人“綠化”的氛圍,你認為大陸應該做些什么來支持統派呢?
我:我覺得大陸的兩岸交流政策不能沒有目標、沒有規劃。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兩岸接觸都很少,一般的交流也很重要。可現在兩岸關系風聲水起,做生意賺錢的人比比皆是,交流都是表面上吃喝玩樂,沒有在思想上做交流。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現在雖然不是革命,但是臺灣歷史沉淀下來的問題想要撥亂反正,需要的力道不亞于革命,怎么可能請客吃飯就能解決呢?
應該做更多思想上的交流,讓大陸的年輕一代、臺灣的年輕一代,還有愛國的學者,學者不一定非要在政權上擁護誰,可是一定要有中華民族的感情、能夠體會中華民族歷史命運。大家一起做個八天七夜、十天九夜的閉門或公開的論壇,可以在大陸的高校舉行,也可以輪流到臺灣高校舉行。這種事情“獨派”做了一大堆,國際上的“反華派”也做了一大堆,都打著“兩岸和平”的旗號,招來兩岸的年輕同學,結果閉門談兩岸沖突的根源,談大陸政府多不好,國民黨也不好,中國人的文明就是落后,西方民主自由至上……越談越差,那怎么會有中國認同?問題在于大陸沒有類似的活動讓大家可以聽一聽大陸是什么看法。
我因為做論文需要所以研究,我才發現原來大陸這么多學者早就已經去解釋了中國模式跟西方的互動問題。臺灣卻一點都不了解,臺灣停留在什么階段?還停留在共產國際的年代,媒體教臺灣年輕人說中共當年怎么搞蘇維埃很可怕,那都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我覺得以后要多做思想的交流,不要怕。很多大陸人怕如果這么快的把一些思想論述告訴臺灣人,會不會有點挑釁,應該要彼此尊重包容。我們同意包容,可是不能包容到根本沒立場。應該負責任地告訴臺灣人大陸的論述是什么,大家直接做思想上的交流,而且不要是學術會議式,要沙龍式的,讓臺灣學生、大陸學生參加思想辯論,不要整天吃喝玩樂,吃五星級飯店那都沒有用,反而還讓臺灣人笑大陸人腐敗,應該腳踏實地,可以吃高校食堂,讓臺灣人體會大陸同學怎么生活,大家彼此聊聊各自家環境怎么樣,這個比較實在。
對兩岸統一有信心但憂心統一的過程
鳳凰歷史:你對將來兩岸統一,以及臺灣年輕人中國觀的撥亂反正,有沒有信心?
我:在物質的層面、在歷史發展層面我有信心,兩岸一定會統一,我憂心的是心理認同跟物質現實的巨大矛盾。兩岸之間的經濟整合包括力量懸殊對比,只要中國大陸決心沒有散掉,統一是遲早的事。所以我們苦口婆心地說臺灣應該去搶統一的主導權,而不是坐等被統一,現在臺灣政客很不負責任,“獨”也“獨”不了,統一也不談,就是吃飽等死。
其實統一不是大家想的那樣可怕的一件事,我們是緩統派,不是急統派,我們覺得應該去談一個真的兩岸都能接受的統一。我們都是中國人,這個要先確定,然而恰恰就是“中國人”這件事在臺灣被急劇妖魔化,乃至于好好談統一的空間也沒有了,這是我最大的憂心。當現實的發展跟心理的認同產生大的矛盾,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就會發生戰爭。我父親是普通臺灣本省人,他都看得很透了,他說如果這樣下去,臺灣的中國觀不能正過來,大陸又不放棄統一,最后只有脅迫下才會統一。
很多人說,大陸經濟發展以后,臺灣人想要有更大的舞臺,就會開始覺醒。我覺得不一定,不要低估了“臺獨”對年輕一代的影響力,他們真有可能像當年支持阿扁的鐵桿“獨派”一樣,肚子扁扁也要投阿扁。就算他覺得臺灣真的在經濟上需要更大的舞臺,也不見得支持跟大陸統一,最后變成只有脅迫才可以逼臺灣上談判桌,講起來非常毛骨悚然,我們不希望走到那一步,還是希望用和平方式來解決問題,可是如果中國觀不能正過來,很有可能最后就會這樣兩敗俱傷。
在這當中我最憂心的是這個統一的過程乃至統一的結果。我的私心是更關心臺灣人,本來臺灣人可以掌握很多話語權,可以有很大發展的空間,我擔心最后臺灣人在統一中因失去時機反被邊緣化,而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也很憂心如果因為這樣造成兩岸兵戎摩擦,也會延緩了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
后記
風掣紅旗凍不翻
2015年2月20日,正值農歷乙未年大年初二,剛經歷人生第一次參選的我,終于在結束選戰后抽得空來,和父親一起借著返鄉過年的機會,走了趟離臺南老家不遠的漚汪文衡殿。
“漚汪”本是平埔語,乃是臺南市將軍區的舊地名,文衡殿則是當地主祀關圣帝君的廟宇。文衡殿的關圣帝君,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末年,由追隨鄭成功的部將攜奉來臺。至于將軍鄉的地名,則是因為施瑯將軍協助清廷攻克臺灣,此地被朝廷封賞給施瑯族人開墾,因而得名。
我和父親特別拜訪漚汪文衡殿,乃是因為從小就聽說漚汪儒俠林昆岡的故事。120年前的乙未年,日軍登陸臺灣,當地文武雙全的秀才林昆岡,便在文衡殿前向關圣帝君起誓,表明自己決心帶領鄉勇義軍,和日軍決一死戰;但假使天命真要臺灣淪于日本,就讓他中頭門銃而死,以免多殺同胞。
后來林昆岡帶領千名壯丁,在學甲竹篙山與裝備精良的日軍苦戰,最終果然身中頭門銃,壯烈犧牲。我和父親走進文衡殿,便見到昔日林昆岡辟建的育英書院遺址,他在這里開設私塾,給鄉人子弟傳授孔孟之道。我看著大殿里香煙裊裊,仿佛也聽見當年朗朗的讀書聲,同時讓我想起了謝晉導演的電影《鴉片戰爭》中的一幕──林則徐走過學堂,望著里頭念著論語的學子,即便西風東漸,中華文化仍是一代又一代,香火綿延。
我在廟門口佇立良久,反復地問自己:像林昆岡這樣的臺灣人,為什么不見了?當媒體總是問我:“你身為臺灣年輕人,又是本省籍的臺南人,為什么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我不禁納悶:“我不過就是繼承了臺南先祖林昆岡敬天法祖的精神,還原了傳統臺灣人本來的面貌,不是嗎?”
當年的林昆岡,見有人在文衡殿前豎起“大日本帝國順良民”的字旗,便大怒將之拔起,并誓死抗日到底;而如今代表所謂本土臺灣人的,卻是頌揚日本殖民、污蔑臺灣慰安婦的李登輝、金美齡之流,這些人稱得上是臺灣人嗎?
我指導成立的臺大學生社團臺大中華復興社,曾經請到抗日先賢丘逢甲的后人丘秀芷老師給我們演講。當時,她娓娓向我們道出她家中的長輩,在經歷日本殖民50年后,仍用客家話繼續給他們教弟子規、三字經,閑暇時即吟唱起唐詩宋詞,就在那一字一句中,堅持傳承了中華文化的道統。就像我臺南老家閩南人的廟里,那些雕梁畫棟的主題,說的也都是傳統中國忠孝節義的故事,何曾有過將荷蘭、西班牙、日本當成我們的文化?“臺獨”為了“去中國化”,硬要把“同心圓”“多元文化”這套史觀搬過來,最后反而斷了自己的根。
在研讀臺灣抗日史的過程中,我讀到了屏東蕭家,包括在乙未年和日軍血戰的蕭光明,及后來又到大陸參加抗戰的第二代蕭道應,而臺灣竟幾乎沒人提起。還有尋找祖國三千里的吳思漢、臺灣義勇隊領袖李友邦、霧峰林家后人林正亨,他們都是英勇參加抗戰的臺灣人,卻在光復后不幸卷入國共內戰下的白色恐怖,魂斷馬場町刑場。林正亨死時才35歲,在牢里留下了絕命詩,最后一句是“吾志未酬身被困,滿腹余恨夜闌珊”。這些英勇抗日的臺灣人,過去被國民黨認為左傾,后來民進黨搞“臺獨”也不提,落得臺灣光復70年的今天,竟只剩下八田與一及“獨派”自我作賤成“戰敗國”的論調,甚至還把“臺灣人參加抗戰”當成笑話。這般情景,又豈只“余恨”二字了得!
我出版這本書,就是要讓大家知道,還有我這樣的臺灣人在這里,除了為歷史作見證,更希望啟發對未來道路的思索。記得最早是在兩年多前,我在整理房間時翻出了中學時代的聯絡簿及作文,后來和身邊的朋友及長輩分享,大家一致鼓勵我應該出書,使我決定將這些資料好好整理出版。
然而,從整理這些手稿開始,到我再從現在的角度為當時的日記寫批注,前后竟拖了兩年時間。其中因為2014年“獨派”發動“太陽花”之亂,我挺身與“獨派”正面斗爭,意外受到了媒體關注,一方面增加了我對公眾發言的機會,一方面卻也拖延了我這本書的寫作進度。尤其后來我投入選舉,直到選后才終于可以認真推動出書計劃,等到2015年12月此書正式在臺灣出版時,我又代表新黨投入了“不分區立委”的選戰。
2015年1月臺灣大選結束后,我趁選后這段稍微較空閑的日子,到大陸拜訪了幾位交情甚篤的朋友,并以這本書的臺灣版作為新年的禮物。結果幾位大陸朋友都一致建議我要將這本書在大陸出版,尤其在民進黨就要執政的此刻,讓大陸同胞知道臺灣還有年輕的統派存在,并告訴他們所謂的“天然獨”是怎么形成的。
因此,我在過完春節后,便緊鑼密鼓地展開大陸版的修訂工作。當然,原有的書稿都還存在,但面對不同背景的讀者群,我仍用心地在每一篇文章中加入應有的背景介紹,讓大陸讀者更容易了解文中所說的臺灣政治事件。此外,我還加入了多篇對于國族認同及“統獨”問題的見解,雖然不像學術文章那樣嚴謹,卻是我多年以來親身體會,并經過多次思考才得出來的結果。
未來我們這些統派在臺灣面對的情勢,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許多大陸網友心疼我,常勸我:如果覺得累,就到大陸來吧!但我絕不會離開臺灣,因為這里是與“臺獨”斗爭的最前線,而反華勢力正是想從其中找到分化中華民族的著力點,在這樣的情況下,臺灣就是中華民族實現復興的前沿戰場。作為一個戰士,我不能夠棄守我的戰場。
我也希望真正追求中華民族復興的朋友,不要只是等待大陸實力的提高,認為到時候兩岸就自然統一,“臺獨”就會解決。我必須再一次嚴正地呼吁:“坐等統一就是坐視‘臺獨”,因為所謂“統一自會水到渠成”的論調,看上去像是自信滿滿,其實是逃避眼前真實存在的問題,低估形勢的嚴峻。大家應該更重視對“臺獨”的思想斗爭,讓更多在臺灣認同統一的人敢于挺身說話,逐漸形成臺灣輿論中的一個堅實的群體,哪怕人數可能并不太多,但思想清晰、明確、堅定,自然就有力量!
想想清朝末年,全中國真正意識到革命的人無疑是鳳毛麟角,但就是這些認識到時代主題的少數人推動了歷史的進程。唐代詩人岑參的一首詩里,有“風掣紅旗凍不翻”這樣的詩句,一直是我特別喜歡的句子。這七字不僅描寫了塞外嚴冬的凜冽景象,更象征了戰士的意志堅定不移,任憑風怎么掣曳,都已經凍到不再飄動。我以這句話自我勉勵,也希望廣大的中華兒女,能夠體會我的心境。
最后,謹以這本書獻給海峽兩岸所有懷抱中國夢的中國人。這百余年來,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道路上,已經有太多太多的人流血犧牲,當中除了抵御外侮,還有中國人之間彼此為不同政治主張而起的爭斗。今天我們好不容易走到了和平發展的年代,更必須對分裂主義抱持警惕,莫再讓反華勢力見縫插針,為的不是制造戰端,而是避免又一個歷史的悲劇。
王炳忠
2016年3月27日凌晨三時,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