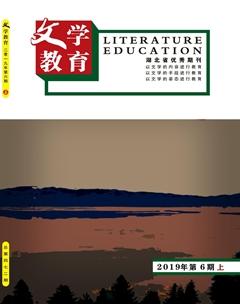來(lái)自天籟的聲音

龍仁青,小說(shuō)家、翻譯家。中國(guó)作協(xié)會(huì)員、青海省作協(xié)副主席、青海省《格薩爾》工作專家委員會(huì)委員、青海省民族文學(xué)翻譯協(xié)會(huì)副會(huì)長(zhǎng)兼秘書(shū)長(zhǎng)。1990年開(kāi)始文學(xué)創(chuàng)作及翻譯。先后在《人民文學(xué)》《中國(guó)作家》《民族文學(xué)》《芳草》《章恰爾》等漢藏文報(bào)刊發(fā)表原創(chuàng)、翻譯作品,多次入選《小說(shuō)選刊》《小說(shuō)月報(bào)》《中華文學(xué)選刊》等及《中國(guó)短篇小說(shuō)年選》《中國(guó)短篇小說(shuō)年度佳作》《中國(guó)短篇小說(shuō)經(jīng)典》等。創(chuàng)作出版有"龍仁青藏地文典"(三卷本)等;翻譯出版有《當(dāng)代藏族母語(yǔ)作家代表作選譯》《火焰與詞語(yǔ)》及《格薩爾》史詩(shī)部本《敦氏預(yù)言授記》等。作品曾獲中國(guó)漢語(yǔ)文學(xué)"女評(píng)委"大獎(jiǎng)等,入圍第五屆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終評(píng)。
周新民:作家走上創(chuàng)作道路,都各有種種原因,請(qǐng)問(wèn)龍仁青老師,有哪些原因促使你走上文學(xué)創(chuàng)作道路?
龍仁青:你的這個(gè)問(wèn)題讓我想起我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師范學(xué)校上學(xué)的時(shí)候,與我有師生之誼的端智嘉先生。他在我的生活中的出現(xiàn),的確是影響我走上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之路的最大緣由。那是在上世紀(jì)80年代中期,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在藏族母語(yǔ)文壇名聲鵲起的端智嘉先生忽然到我校任教。那時(shí)候,恰是改革開(kāi)放的盛世時(shí)代,我國(guó)的文壇就像是百花遇到了陽(yáng)光雨露一般,到處盛開(kāi)和洋溢著文學(xué)之花的多彩和芬芳。那時(shí)候,端智嘉先生已經(jīng)在許多的文學(xué)刊物上發(fā)表了自己的作品,還出版了自己的文學(xué)作品集。他的作品有原創(chuàng),也有翻譯。當(dāng)時(shí),他并沒(méi)有給我所在的那個(gè)班授課,所以我總是逃課跑到他授課的班級(jí)去聽(tīng)課,因此也受到了學(xué)校的一些責(zé)罰。但至今想來(lái),那是我在此生做出的一件最有益的事情,是冥冥之中的某種意志對(duì)我這個(gè)懵懂少年的一種指引。端智嘉先生是一位非常優(yōu)秀的藏族作家,為藏族母語(yǔ)創(chuàng)作做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有人稱其為“藏族的魯迅”。那時(shí)候,他是我和我們同學(xué)共同的偶像,正是由于受他的影響,在那段時(shí)間,我的同學(xué)中出現(xiàn)了許多文學(xué)愛(ài)好者,其中有許多人至今堅(jiān)持文學(xué)創(chuàng)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績(jī)。比如藏族導(dǎo)演萬(wàn)瑪才旦先生,他的電影作品在國(guó)際上屢獲大獎(jiǎng),而他的電影處女作,則是專門(mén)到先生的家鄉(xiāng)青海尖扎取的景。這部電影獲得大獎(jiǎng)后,有記者采訪問(wèn)及選景的問(wèn)題,他說(shuō)他之所以在尖扎拍這部電影,是為了向?qū)Π炎约簬У搅宋膶W(xué)藝術(shù)之路上的先生表達(dá)敬意。我后來(lái)翻譯出版了端智嘉先生的小說(shuō)作品集,我個(gè)人也認(rèn)為,我是對(duì)他的一種報(bào)答或者一個(gè)匯報(bào)吧。至今活躍在藏族文壇上的德本加、扎巴、阿寧·扎西東主也是我的同班同學(xué),當(dāng)時(shí),我們都是端智嘉先生的追隨者。這三位后來(lái)先后獲得了“駿馬獎(jiǎng)”。德本加先生一直在青海牧區(qū)基層從事教學(xué)工作,他創(chuàng)作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寂靜的草原》是安多藏地的首部藏文長(zhǎng)篇小說(shuō),扎巴先生如今是中央民大藏族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博士生導(dǎo)師,扎西東主先生是有著“藏族的《人民文學(xué)》”之譽(yù)的藏文文學(xué)期刊《章恰爾》的常務(wù)副主編。端智嘉先生英年早逝,在他32歲,正當(dāng)文學(xué)創(chuàng)造的盛產(chǎn)期離開(kāi)了人世,為藏族文壇留下了一個(gè)巨大的遺憾。我們依然走在他曾經(jīng)摯愛(ài)的這條文學(xué)之路上,希望他在天之靈有知,看到我們?nèi)〉玫倪@些小小的成績(jī)。
除此之外,我的父親也是我走上文學(xué)創(chuàng)作道路的重要原因。我父親在當(dāng)?shù)厮闶且粋€(gè)知識(shí)分子,他非常看重閱讀,收藏了包括四大名著在內(nèi)的許多書(shū)籍,還為我訂閱了許多報(bào)刊雜志,我家是我出生長(zhǎng)大的那個(gè)小牧村里唯一訂閱報(bào)刊雜志的一家人,記得有《中國(guó)少年報(bào)》《青年文學(xué)》《連環(huán)畫(huà)報(bào)》《遼寧青年》等,還有一份《飛碟探索》。我后來(lái)離開(kāi)我出生的小牧村,到當(dāng)時(shí)的公社小學(xué)去上學(xué),那時(shí)候,我父親也剛好成為公社農(nóng)機(jī)站的臨時(shí)聘用工人,有一間宿舍屬于他,我便住在他的宿舍里,看了他收藏的《呂梁英雄傳》《侍衛(wèi)官雜記》等書(shū)。我在寫(xiě)一篇有關(guān)家鄉(xiāng)的小文時(shí),忽然意識(shí)到,我的父親也是影響我走上文學(xué)創(chuàng)作道路的關(guān)鍵人物。我在之前的采訪中,幾乎沒(méi)有提及這些,今天,向您提及這些,也表達(dá)一下對(duì)我很早就離開(kāi)了我們的父親的深深懷念和感恩之情。
周新民:你出生于青海湖畔鐵卜加草原,談?wù)勀愕耐旰凸枢l(xiāng)青海吧。作家的故鄉(xiāng)和童年生活對(duì)作家創(chuàng)作的影響也很大。
龍仁青:我正要談及我的故鄉(xiāng),您就問(wèn)到了這個(gè)問(wèn)題,心有靈犀啊!我一直覺(jué)得我的故鄉(xiāng)非同一般,雖然它偏遠(yuǎn)、小得只有七八戶人家,但它并沒(méi)有因此少了它的豐饒和厚重。我的故鄉(xiāng)叫鐵卜加,也是青海湖西岸一片草原的名字,有關(guān)這個(gè)地名的含義,大致有兩種說(shuō)法。據(jù)藏文史書(shū)《熱貢族譜》記載,迭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下轄縣)地方的一名男子曾入贅到青海湖西岸的鐵卜加地方,人們便將此男子以他的故鄉(xiāng)“迭部”稱之,他的子女和后裔形成的家族亦被后人稱為迭部倉(cāng)——意即迭部家的人。“迭部”一詞,以環(huán)青海湖安多藏語(yǔ)發(fā)音,音近“鐵卜”,這一發(fā)音逐漸轉(zhuǎn)為“鐵卜加”,地名由此形成。另一種說(shuō)法則在民間廣為流傳:舊時(shí),鐵卜加一帶經(jīng)常有絲綢出土,而這種絲綢上有一種圖案,就像是用人的拇指按上去的指印,而“鐵卜加”則是“一百個(gè)大拇指的指印”之意。我對(duì)后一種說(shuō)法深以為然,因?yàn)殍F卜加的位置,恰好是古代南絲綢之路青海道的必經(jīng)之地,也屬于都蘭吐蕃古墓葬群的邊緣地帶,我國(guó)古代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吐谷渾王朝的核心地帶也是在這里,歷史久遠(yuǎn)。我很小的時(shí)候,就經(jīng)常見(jiàn)到掛在芨芨草上隨風(fēng)飄搖的古代絲綢,這種絲綢被當(dāng)?shù)厝朔Q為“若辛”,意即裹尸布,不讓我們小孩們動(dòng)它,更不允許把它拿回家,認(rèn)為會(huì)沾染上晦氣。如此,每每在放羊的路上看到在風(fēng)中飄搖的“若辛”,我們就像是看見(jiàn)了妖冶的鬼魅正在跳著引誘人們墮入不幸的舞蹈一樣,心生恐懼,遠(yuǎn)遠(yuǎn)躲開(kāi)。
離我出生的小牧村大概一公里左右,有一座古城遺址,是我們小時(shí)候最愛(ài)去玩兒的地方。這座古城在歷史上有明確記載,叫伏俟城,是一個(gè)與我國(guó)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有著交集的地方。是吐谷渾王朝的都城。
家鄉(xiāng)的伏俟城,還是古絲綢之路上重要的的樞紐和要沖。歷史上,沿著河西走廊延伸的絲綢之路河西道在不斷受到諸多地方割據(jù)政權(quán)的阻隔時(shí),吐谷渾王朝卻乘勢(shì)開(kāi)辟了青海道,并著力經(jīng)營(yíng),使這條古道成為了當(dāng)時(shí)國(guó)際貿(mào)易的中心路線。
我就出生在這樣一片草原,這樣的一個(gè)小牧村,我想,在我身上自然而然地沾染上了它所擁有的豐饒和厚重,抑或說(shuō),它在文化上的豐饒和厚重,啟迪了我的慧識(shí),讓我很早就與文字發(fā)生了關(guān)系。
故鄉(xiāng)有著深厚濃郁的歷史,隨處可以看到歷史留下的蹤影:那些在芨芨草尖上隨風(fēng)飄搖的古絲綢,那些在古城遺址中俯首皆是的青色瓦礫等等。有一次,我和幾個(gè)半大小孩在一起玩耍的時(shí)候,甚至還撿到了一只古代兵士的頭盔,記得我們把它放在一個(gè)制高點(diǎn)上,用放牛羊用的爾日加(拋石器)瞄準(zhǔn),擊打它,最后我們?cè)谄渲幸粋€(gè)小孩的帶領(lǐng)下,口中高喊著“沖啊!”(從當(dāng)時(shí)的黑白戰(zhàn)爭(zhēng)片中學(xué)來(lái)),每人懷抱一塊大石頭,沖上前去,幾下就把它砸了個(gè)粉碎。后來(lái)我上了學(xué),懵懂中了解到一些故鄉(xiāng)的過(guò)往,所有這些,便成為我的一種好奇,有了好奇,,就需要探究,而最初的探究便是從閱讀開(kāi)始。記得我父親曾經(jīng)給我一本厚厚的《青海歷史紀(jì)要》,我一遍遍地翻閱這本書(shū),特別是這本書(shū)中有關(guān)茶馬互市、絹馬交易及伏俟城的記載,經(jīng)常在腦子里遙想著故鄉(xiāng)曾經(jīng)的樣子。因此,正如您所說(shuō),影響我最初與文學(xué)發(fā)生聯(lián)系的就是我故鄉(xiāng)的這些點(diǎn)點(diǎn)滴滴。
周新民:談到你小說(shuō)中的一些具體內(nèi)容,我發(fā)現(xiàn),你的作品里處處體現(xiàn)出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情境,比如《光榮的草原》中人與動(dòng)植物的心靈相通、《情歌手》中太陽(yáng)與人的互動(dòng),這就使得大自然不再是簡(jiǎn)單的敘事背景,而是與人物的生命體驗(yàn)緊緊交融在一起。這種“萬(wàn)物有靈”的“神性思維”敘述方式是你的獨(dú)創(chuàng)還是受到民族、宗教亦或是現(xiàn)代流派的某種啟發(fā)?
龍仁青:許多批評(píng)家都提及我的小說(shuō)中的這種“神性思維”,在他們提出這種觀念之后,我才回頭去閱讀或回憶我的小說(shuō)中的一些情景,我好像是恍然發(fā)現(xiàn)了我自己,發(fā)現(xiàn)我在不經(jīng)意之間,在作品中用到了這樣一種思維,這樣一種敘事手法。這樣一說(shuō),其實(shí)也就承認(rèn)了我并沒(méi)有受到任何文學(xué)流派的影響,因?yàn)槲以谛≌f(shuō)中寫(xiě)下那樣的語(yǔ)言的時(shí)候,我根本沒(méi)有意識(shí)到它與某種文學(xué)流派有關(guān)。承認(rèn)了這一點(diǎn),那么是不是也就承認(rèn)了另一種可能,那就是受到了民族、宗教的影響?
“萬(wàn)物有靈”是藏族民間普遍存在的一種認(rèn)知世界的方式。記得小時(shí)候,在春夏季節(jié),草原上多彩的野花競(jìng)相開(kāi)放,一時(shí)間赤橙黃綠,就像是有人把彩虹打碎在了碧綠的草地上一樣。出于孩童天生的好奇,總是要去采摘那些野花,大人們便會(huì)阻止我們,他們說(shuō),那是大地的頭發(fā),“如果有人也像你一樣拔了你的頭發(fā),你不疼嗎?”于是,我們便不再去采摘野花。這似乎只是一種習(xí)俗,但它的確與民族、宗教有關(guān)。或許,我這樣的“神性思維”,就來(lái)自于我曾經(jīng)生活的地方,那里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
評(píng)論家段懷清先生曾經(jīng)為我寫(xiě)過(guò)一篇評(píng)論,題目是《當(dāng)孤獨(dú)成為一種審美》。小時(shí)候做為一個(gè)小牧童,的確體驗(yàn)過(guò)太多的孤獨(dú)。在荒蕪闊大的草原上,一個(gè)人放牧著牛羊的時(shí)候,與牛羊說(shuō)話,與野花、鳥(niǎo)雀、螞蟻說(shuō)話,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說(shuō)穿了其實(shí)便是自言自語(yǔ)。自言自語(yǔ),應(yīng)該是每一個(gè)牧人的習(xí)慣吧,或許可以說(shuō)是每一個(gè)孤獨(dú)的牧人的一種疾病。我的作品,便是在不經(jīng)意之中,暴露了我也患有這種疾病。
周新民:毫無(wú)疑問(wèn),“神性思維”成為了你創(chuàng)作的一種很重要的思維模式。你生活在藏區(qū),我想了解下你和宗教的遭遇。宗教是否對(duì)你的人生或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產(chǎn)生影響?
龍仁青:我出生于上世紀(jì)60年代中期,出生的地方的確是名副其實(shí)的“天高皇帝遠(yuǎn)”,但這并沒(méi)有阻擋住那個(gè)年代的風(fēng)吹到那里。記得我在四五歲的時(shí)候,我的父親被從家里拉出去,在當(dāng)時(shí)我們叫做倉(cāng)庫(kù)的一座平房前接受批斗,說(shuō)他是保皇派。我至今記得當(dāng)我看到父親站在大家面前,他的頭被幾個(gè)人深深按下去的的樣子時(shí)的驚恐不安,那也是我第一次聽(tīng)到我的心跳撞擊在我的耳膜上發(fā)出的咚咚聲。我也記得,與保皇派相對(duì)應(yīng)的,還有一個(gè)詞,叫八一八,這些都是當(dāng)時(shí)紅衛(wèi)兵的名字,這些詞以漢語(yǔ)的發(fā)音勢(shì)不可擋地到達(dá)了我的故鄉(xiāng),把一群人分成了勢(shì)不兩立的兩個(gè)部分,藏族牧民們并不明白這兩個(gè)詞的實(shí)際含義,但他們根深蒂固地記住了這些詞匯的漢語(yǔ)發(fā)音。多年以后,我考上了縣城的中學(xué),我乘坐長(zhǎng)途客車(chē)離開(kāi)我的家鄉(xiāng)到縣城去上學(xué),途中要路過(guò)一個(gè)叫一五一的地方。這個(gè)地方的命名,是因?yàn)檫@里離西寧的距離是151公里。我至今記得,在我乘坐的長(zhǎng)途客車(chē)上,有一個(gè)年老的藏族牧民,他記不住他要去的地方的名字,但他依然記著那個(gè)紅衛(wèi)兵派別的名字,于是他告訴長(zhǎng)途客車(chē)伺機(jī),他要去八一八!可見(jiàn)這個(gè)名字是那樣頑固地盤(pán)踞在他的腦際!當(dāng)時(shí),客車(chē)司機(jī)即刻知道了牧民要去的地方,我至今記得他開(kāi)著玩笑給牧人解釋的情景。
我也記得我第一次見(jiàn)到唐卡的情景。那是我大概在上小學(xué)三年級(jí)的時(shí)候。一個(gè)牧戶家偷偷藏在家里的佛教用品被人發(fā)現(xiàn)了,被沒(méi)收后,展覽在公社供銷(xiāo)社前面的土臺(tái)子上讓大家觀看,以此來(lái)批判這個(gè)牧戶的頑固不化和死不改悔。我是在學(xué)校組織下和同學(xué)們一起去觀看的,當(dāng)我看到其中一幅唐卡時(shí),那艷麗的色彩立刻震撼到了我。我記得當(dāng)時(shí)是冬天,家鄉(xiāng)的大地只剩下蒼茫的灰黃色,而那幅唐卡卻鮮亮無(wú)比,好像是一片灼灼燃燒著的彩虹,整個(gè)大地因?yàn)樗拇嬖诙@得汗顏,我的眼睛被那幅唐卡點(diǎn)燃了,我看到那幅唐卡上的女神那樣妖嬈多姿,在這灰黃色的冬天里坦然而一覽無(wú)遺地仰臥在那里,有一種招搖的樣子,她讓這個(gè)冬天顯得灰頭土臉,抬不起頭來(lái)。
在您問(wèn)我有沒(méi)有宗教信仰的時(shí)候,我不厭其煩地說(shuō)起這些往事,是想告訴您,在我的孩童時(shí)代,其實(shí)我并沒(méi)有經(jīng)歷過(guò)宗教的儀式、活動(dòng)什么的,而就在我慢慢長(zhǎng)大,要離開(kāi)我的故鄉(xiāng)去縣城上學(xué)的時(shí)候。適逢改革開(kāi)放,宗教信仰政策全面開(kāi)放,我的故鄉(xiāng)幾乎在一夜之間便發(fā)生了改變,小小的寺廟里重新有了僧侶,經(jīng)幡飄搖在所有高一點(diǎn)的山頭上,家家戶戶的房后都有了煨桑臺(tái),每一個(gè)老人都手持佛珠,那樣稔熟地誦頌著佛經(jīng)。我相信,我的故鄉(xiāng)一直就氤氳在一片藏傳佛教文化的氛圍之中,只是在那些特殊年代,故鄉(xiāng)從外在的形式上收斂了自己虔誠(chéng)的樣子,內(nèi)心里卻深深地掩藏著自己的信仰,那信仰便是一堆干柴烈火,單等著一把火的點(diǎn)燃,一旦點(diǎn)燃,便會(huì)獵獵燃燒。而如今,它正在熊熊燃燒。每每回到故鄉(xiāng),看到這些,我就會(huì)想起第一次看到唐卡的情景,那幅唐卡曾經(jīng)在瞬間讓一個(gè)冬天灰飛煙滅。
我曾經(jīng)說(shuō),贊美故鄉(xiāng),應(yīng)當(dāng)是文學(xué)的義務(wù)之一。我會(huì)一點(diǎn)點(diǎn)地寫(xiě)下我在故鄉(xiāng)的這些過(guò)往。
周新民:我注意到你的小說(shuō)經(jīng)常運(yùn)用“孩童視角”,比如《奧運(yùn)消息》借小次洛的目光鋪展開(kāi)隱藏在背后的歷史事件奧運(yùn)會(huì),《遙遠(yuǎn)的大紅棗》利用扎洛限知的所見(jiàn)所聞推測(cè)了可能存在于父輩中的愛(ài)恨情仇,這種視角使得某些重大的主題得以消隱,這是否是你的有意為之?
龍仁青:我寫(xiě)兒童生活的小說(shuō)比較多,我曾經(jīng)在幾篇小說(shuō)里塑造了一個(gè)叫次仁的小牧童,我甚至設(shè)想過(guò)以這樣一個(gè)人物去寫(xiě)一系列兒童題材小說(shuō),《奧運(yùn)消息》便是我設(shè)想中的這個(gè)系列小說(shuō)中的一篇。這些小說(shuō)中的次仁這一人物身上,有許多我自己孩提時(shí)代的影子。寫(xiě)這些小說(shuō)的時(shí)候,我讓自己的思緒回到我的童年時(shí)代,讓這個(gè)叫次仁的小牧童在我的腦際活起來(lái),讓他指揮著我敲鍵盤(pán)的手,寫(xiě)下那些與我的童年有關(guān)的文字。我沒(méi)有刻意運(yùn)用“孩童視角”,也沒(méi)有要去消隱重大題材的意思。我有時(shí)候也在想,我之所以能夠這樣去寫(xiě)小說(shuō),是因?yàn)槲以谀撤N程度上還保留了一些兒童思維,是一種不成熟的表現(xiàn)。
周新民:你的小說(shuō)敘事節(jié)奏追求“慢”,如《牧人次洋的夏天》等。你在訪談錄中也提到你個(gè)人的生活節(jié)奏也追求“慢”。你說(shuō)你不會(huì)像其他作家那樣每天一如坐禪、修行一般地面對(duì)寫(xiě)作,而是會(huì)選擇去行走。能否談?wù)勥@種追求“慢”的寫(xiě)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于你而言意味著什么?
龍仁青:說(shuō)一件事情吧。記得大概是北京奧運(yùn)會(huì)不久,我去了一趟北京,鳥(niǎo)巢是自然要去看的。當(dāng)我買(mǎi)了門(mén)票,守候在門(mén)外等著進(jìn)去參觀的時(shí)候,在我面前攢動(dòng)的人頭以及從這些人頭上空飄浮而來(lái)的嘈雜的人聲忽然讓我感到了慌張不安。他們用各自的方言大聲地說(shuō)著什么,看上去心不在焉又焦慮不安。他們似乎對(duì)參觀鳥(niǎo)巢之事毫不在意,但又是那樣的急躁,甚至有些慌亂。我知道,這并不是我有所謂密集恐懼癥,在我還是個(gè)牧童的時(shí)候,我經(jīng)常蹲守在蟻巢前,看著忙亂的螞蟻們?cè)谙伋怖镞M(jìn)進(jìn)出出,一看就是很長(zhǎng)時(shí)間。那時(shí)候,我喜歡忽然搬起靜臥在草原上的一塊石頭,往往,石頭下便會(huì)是一個(gè)螞蟻的大家族,就在石頭被搬離的瞬間,所有螞蟻便開(kāi)始行動(dòng),把它們忽然被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蟻卵迅速搬到安全的地方,它們看似忙亂,毫無(wú)章法,但就在很短的時(shí)間里,它們就完成了搬走蟻卵的工作,不大一會(huì)兒,就看不見(jiàn)一個(gè)蟻卵了。有一次,我的這一行為被我母親發(fā)現(xiàn),那一天,她狠狠揍了我一頓,她說(shuō),如果有人忽然拆了咱們的家,你不傷心嗎?從此,我再也不去搬掉那些靜臥在草原上的石頭,但我依然迷戀蹲守在蟻巢前,看它們的協(xié)同合作,看它們勤勞地忙亂。之所以說(shuō)這件事情,一是想證明我并沒(méi)有密集恐懼癥,二是,我從同樣的忙亂里看到了不一樣,我從螞蟻身上看到的是一種從容不迫,而從人群身上,看到了一種浮躁不安。我是想說(shuō),我看到了快與慢的辯證法,其實(shí),快與慢,并不是時(shí)間意義上的那種速度,而是一種心態(tài),從容地面對(duì),就是一種慢,浮躁地處置,就是快吧。只要從容了,不論是在現(xiàn)實(shí)中還是在文學(xué)里,四處都會(huì)是精彩的風(fēng)景。
周新民:你說(shuō)的很對(duì),“慢”是一種人生態(tài)度。我發(fā)現(xiàn),你早期的小說(shuō)作品如《小青驢馱金子》等大都描寫(xiě)的是單純的草原上的藏民族生活,和煦溫暖中帶著淡淡的憂傷,那是在工業(yè)時(shí)代來(lái)臨下對(duì)草原原初的傳統(tǒng)遭到破壞的擔(dān)憂與無(wú)奈。而近期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如《巴桑寺的C大調(diào)》、《咖啡與酸奶》《看書(shū)》和《鳥(niǎo)巢》等則開(kāi)始有意識(shí)地將藏民族生活地域環(huán)境的描寫(xiě)從草原牧場(chǎng)向城鎮(zhèn)都市轉(zhuǎn)移,在探討藏民族傳統(tǒng)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同時(shí),亦開(kāi)始探究在當(dāng)代城鎮(zhèn)化與都市化的進(jìn)程中新藏民更具有時(shí)代感與當(dāng)下都市感的文化心理。這種寫(xiě)作上的“轉(zhuǎn)型”與時(shí)代同步的快速發(fā)展之間有什么必然的聯(lián)系?
龍仁青:這個(gè)問(wèn)題可能涉及什么是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問(wèn)題吧。記得曾經(jīng)與70后作家徐則臣有過(guò)一次對(duì)談,他是我的小說(shuō)《一雙泥靴的婚禮》的責(zé)任編輯。在與他對(duì)談時(shí),他特別提到了這篇小說(shuō),他認(rèn)為這篇小說(shuō)有一種懷舊的敘事口吻,也就是您所說(shuō)的那種對(duì)業(yè)已失去的東西抱有一種不甘的心態(tài)。則臣認(rèn)為,這種對(duì)田園牧歌似的以往的過(guò)度渲染,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一種疏離。我承認(rèn)他的說(shuō)法,也一直在思索這個(gè)問(wèn)題,那就是,如何使作品直面現(xiàn)實(shí),不去有意遮蔽現(xiàn)實(shí)中的真實(shí)存在,不去營(yíng)造出一種虛幻的現(xiàn)實(shí)。我是一個(gè)攝影愛(ài)好者,也經(jīng)常到草原牧場(chǎng)去采風(fēng)、攝影,每每面對(duì)自然山水,為了追求畫(huà)面的唯美,就會(huì)有意躲開(kāi)一些東西,比如空中橫七豎八的電線、地上水泥的或者鋼鐵的電線桿、以及一些現(xiàn)代化的建筑等等。問(wèn)題是,這些東西的存在已經(jīng)是一種現(xiàn)實(shí),它們之所以存在,是因?yàn)楫?dāng)今牧民的生活已經(jīng)離不開(kāi)它們了,各種家用電器已經(jīng)是牧民們最日常的需要。因此,就草原牧場(chǎng)來(lái)說(shuō),它們已經(jīng)與自然山水渾然一體,共同構(gòu)成了現(xiàn)代化畜牧業(yè)的一種情狀。加上我國(guó)城鎮(zhèn)化建設(shè)的大踏步發(fā)展,城市與鄉(xiāng)村、牧場(chǎng)的差距正在逐漸縮小,一個(gè)具有這個(gè)時(shí)代特色的新的草原牧場(chǎng)已經(jīng)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做為一個(gè)寫(xiě)作者,就要去描寫(xiě)我們所看到的火熱與掙扎、歡樂(lè)與痛苦。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我并沒(méi)有轉(zhuǎn)移我要描寫(xiě)的地域環(huán)境,我的筆觸依然在描摹我所熟悉的草原牧場(chǎng)。正如您所說(shuō),我只是看到了這片地域與這個(gè)時(shí)代的必然聯(lián)系。
周新民:你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就創(chuàng)作而言,我始終感謝生活對(duì)我的特別賜贈(zèng),不論是草原還是城市,生活以它的豐富性和不斷的變化,昭示我真誠(chéng)面對(duì)生活,并寫(xiě)好自己的東西。我越來(lái)越欣喜地看到我的寫(xiě)作可能會(huì)展示出的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不會(huì)受到我的族屬的影響,我也不會(huì)站在任何一種族屬的觀念上去看待問(wèn)題。”我對(duì)這種超越族屬觀念進(jìn)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很感興趣,能不能就此點(diǎn)展開(kāi)更詳細(xì)的闡釋?
龍仁青:我在青海生活、寫(xiě)作。說(shuō)起我的故鄉(xiāng)青海,它的地理位置和地域文化特色卻顯得有些模棱兩可,令人尷尬——在人們的印象里,它是邊疆,但從中國(guó)地圖去看,它幾乎處在中心的位置;在人們的印象里,它是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但它是一個(gè)省,而不是自治區(qū)。
青海是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的過(guò)渡帶,是農(nóng)耕文明與游牧文化的交界地,是外流區(qū)域與內(nèi)流區(qū)域、季風(fēng)區(qū)與非季風(fēng)區(qū)的分界線,這里因此民族眾多,文化多元,它幾乎囊括了與它接壤的所有地區(qū)的文化特色,也因?yàn)榍∏∈沁@個(gè)原因,過(guò)多的特色卻讓它顯得毫無(wú)特色。就拿它的省會(huì)城市西寧來(lái)說(shuō),這座城市生活著35個(gè)民族的人群,早在漢代時(shí),這里已經(jīng)開(kāi)始了大規(guī)模的農(nóng)耕生產(chǎn),這里曾經(jīng)是一座叫做青唐城的吐蕃政權(quán)的所在地,藏族先民唃廝啰的后裔們依然生活在這里,這里也聚集著眾多的穆斯林民族,他們居住在城東區(qū)的東關(guān)大街一帶,幾乎占據(jù)了這座城市的四分之一,這里還有土族、撒拉族等青海獨(dú)有民族。但是,西寧至今沒(méi)有一座地標(biāo)性的建筑——建筑做為用外在形象呈現(xiàn)一個(gè)地區(qū)特色文化的存在,西寧卻沒(méi)有任何鮮明的文化去用建筑來(lái)體現(xiàn)。這種地理位置和地域文化上的尷尬,也體現(xiàn)在青海作家以及他們的作品之中——在青海周邊的西藏、寧夏、新疆等自治區(qū),以及甘肅、陜西等省份,幾乎都有自己相對(duì)單一而又特色顯著的文化,比如西藏的藏文化、寧夏的穆斯林文化、甘肅與陜西的農(nóng)耕文化等,這種顯著的民族地域文化的滋養(yǎng),讓這些地區(qū)擁有了從各自文化中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作家,而這些作家的身上,在他們的作品中,明顯沾染著他們各自的文化色彩,比如,陳忠實(shí)、賈平凹、扎西達(dá)哇、次仁羅布、石舒清、李進(jìn)祥等,他們和他們的作品就這樣帶著各自民族地域文化給他們的滋養(yǎng),在中國(guó)文壇上樹(shù)起了他們自己的形象。而青海的作家,卻很尷尬,他們面對(duì)的是一個(gè)龐大的多元文化體系。
其實(shí),青海的文化特色應(yīng)當(dāng)就是多元,這就要求青海的寫(xiě)作者們要博學(xué),要站在一個(gè)高度上,以一種客觀、理解、包容、欣賞的眼光去看待自己身邊的任何一種文化,剔除偏執(zhí)和文化中心主義立場(chǎng),融會(huì)貫通,兼容并蓄,去描寫(xiě)包羅萬(wàn)象、豐富多彩的青海文學(xué)。
周新民:繼阿來(lái)的《塵埃落定》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之后,一批努力探索小說(shuō)藝術(shù)的藏族作家?jiàn)^力筆耕,次仁羅布的短篇小說(shuō)《放生羊》獲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江洋才讓的《康巴方式》和四川作家尹向東描寫(xiě)康定草原的小說(shuō)異軍突起,在以漢語(yǔ)寫(xiě)作為主的當(dāng)代文壇中綻放出一片又一片的碩果。你如何看待這一現(xiàn)象?
龍仁青:比起藏族作家的漢語(yǔ)寫(xiě)作,我似乎更關(guān)注或者說(shuō)在意藏族作家們的母語(yǔ)寫(xiě)作。這可能與我剛剛開(kāi)始進(jìn)入文學(xué)寫(xiě)作的時(shí)候,便是用藏文寫(xiě)作有關(guān)。面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我忽然發(fā)現(xiàn),您羅列的這些作家恰好涵蓋了藏族三大方言區(qū),抑或說(shuō)藏族三大文化區(qū),從這一點(diǎn)去看,藏族作家的異軍突起,也體現(xiàn)在不同區(qū)域作家們的共同努力上。近年來(lái),康巴地區(qū)的作家們很活躍,他們以他們大量的作品以及作品所體現(xiàn)出來(lái)的上乘的質(zhì)量,造就出了一個(gè)“康巴作家群”。這一現(xiàn)象已經(jīng)引起整個(gè)文壇以及評(píng)論界的關(guān)注。其實(shí),在藏地,在三大方言區(qū)的衛(wèi)藏和安多,一批有著本土地域特色的創(chuàng)作隊(duì)伍也在成長(zhǎng)壯大。以西藏為例,近年來(lái),西藏的母語(yǔ)寫(xiě)作異軍突起——再次借用一下這個(gè)成語(yǔ)——?jiǎng)?chuàng)作成果豐碩,就我所知,近兩年來(lái),西藏母語(yǔ)作家創(chuàng)作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就不下十部,其中多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一經(jīng)出版,就引起了藏族母語(yǔ)文壇以及讀者的強(qiáng)烈反響。而以青海為主的安多藏區(qū),卻涌現(xiàn)出了一批漢藏雙語(yǔ)寫(xiě)作的作家,這些作家們不僅在寫(xiě)作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jī),比如梅卓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與詩(shī)歌創(chuàng)作、萬(wàn)瑪才旦、拉先加的短篇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等,他們的漢藏/藏漢翻譯方面更是成就斐然。就我所知,2013年以來(lái),青海民族文學(xué)翻譯協(xié)會(huì)就組織翻譯了不少于20部的母語(yǔ)作家作品,并完成了由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主持的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翻譯工程“漢譯民”項(xiàng)目約800萬(wàn)字的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工作。
周新民,湖北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二級(jí)),博士生導(dǎo)師。國(guó)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jì)劃(萬(wàn)人計(jì)劃)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領(lǐng)軍人才、全國(guó)文化名家暨四個(gè)一批人才(理論界)、國(guó)家百千萬(wàn)人才工程人選、國(guó)家“有突出貢獻(xiàn)中青年專家”、國(guó)務(wù)院特殊津貼專家。兼任中國(guó)新文學(xué)學(xué)會(huì)副會(huì)長(zhǎng)、《新文學(xué)評(píng)論》副主編、武漢作協(xié)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協(xié)會(huì)全委會(huì)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