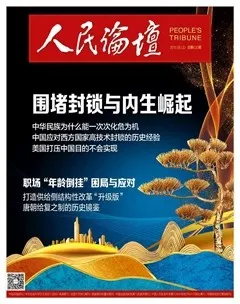中國如何應對西方國家政治和經濟制裁
馮維江
1989年后,以美國為首的眾多西方國家對中國發起大范圍、廣領域、長時間的政治經濟制裁。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宣布五項多方位制裁中國的行動,由此拉開了美國單獨及聯合西方國家制裁中國的序幕。這次制裁讓改革開放的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美國、加拿大、歐共體12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等幾乎所有西方發達國家都參與了制裁。“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盡管形勢嚴峻、外力強橫,但中國并沒有被嚇住,更沒有被壓倒,而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保持定力、繼續開放,外交上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經濟上用利益分化西方陣營,逐步打破了制裁,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推進確保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首先,中央對國際形勢有準確的判斷。中國政府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道路的大方向有堅定的信心,立足“做好自己的事”這個基礎來應對外部沖擊。面對制裁,鄧小平同志提出,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抓住機遇、有所作為”。他還在不同場合表示,“現在國際輿論壓我們,要泰然處之”;“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不了的。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戰爭我們并不怕”;“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鎖、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
其次,做好中國市場規模的文章。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出現持續低迷的情況,歐洲貨幣體系出現問題,日本更是出現股市暴跌和經濟下滑交織的狀況。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十一億多人口巨大規模的單一市場對它們的吸引力是難以抗拒的。中國也敏銳地把握住了西方國家愿意與中國發展合作的積極信號。日本等國雖然也加入制裁中國的行列,但較早表現出松動跡象。1989年7月,時任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就表示,“日本不同意制裁中國”。與日本相似,德國在對華制裁上也比較謹慎。西班牙、意大利等對制裁中國的態度也相對比較消極。1990年開始,中國與部分西方國家的關系出現積極變化。1990年1月和6月,時任國務委員鄒家華和李鐵映應邀訪問日本,7月日本宣布正式恢復對華官方日元貸款。1990年10月,歐共體外長會議決定取消對華限制措施,恢復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對華正常關系。1991年,日本首相、英國首相和意大利總理先后訪華。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系逐漸正常化。
再次,通過多種方式與其他國家積極建立外交關系。面對西方制裁,中國重點針對發展中國家、周邊國家、前蘇聯地區轉軌國家等,開展全方位積極主動的外交工作。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國領導人密集出訪,積極拓展外交關系,同時也接待幾十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的友好訪問。1990年與沙特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同年,中國恢復了與印度尼西亞的外交關系。中國與東盟國家關系也全面發展,領導人頻繁互訪。從1991年到1992年,中國實現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1992年8月,中國與韓國決定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除積極主動開展政府外交活動外,中國還借助1990年在北京舉辦第十一屆亞運會的契機,通過主場外交、公共外交,集中展示中國文化魅力、提升國際聲望。通過在國際社會廣交朋友,中國并沒有因為西方的集體制裁而陷于孤立,而是獲得了應對制裁的更大戰略自由度。
最后,應對美國“兩面性”的對華政策,積極引導鼓勵合作方向。在美國國內,一方面其國會積極敲打政府,敦促其對華采取強硬措施,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及私人部門不愿意放棄中國市場,希望加強與中國的合作。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在宣布制裁中國后不到一個月,就幾次私下向中方傳遞口信,表示自己重視中美關系,對中國的制裁只是國會壓力下的被迫之舉。在國際上,美國一方面糾集西方國家制裁中國,另一方面在柬埔寨問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誘發海灣危機等問題上,又需要同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中國的支持。在美方要求下,中美在柬埔寨問題會議等第三方場合,借商議其他問題討論如何改善雙邊關系。1990年11月,美方邀請中國外長錢其琛正式訪美,并在錢訪美期間安排總統會見。此舉打破了美國中止高層互訪的制裁。1993年11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美國西雅圖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并與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正式會晤,標志著美國對華制裁政策基本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