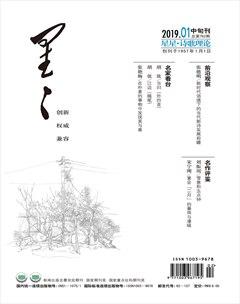西方繪畫札記:“畫肉”,以及“成為一臺機器”
陽飏
弗洛伊德:“畫肉”
盧西安·弗洛伊德(1922—2011)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認為人類最基本的本能有兩類:對生的本能和對死亡的恐懼。生的本能包括性欲本能與生存本能,所以性欲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特性,也是分析人的本質的重要方式。爺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沖動是人一切心理活動的內在動力的理論,在孫子盧西安·弗洛伊德的繪畫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弗洛伊德用傳統的寫實繪畫,表達了當代人精神與肉體的真實形態。
他想通過裸體揭示更深層次的內容。他特別喜好對一些特異體型人物的描繪,他不需要模特兒擺出所謂美的姿勢,而是隨意躺著、睡著、叉開腿坐在沙發上,他要表達的是毫無掩飾的暴露。
弗洛伊德習慣站著畫畫。在畫室里,他趿拉著拖鞋、半裸著身子,一站就是10多個小時。其生前好友、英國泰特美術館館長說,畫室中至今還留著幾幅未成品,“他總是保持著3至4幅作品同時在架上的活躍創作狀態。”
《破布旁的立像》用冷靜的筆觸、犀利的目光,向我們展現了一個女裸體。女裸體身后的破布仿佛要倒塌下來一般,給人一種危險的暗示。他的肖像畫不僅僅是對人體的描摹,更是對人的內心的深刻揭露。
弗洛伊德的畫作中看不到肢體美,無論男性還是女性,肥胖臃腫的身軀,下垂的皮膚和耷拉的乳房,疲憊無力的人體,好似一個個破舊的物體被隨意棄置在那兒。
《熟睡中的保險顧問》蘇·蒂利當時體重250多斤,正可謂“投其所好”。人體是弗洛伊德一生探尋和表現的主題,一具具活生生的血肉之軀一絲不掛地呈現在觀眾的眼前,他更想畫的是皮肉之下的靈魂。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請弗洛伊德為她畫肖像。在他筆下,眾生平等,女王也不例外。《伊麗莎白二世》肖像畫公開后,一片嘩然,因為在這幅肖像畫上,女王即使頭戴象征最高權威的皇冠,但在弗洛伊德眼里,她首先是作為一個81歲高齡的老婦人而存在,找不到絲毫美化的意味。
《每日郵報》說畫像中的女王精力耗盡;《鏡報》以“表情冰冷”形容;《太陽報》則指責這幅作品是對女王的“肆意歪曲”。
弗洛伊德回憶,當年作畫時,他曾試圖激怒女王,但沒成功:“她不太熱情,但我喜歡她那樣。”
在他筆下,沒有美,只有真實的肉體。
除了裸還是裸,除了肉還是肉。人體在古典繪畫里是力量和美的化身,但弗洛伊德更像是一個用眼睛和畫筆去解剖人體的外科醫生。
弗洛伊德畫各種各樣體態的男人和女人,他曾經說:“我只在我生活、熟悉的房間里,和我感興趣的、我在乎的人合作。”他所畫的是自傳性質的,作畫對象只是些熟人和他所感興趣的、所關注的人。如他的母親,以她的形象為題材的畫作就有多幅,幾個女兒也當過他的模特兒。
他承認自己是個“被壓抑的‘縱火狂”。生活中他是個性急的人,遠遠看到快要靠站的公共汽車也會狂奔著去追趕。
弗洛伊德說,自己閑暇時愛做白日夢,喜歡賭博,也酷愛舞蹈。幾年前,他曾對朋友遺憾地說:“再沒時間跳舞了,對賭博也漸漸失去了興致,因為現在我可以承受輸錢的打擊了。”
弗洛伊德對女人有著永遠的激情。英國《周日電訊》報道,傳聞弗洛伊德有超過40個私生子。
2007年10月,弗洛伊德獲得騎士勛章,在頒獎典禮上合影時,他在攝影師按下快門的同時出人意料地把身子扭了過去,并且用手遮住了臉。
對于弗洛伊德而言,“畫肉”——這個形容真是恰如其分的說明。
沃霍爾:我想成為一臺機器
安迪·沃霍爾(1928-1987)是上世紀60年代興起的波普藝術畫家。60年代,對于中國人來說是挨餓的記憶,我想不出來,用波普藝術表現挨餓會出現什么效果——畫一大堆包谷面窩窩頭,或者一根根排列整齊的油條?沃霍爾是在畫完他的成名作《綠色的可口可樂瓶子》之后,又制作了《瑪麗蓮·夢露》。食色,欲也。沃霍爾灌了一肚子的可口可樂,又開始打美女的主意了。
“波普”這個詞最早出現在英國畫家漢密爾頓《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別致,如此動人?》這幅畫中,漢密爾頓給波普所下的定義是:通俗的(為廣大觀眾設計的),短暫的(短時間解答的),便宜的,大批生產的……
《瑪麗蓮·夢露》以好萊塢性感影星瑪麗蓮·夢露的頭像,作為畫面的基本元素,一排排地重復排立,色彩簡單、整齊單調的一個個夢露頭像,故意以黑版印刷的低劣質量和彩版印刷的錯位效果,強調了美國社會大眾趣味正像這幅畫一樣,被大批量地粗制濫造出來,直到你感到厭倦為止,突出了一種嘲諷與冷靜,反映出現代商業化社會中人們無可奈何的空虛與迷惘。沃霍爾描繪的簡單清楚而反復出現的東西,都是現代社會中最令我們熟悉視牢記的形象符號,重要的是,他打破了永恒與偉大的界限。
沃霍爾可謂是一個獨具美國價值的藝術家。
沃霍爾被譽為是畢加索之后一位最有價值的前衛藝術家,哪怕是一卷廁紙,只要蓋上他的印章,立刻身價百倍時髦起來。
羅森伯格《現代藝術觀念》評價:“麻木重復著的坎貝爾湯罐組成的柱子,就像一個說了一遍又一遍的毫不幽默的笑話。”
他偏愛重復和復制。“我二十年都吃相同的早餐。”他解釋說:“我想這也是反復做同一件事吧。”對于他來說,作品全是復制品,他就是要用無數的復制品來取代原作的地位。他有意地在畫中消除個性與感情的色彩,不動聲色地把再平凡不過的形象羅列出來。
沃霍爾有一句名言:“我想成為一臺機器。”
羅伯特·休斯《新藝術的震撼》評論說:“因而它能引起無限的好奇心——是一種略微有點可怕的真空,需要用閑聊和空談來填滿它。”
沃霍爾畫中特有的那種單調、無聊和重復,所傳達的是某種冷漠、空虛、疏離的感覺,表現了高度發達的商業文明社會中人們冷漠的感情。
波普藝術改變了世人評價世界、生活和藝術的方式,并以此證明生活和藝術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藝術不再是少數人的專用,而應該屬于普通大眾。
令人驚訝的是,早在俄國十月革命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初期,就有先鋒的俄羅斯藝術家們決意要創造“一種5戈比的藝術”——便宜,每個人都可以享受的現代藝術。而最終的結果是,社會主義藝術家的愿望,在所謂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得以實現。這是戲謔還是安慰?是必然還是偶然?
沃霍爾和母親住在一起,一只貓,兩個菲律賓女傭,家中沒有現代器物和當代藝術品,他瘋狂購買的物品中,有古舊手表、珠寶首飾、杜尚的小便池、化妝品、玩具……他死后,蘇富比拍賣行為他舉行的專場拍賣中,許多物品都是第一次打開包裝。他還堅持每年圣誕節在哈林區的一家教堂為窮人施粥。
1987年2月14日,沃霍爾去世前一周,他在日記中寫道:“做瑣碎的事,很短的一天過去了,沒有什么發生,我上街購物,回家電話聊天,如此,真是很短的一天。”
沃霍爾后來熱衷于電影,并且被授予1966年第六屆獨立電影獎,頒獎辭這樣評價他的電影:
“安迪·沃霍爾將電影帶回了它的源頭……他以一種偏執的態度記錄人的日常生活及他周圍所見的事物。我們所見的世界比過往清晰,但并不是在一個被高度戲劇化的狀態,也不是為了服務于其他什么目的,只是單純、最低限的原質,像吃就是吃,睡就是睡……”
女同性戀者索拉娜絲為她所寫的劇本尋求拍攝機會,來到沃霍爾制作電影的工廠,當她的劇本無端遺失之后,沃霍爾成為了索拉娜絲糾纏的對象,最后她一槍射進沃霍爾的胸部。索拉娜絲入獄后出版的女性主義著作,多次再版,成為女權主義的經典作品。
加拿大女導演瑪莉·哈倫曾于1996年將索拉娜絲槍殺沃霍爾的事件搬上銀幕,名為《我槍殺了安迪·沃霍爾》。
沃霍爾1987年死于外科手術。
感謝復印技術,沃霍爾留下了超過1萬件的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