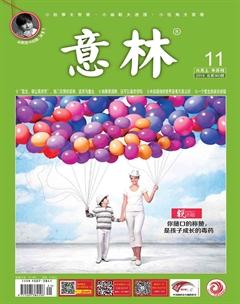閑逸之美
李娟:曾獲“第五屆冰心散文獎”“首屆孫犁文學獎”,有80余篇作品入選中高考真題、模擬題及中學生語文閱讀教材。
意林:散文《閑逸之美》的創作初衷是什么?
李娟:創作《閑逸之美》時,我正在讀張潮的《幽夢影》與沈復的《浮生六記》,齊白石和豐子愷的畫作也是我的枕邊書。歷代文人雅士閑逸雅致的精神世界,給予我寫作的靈感。在如今快節奏的生活狀態下,閑情從容的生活仿佛是一種奢望。希望大家都能卸下生活的重壓,脫去功利的外衣,回歸生活的起點,終將做回自己。
意林:你認為這篇文章為何會入選高考題?
李娟:這篇散文思路清晰,溫婉清麗,意蘊悠長。文章的結構方式是典型的“總—分—總”式。開篇開門見山,提出自己的藝術見解,指出“閑逸是藝術創作必需的氣質”;隨即用文化名人的事例,進行事實論證;最后總結升華主題,水到渠成地表明自己的志向。
意林:文章入選高考題后 ,是否會把入選作為創作方向?
李娟:《閑逸之美》寫作于2012年,我寫過:“閑,是不為寫作而寫作,不為功利而寫作;閑逸的文字里,有一顆自由的靈魂。”這是我寫作的訴求,也是一種自省。一個作家不為功利的寫作,才是心靈泉水的自然流淌。我一直會這樣堅守下去。
(圖/吳敏)

閑逸,是藝術創作必需的氣質,也是一種心境。凡是雅致和有情趣的事,往往都來自一份閑情。
夏夜,翻看豐子愷先生的文章和畫,懂得了閑逸之美。抗戰期間,他帶著全家遷往重慶郊區的一座荒村,物質貧瘠,生活困頓不堪。可是,一家人種豆種菜,養鵝養鴨,自得其樂。他養著一只大白鵝,稱它為“鵝老爺”。那篇《大白鵝》的文章,至今讀來,風清月白,閑淡清雅。寫盡荒寒生活中之樂趣,令人忍俊不禁。他寫道:“鵝的步調從容,大模大樣的,頗像平劇里的凈角出場。”我猜想,豐先生作畫累了,就倚在窗前看白鵝吃飯,“我們的鵝是吃冷飯的,一日三餐。它需要三樣東西下飯:一樣是水,一樣是泥,一樣是草。先吃一口冷飯,次吃一口水,然后再到某地方去吃一口泥及草……但它的吃法,三眼一板,絲毫不茍……這樣從容不迫地吃飯,必須有一個人在旁侍候,像飯館里的堂倌一樣。”白鵝的憨態躍然紙上,仿佛一個頑皮而倔強的孩子。
豐子愷于亂世中讀書作畫,種豆養鵝,在困境中保持文人優雅、閑逸的心態。生之樂趣和閑散,就在淡定從容,妙趣橫生的文字里。
閑情,是三月間看桃花開遍陌上,聽杜鵑鳴,什么也不做,也不想了。也是偷得浮生半日閑,邀三兩知己,去水邊品茗。有時,從午后一直坐到日暮黃昏,不知不覺,一彎新月爬上柳梢。人散去,一回頭,仿佛看見豐子愷先生那幅畫《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只見天空新月一彎,竹簾半卷,竹椅幾把,桌上茶杯幾盞,就是不見一個人,卻有著說不出的意境。
閑逸的文字里,有一顆自由的靈魂。如秋天的果子,豐盈飽滿。文字不端架子,讓所有的限制都解甲歸田。文字才有了靈性和飛翔感。 其實,閑情逸致的人也一樣。
我追求自己的文字里有一份閑逸之美,學做一個嫻雅之人,氣定神閑,淡定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