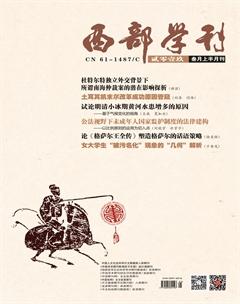小城鎮在城鄉關系中的功能
王昱皓
摘要:小城鎮是農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它的發展狀況,對于城鄉協調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具有重要意義。文章通過對費孝通關于小城鎮研究的思想脈絡的梳理,認為小城鎮在城鄉關系中具有中介、緩沖和平衡功能。只有在城鄉關系視角下來看待小城鎮的功能,才能看到小城鎮的價值所在。
關鍵詞:小城鎮;城鄉關系;費孝通;功能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CN61-1487-(2019)05-0139-03
費孝通早在農村調查時期就發現了一種“比農村社區更高一級社區”的存在,它與周圍農村社區保持聯系但又具有不同的特點,費孝通稱之為“小城鎮”[1]。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由于社隊(鄉鎮)工業的迅速發展,全國各地小城鎮復興,人口迅速增加,費孝通在1981年三訪江村時又提出小城鎮研究。從總體來看,費孝通對于小城鎮建設問題雖有探討但不是重點,實際上是從小城鎮與外部的關系,特別是作為小城鎮復興主要原因的社隊(鄉鎮)工業與城鄉之間的關系來探討小城鎮的地位與作用。因此,只有在城鄉關系視角下來看待小城鎮的功能,才能看到小城鎮的價值所在。
一、費孝通小城鎮研究歷程
費孝通在《四年思路回顧》(1989)和《農村、小城鎮、區域發展──我的社區研究歷程的再回顧》(1995)兩文中都回顧了進行小城鎮研究的緣起。費孝通早在江村調查時期就已經發現了集鎮對于城鄉聯系的重要性,但由于時間和條件的限制,沒有進一步對小城鎮問題開展研究。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的小城鎮正處于衰落,城鎮人口處于停滯甚至下落狀態。費孝通重訪江村時提出的主張受到了政治運動的批判,他的第一次學術生命終止。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第二次學術生命開始后,費孝通發現由于社隊(鄉鎮)工業的發展,小城鎮迅速復蘇,費孝通在三訪江村時又提出小城鎮研究。可以看出,費孝通的小城鎮研究其實是對于農村研究的發展與延續。1983年,費孝通從吳江縣各鎮入手,發現各鎮正在從衰落走向復蘇,提出了“小城鎮? 大問題”的論斷,而后又逐步擴大研究范圍,包括蘇州、無錫、常州、南通四市。1984年,費孝通的研究領域又擴大到蘇北,寫成《小城鎮? 蘇北初探》。在對蘇南和蘇北的對比中,費孝通發現江蘇省內蘇北與蘇南存在不同的發展模式。之后,費孝通的研究范圍又延伸到南京、鎮江和揚州。1984年,費孝通的研究跳出了江蘇,由點及面逐漸擴展到全國,發現了小城鎮的重要作用。
二、城鄉關系中的小城鎮
費孝通在對小城鎮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總結了以社隊(鄉鎮)工業為基礎的小城鎮具有不同的發展路子,即不同的發展“模式”。在對各種模式進行比較分析時,費孝通注意到“靠近城市的鄉村更容易發展起來鄉鎮企業,城市具有較好的現代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而內地和邊區的鄉村即使有了內發,沒有外援還是沒辦法發展”[2]。這個發現使費孝通注意到城鄉關系的存在,開始從小城鎮研究逐步走向城鄉關系研究。
費孝通在《鄉土重建》(1948)論文集中,對城鎮和城鄉關系展開了論述。在《論城·市·鎮》一文中,費孝通針對城鄉關系中的“城”這一社區加以區分,將沒有受到現代工業影響的稱為“市鎮”,反之則稱為“都會”。臨時性的市集發生了集合,因此“從商業的基礎長成的永久性社區”被稱作“鎮”[3]。在《鄉村·市鎮·都會》(1947)一文中,費孝通提出了對城鄉關系的兩種看法:相生和相克。“鄉市相成論”認為鄉村和都市是相關一體的[3]。都市需要鄉村的農副產品作為糧食和工業原料,而都市的工業制造品則輸入農村,鄉市之間的商業愈繁榮,雙方居民的生活水平愈高。而“城鄉相克理論”則認為城鄉是相克的,一是因為“市鎮并非生產基地”。鄉村人多地少,存在過剩勞動力,勞動成本降低,地主便出租土地脫離了勞動。離地地主在脫離勞動進入市鎮后,依靠地租、利息等收入剝削鄉村;二是因為“鄉村靠不上都會”,都會輸入洋貨并用機器生產工業品,奪走了鄉村手工業收入。西方機械化引入,鄉村手工業不能與之競爭。農民失去了手工業的重要收入,需要依靠土地來獲取收入,土地問題變得尖銳。外國商品引入,離地地主的消費增加,鄉村的血液便枯竭了,最終形成“都市克鄉村,鄉村侍奉都會”的局面,都市興起則鄉村衰落。從這種觀點來看,本應給雙方帶來繁榮的城鄉關系卻給農村帶來了破壞,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來看,城鄉之間的關系經常處于對立之中。
在《中國士紳:城鄉關系論集》(2013)中,費孝通詳細論述了城鄉之間的經濟關系,這種關系給鄉村帶來不利影響。城市靠向農村收取地租和利息等來獲取收入,卻未能提供鄉村農民需要的產品,城鄉差別也在不斷擴大。費孝通在書中對于“城”和“鎮”的概念進行了區分,提出“鎮”是聯系鄉村工業和更為發達的商業與制造業的紐帶[4]。
在抗日戰爭時期,城鄉聯系被割斷,在某種程度上來看,鄉村反而得到了發展。由于城鎮和都會需要鄉村提供農副產品,并向農村收取地租和利息等來獲取收入,城鄉聯系的割斷造成了城鎮和都會衰落,影響了傳統城鎮的經濟結構。“想要恢復良好的互補性的城鄉關系,關鍵就在于城鎮需要變為生產社區,不用去剝削鄉村”[4]。因此在鄉土重建時期,城鎮是在剝削鄉村,城鄉關系的矛盾是存在的。問題的解決需要先從都市入手,迫切需要傳統的市鎮發生變質,發展鄉鎮企業,使城鎮從“消費集團”變為“生產社區”。從《江村經濟》到《鄉土重建》,可以看出費孝通認為在城鄉關系中,城市在吞食鄉村,提出的對策是城鄉需要一體化的改革,形成一種良好的互補關系,需要小城鎮在其中予以調和,成為連接紐帶,促進城鄉共同發展。
三、小城鎮在城鄉關系中的功能
通過對費孝通城鄉關系和小城鎮研究文本的研究思路進行回顧,可以總結出小城鎮在城鄉關系中可以發揮以下功能:
(一)中介
在《江村經濟》中,費孝通就看到江村作為農村社區,并不是孤立和自給的。江村水運便捷,依傍震澤鎮,震澤鎮作為商品銷售中心,農民通過中間商人購買工業品,販賣土特產品。震澤鎮通過航船與周圍的農村聯系起來,成為這個區域的商品流轉中心[5]。
在《云南三村》中,費孝通發現祿村存在一種臨時貿易場所“街子”[6],農民在“街子”上進行商品交換。隨著貿易頻繁增加,最終臨時性的貿易場所固定下來,成為“鎮”。而三村之一的玉村靠近玉溪縣鎮,具有靠近城鎮的菜園經濟特點。費孝通在《云南三村》序言中提及,玉村調查的主題為他在80年代的小城鎮研究開辟了道路[5]。
費孝通在《鄉土重建》(1948)中提出,“鄉村和都會中間還隔著市鎮,市鎮不從事生產的地主搜刮鄉村的農產品送入都會,起著中介的作用”[3]。小城鎮作為農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帶動了農村的發展。農村產生的剩余勞動力首先進入小城鎮,城市的產業轉移又連接著小城鎮。小城鎮作為中介者,在自身經濟得到發展的同時,能夠促進周圍附近鄉村的發展,以工補農、以工促農、城鄉互惠,從而縮小城鄉的差距。
費孝通在《紀念費孝通教授<小城鎮大問題>發表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03)中指出,小城鎮在城鄉一體化道路上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小城鎮的發展還需要依靠城市的發展。蘇南農村能夠發展出鄉鎮企業還因為靠近大中城市,以大中城市作為依托,同時大中城市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也通過小城鎮傳播到農村中去,促進資源能夠在城鄉之間的資源流動和自由組合,促進城鄉共同繁榮。
1982年,費孝通以訪問江村作為起點,三訪、四訪江村,發現鄉村發展出了鄉鎮企業,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具有良好的前景,拉動了鄉村經濟發展。為了尋找鄉村致富的原因,費孝通將小城鎮看作是城鄉結合部,開始進一步研究作為農村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小城鎮來認識中國社會。費孝通在《小城鎮? 大問題》一文中提出,小城鎮是農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沒有小城鎮,農村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就沒有腿”[1]。小城鎮建設是發展農村經濟、解決人口問題的關鍵。費孝通提出:“農村發展之后,必然會產生一個商品集散中心,也就是市鎮。”從歷史上來看,過去的小城鎮是鄉村交換物資的中轉站,鄉村將農副產品運往集鎮,而集鎮將城市里的工業品輸入鄉村。小城鎮作為鄉村的商品集散中心,不僅與農村之間具有聯系,同時也與大中城市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
在建國初期,鄉村實行以糧為綱,取消了商品生產。特別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限制商品買賣,全部由國家統購統銷,沒有行政機構的小城鎮失去了商品流通功能,失去了與周邊農村的聯系。商業國營化,小城鎮的人口大大衰落,而商品經濟發展以來,小城鎮的商品流通渠道暢通。城市運往集鎮的不僅有工業品,還有供應鄉鎮企業的原料;從集鎮運往城市的也不單單是農副產品,也包括工業品。小城鎮是中國城鄉系統中聯結農村與城市的重要環節,小城鎮發展出鄉鎮企業來承接城市的產業轉移,形成了“一條龍”工業體系,生產關鍵部件和承擔總裝任務的“龍頭”設在市內,“龍尾”則擺在集鎮和鄉村[1]。鄉鎮企業以城市工業為依托,城市工業以鄉鎮工業為后方,城鄉在經濟上有所分工,生產要素能夠在城鄉之間流動和自由組合。
(二)緩沖
由于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優先發展重工業,優先發展城市,并且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動,而農村人多地少,存在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城鄉差別逐漸拉大。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戶籍制度的松動,人口流動增加,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費孝通認為由于缺乏小城鎮積聚人口的作用,我國城鄉人口呈現出“中間細,兩頭粗”的葫蘆狀分布,人口級差太大。費孝通(2002)提出:“這20年里,我們看到了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現象,而且這種集中的速度相當快。農民離鄉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在鄉下活不下去了或是生活得不好;二是農民離鄉出去后要有活路,也就是有活干,能生活得下去。”[7]小城鎮的興起,逐漸構建了合理的城鎮等級體系,改變了費孝通所說的葫蘆狀的不合理分布。
費孝通在《小城鎮研究十年反思》(1995)中分析了小城鎮具有增加農村收入、人口蓄水池和走上現代工業化的功能。小城鎮可以在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盲目流動的過程中起到控制和緩沖作用,工業下鄉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到小城鎮。大中城市的承受力在初期較為薄弱,國家缺乏足夠的資金來加強大中城市容納剩余勞動力的設施建設。小城鎮在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方面有很大的優勢,就是成本低。“各個層次的小城鎮都在一定程度上將聚居的人口分散,減輕大中城市的人口壓力”[8]。勞動人口從農村向小城鎮聚集,“離土不離鄉”“離鄉不背井”。
(三)平衡
費孝通比較吳江縣不同類型的小城鎮,分析了小城鎮在70年代以前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傳統重農輕商的政策,造成了農村和城鎮在經濟上的惡性循環。費孝通提出了“農村城市化”的觀點。費孝通在《小城鎮? 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鄉村工業化的道路,鄉村的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由于社隊工業即后來的鄉鎮工業的發展,使得小城鎮得以復興。費孝通首次提出了“蘇南模式”[1],分析了蘇南地區鄉鎮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內在聯系,又分析了鄉鎮工業和城市工業的經濟聯系,認為鄉鎮工業、農副業和城市工業形成了一個系統。在《小城鎮? 新開拓》一文中,費孝通提出鄉鎮企業是城鄉聯合的環節,鄉鎮企業帶動了小城鎮的復興,也帶來了城鄉關系的變化。小城鎮作為聯系城鄉的紐帶,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城鄉社區之間分工合作,形成社會經濟統一體。
農村由于工業化的深入,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過去城鄉對立以及城鄉區別的消滅,出現城鄉一體化。以鄉鎮企業為依托的小城鎮能夠加強城鄉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小城鎮對農村不僅是經濟的促進,也是文化的傳遞和信息的交流。小城鎮使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使之能夠享受到城市生活方式。城鄉交流在小城鎮的媒介之下迅速增加,在小城鎮工作的居民鐘擺式地往返城鎮與農村,他們將城市居民的行為與價值規范傳播到農村,使農村居民的意識、需求、興趣和價值標準發生變革。小城鎮作為農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其發展促進了城鄉的經濟發展。在經濟發展的帶動下,教育、衛生和科學技術等各項社會事業都得到了蓬勃發展,道路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也得到了完善。小城鎮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城鄉之間的聯合,城鄉之間的人員、物資和信息等方面聯系越來越密切,城鄉差距縮小,小城鎮的發展水平體現了城鄉一體化的水平。小城鎮的平衡功能還體現在維系政治穩定上,“不論附屬于‘城的工商業怎樣發達,在以地主為主要居民的社區里,它的特性還是在消費上。這些人口之所以聚集的基本原因是在依靠政治以獲得安全的事實上”[3]。
參考文獻:
[1]費孝通.小城鎮四記[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
[2]費孝通.中國城鄉發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課題[J].中國社會科學,1993(1).
[3]費孝通.鄉土中國(修訂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費孝通.中國士紳:城鄉關系論集[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3.
[5]費孝通.江村經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6]費孝通,張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7]費孝通.學術自述與反思:費孝通學術文集[M].北京:三聯書店,1996.
[8]費孝通.志在富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