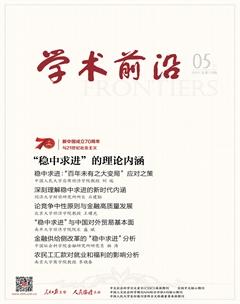歷史制度主義視角下的鄉村生態治理觀察
嚴燕 馮緒猛
【摘要】環境問題由來已久,鄉村環境制度屢經調整。制度的構建要從歷史情境和現實境況中尋找根據。從鄉村環境應對的歷史脈絡看,鄉村環境應對受到宏大歷史情境、政策影響變量及相關主體之間的博弈約束等三個維度的影響。正是在多種結構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環境應對才實現了制度變遷。鄉村環境應對具有路徑依賴和漸進轉型的特征,在應對過程中存在著關鍵節點和斷續平衡,鄉村環境應對需打破當前的歷史否決點,構建鄉村生態專項制度體系,健全鄉村環境保護問責機制,從而實現鄉村環境保護制度創新。
【關鍵詞】鄉村環境問題 ?政府應對 ?歷史制度主義 ?制度變遷
【中圖分類號】D60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0.008
鄉村環境善治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重要保障。近年來,面對嚴峻的鄉村環境問題,鄉村環境政策不斷調整,鄉村環境應對經歷了一個日漸完善的過程。歷史制度主義注重從宏大的歷史情境中分析與解讀制度變遷的動力影響以及制度變遷本身表現出來的復雜特征,強調制度與歷史的關聯性。鑒于此,本文結合歷史制度主義的研究范式,對政府應對鄉村環境的嬗變軌跡進行歷史回溯,旨在厘清鄉村環境應對的歷史脈絡,為政府應對鄉村環境的未來走向提供決策參考。
鄉村環境應對的理論范式及歷史沿革
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范式。20世紀80年代初,歷史制度主義作為西方政治科學的一個新制度主義流派出現以來,就被學者們廣泛采納。作為一種中觀層次上的制度分析,歷史制度主義通過中間層次的制度來聯接宏觀層面上的社會經濟背景和微觀層面上的政治行為。[1]歷史制度主義強調在歷史的情境中探究制度作為自變量和因變量的雙重特征,“歷史是某一事件發生的時機與情境,而這種時機與情境中又內含有制度的遺產。”[2]歷史制度主義主張在一定的時間序列和空間結構中探尋制度的生成和變換的過程。正如豪爾和泰勒所言,“歷史制度主義需要尋求對不同國家的不同的政治后果和政治后果的不平等作出更好的解釋。”[3]歷史制度主義認為制度一旦形成,就會依據慣性形成一種發展路徑,即“路徑依賴”,從而實現自我強化的目標。直至出現了“關鍵節點”,制度則“斷裂”,形成新的循環,制度隨社會的發展而被重新建構實現均衡。當然,制度變遷并非都是“關鍵節點”“偶然事件”促成,還有內部因素考量。因此,歷史制度主義者也提出了制度變遷的內生理論,認為“理念可以形塑和改變行動者的偏好以及對時機和情境的認知,從而導致行為選擇的改變”。[4]從宏觀層面看,歷史制度主義主要運用歷史研究方法和比較研究方法對歷史和現實世界的重大問題進行解釋;從微觀層面看,歷史制度主義主要關注歷史發展過程中制度的作用以及制度變遷的規律,冀望在歷史的進程中探尋制度、觀念和利益的結構性關系。
政府應對鄉村環境的歷史沿革。在中國古代,古人在長期的勞作過程中意識到農業生產和自然界之間的依附關系,環境應對多數致力于合理利用資源、緩解人地關系。早在秦漢時期,政府設置環境保護機構,制定環境法律來保護環境。明清時期,政府為了抵御自然災害,大規模地興修水利。民國時期,囿于國土淪喪以及政局動蕩等因素,環保措施多流于形式,成效甚小。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著力采取措施整治土地開發不當造成的生態破壞。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受到“以糧為綱”的目標導向影響,許多地區的自然環境和農業生態環境處于惡性循環之中,鄉村環境問題開始受到關注。改革開放后,鄉鎮企業飛速發展,鄉村生態破壞程度加深,保護環境成為政府關注的重點。中央政府陸續頒布了《關于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這些文件對農業生態保護和鄉村生態保護都作了相關說明。1979年,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此后,政府相繼頒布了一批農業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條例和管理辦法,其內容主要涉及面源污染和工業污染的預防防治。21世紀后,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環境問題進一步凸顯,政府采取了諸多措施改善鄉村環境,提高鄉村的生活質量。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2007年,黨的十七大把生態文明首次寫入政治報告,并指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鄉村建設。2012年,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列入重要議題,并提出美麗鄉村建設的新目標。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調農業鄉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
鄉村環境應對的結構性變遷
任何制度的產生都源于當下社會現實問題的考慮,同時也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制度是把歷史經驗嵌入到規則、慣例和形式中去,又超越于歷史片段和條件而存留下來。[5]因此,制度的構建要從歷史情境和現實境況中尋找根據。從鄉村環境應對的歷史脈絡看,鄉村環境應對受到宏大歷史情境、政策影響變量及相關主體之間的博弈約束等三個維度的影響。正是在多種結構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環境應對才實現了制度變遷。
鄉村環境應對的宏大歷史情境。新中國成立后,囿于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和不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生產、生活過程中出現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鄉村環境保護在相關的規章制度中有所涉及。改革開放后,經濟進入快速增長時期,鄉村環境問題從早期一元的農業環境問題轉變為農業與鄉鎮企業二元并存的環境問題,鄉村的環境保護從早期的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增加了鄉鎮企業污染防治、鄉村居住環境改善等方面的內容,制度體系綜合化,實施手段可操作性增強。[6]2000年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階段,高污染產業向農村轉移、城市化進程等帶來了新的環境問題,鄉村環境問題愈加復雜。2005年,國務院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鄉村建設的若干意見》。同年,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這兩大綱領性文件強調統籌城鄉發展,加快發展生態農業,將鄉村的環境保護事業放在了突出的位置。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落實“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鄉村環境制度建設邁向新的高度。
鄉村環境應對的政策影響變量。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觀強調制度對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關聯作用,同時又特別強調政策變量對制度的形塑作用。建國初期,政府優先發展重工業,環境保護長期讓位于經濟發展。1978年后,中央政策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發展鄉鎮企業。在農民積極性提高和鄉村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誘發了鄉村環境問題的產生。作為對現實問題的回應,鄉村環境保護快速發展。1986年,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強調鄉村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并明令制止城市向農村轉嫁污染。1988年,部分地區實施鄉鎮企業排污許可證制度。1996年,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強調加強對鄉鎮企業環境管理。2000年后,鄉村受到中央層面的高度關注。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黨的十七大提出“推進社會主義新鄉村建設”。黨的十八大提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在環境政策演變的過程中加強了鄉村環境保護制度的頂層設計,治理內容從單一水土保持、資源保護層面,逐漸轉變到從整體上對鄉村環境規劃,全面提升鄉村的現代化水平,提升鄉民生活質量。
鄉村環境應對的主體博弈約束。鄉村環境應對中,主要涉及到三方面的主體:地方政府、企業和農民。政府代表公共利益,要維護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協調性,均衡各方利益,強化自身政權合法性建設。在環境應對的每個環境制度變化節點,政府都通過制度設計推動了制度創新。但毋庸諱言的是,囿于壓力型體制的影響,地方政府會出現策略失當和政府失靈現象。對企業而言,在經濟利益最大化目標的驅動下,會逃避法律法規,產生機會主義行為。對農民而言,他們既是鄉村環境的保護者,也是環境問題的產生者。由于參與機制的不健全,他們通常被排除在環境決策主體之外,自身的利益無法得到有效地保障。但同時,由于農業生產方式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農戶也會有機會主義行為,過量地施肥和撒藥,致使農業面源污染的產生。在三方主體的利益博弈下,鄉村生態危機的現實窘境必然產生。最終,在輿論壓力及高層關注下,政府會解除和企業的利益關系,監督和處置一切違反環境法律法規的行為,鄉村生態制度也因此得到發展。
鄉村環境應對的歷史性變遷
路徑依賴與漸進轉型。路徑依賴是歷史制度主義的重要概念,它來源于經濟學,強調的是歷史進程某個重要的制度、結構、社會力量、重大事件或者其他關系對當前制度型構所產生的方向、內容和模式方面的同質性的依賴性影響。[7]在我國環境應對過程中,鄉村環境保護是在歷史的基礎上積淀而成的,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特征。新中國成立后,政府頒布的法令重在保護生態資源。改革開放后,鄉村環境保護不僅注重資源保護,也涉及污染防治,但總體而言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2000年后,城鄉二元結構的路徑慣性導致城鄉之間環保差距依然突出,鄉村環境保護普遍存在治理主體缺失、環保投入資金不足、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等問題,鄉村環境問題制約著新農村建設目標的實現。近十年來,鄉村環境保護逐漸被提高到戰略高度,政策手段從早期的單一行政命令為主導向多元的以法律、經濟和技術手段轉變,鄉村環保制度建設不斷完善。
關鍵節點和斷續平衡。歷史制度主義者強調,制度變遷的過程中,關鍵節點很重要。它是具有特定順序的因果變量間的相互影響在某一具體時刻的這一點上結合在一起,[8]這種聚集在一起的影響能夠打破舊制度體系,產生新制度。在鄉村環境應對中,存在三個關鍵節點。第一個關鍵節點是1972年,聯合國召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這次會議給世人敲醒了警鐘,也對我國環境保護產生巨大沖擊。1973年,國務院召開了全國第一次環境保護工作會議,它是全國環境保護的一個轉折點。人們認識到環境保護工作不僅是治理“三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保護資源、維持生態平衡。第二個關鍵節點是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會議的重要議題就是強調環境與經濟并重發展,并得到世界各國的積極響應。同年,我國確立“可持續發展戰略”。此時,我國農業生態環境問題已經日益顯現,迫使政府將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持續性開始納入農業發展目標體系之中,各種法規陸續修訂。[9]第三個關鍵節點是2004年,以“三農”(農業、鄉村、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了“三農”問題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重中之重”的地位。此后連續十五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均是以“三農”為主題,代表了中央高層對鄉村問題包括鄉村生態環境問題的高度重視,鄉村生態制度改革持續推進,許多政策法規陸續出臺或修訂。
歷史否決點和制度創新。歷史制度主義者們試圖在歷史時段內闡釋制度的因果過程和重大結果。但是歷史過程是緩慢的,碎片式的制度不會強化制度優化,同時也暴露自身的脆弱,從而使得歷史否決點的數量逐漸增加。就我國而言,鄉村環境應對經歷了從無到有的歷程,呈現出漸進演變的變遷邏輯。但當下的鄉村環境形勢依然很嚴峻,在鄉村環境應對過程中,存在諸多否決點:當前鄉村環境問題不僅僅是停留在一元的環境污染層面,環境問題的廣度和深度都在累加,各種相互交織的新舊問題所帶來的環境風險也在增加;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我國鄉村的環境保護制度落后于城市,鄉村環境保護的專門立法還未設立。雖然鄉村生態制度一直在尋求變革,但因受到“重城輕鄉”的影響,鄉村環境保護發展緩慢;地方政府在環境應對過程中,秉承慣性思維,很容易經濟發展優先,出現“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消極行為取向,政策執行有失偏頗。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這些歷史否決點終將被打破,路徑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消弭政府應對主體的中心地位,完善鄉村環境保護的手段。政府重塑自身角色,走出路徑依賴的困境,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動員多種社會力量,共同建設美麗鄉村,實現鄉村環境有效治理。二,完善鄉村環境保護的政策體系,健全鄉村環境保護問責機制。制定鄉村環境保護的專項立法,完善鄉村環境保護的實施細則,使得鄉村環保制度更具針對性、可操作性。三,加大鄉村環保投入,重視鄉村環保設施建設。完善鄉村環境問題的預警機制,健全環保執法機構,提高環境執法實效性。強化鄉村環保宣傳教育,提升鄉民的環保意識。
(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于利益博弈的農民集體行動及鄉村生態合作治理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社會資本視域下的鄉村環境治理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8ZZB006、SKYC2019011)
注釋
[1]何俊志:《結構、歷史與行為——歷史制度主義對政治科學的重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9頁。
[2]Immergut, Ellen.,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1998.
[3]江帆:《東盟安全共同體變遷規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06頁。
[4]王晨光:《路徑依賴、關鍵節點與北極理事會的制度變遷——基于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外交評論》,2018年第4期,第54~80頁。
[5][美]詹姆斯·G·馬奇、[挪威]約翰·奧爾森:《重新發現制度:政治的組織基礎》,張偉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168頁。
[6]王西琴等:《我國鄉村環境政策變遷:回顧、挑戰與展望》,《現代管理科學》,2015年第10期,第28~30頁。
[7] 劉圣中:《歷史制度主義:制度變遷的比較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6頁。
[8][美]保羅·皮爾遜、瑟達·斯考克波爾:《當代政治科學中的歷史制度主義》,轉引自何俊志、任軍鋒、朱德米編譯:《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譯文精選》,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6頁。
[9]張詠、郝英群:《鄉村環境保護》,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24頁。
責 編/趙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