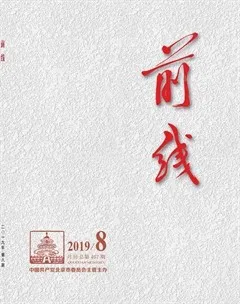密云水庫之戀
張蕾磊 尹穎堯
“北京城里三杯水,一杯來自密云水庫。”這杯水是兜底的,是生命之水。源于塞外的潮白二水,在燕山群峰中蜿蜒曲折,在密云城南交匯成潮白河。61年前,因這東來的潮水、西繞的白水,人們筑起了大壩,修成了密云水庫。1985年,北京市將密云水庫確定為首都飲用水源地。為了守護北京人的“大水缸”,密云叫停水庫旅游資源的開發,拆除水庫壩上的商業、餐飲、娛樂等設施,撤出網箱養魚,先后關閉鉻礦、小型鐵礦、水泥廠等200多個對水源有污染的工業企業。如今,密云人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指引下,以生態富民戰略,發展電商農業圈,探索田園綜合體的實踐,開創密云生態文明建設新格局。
鄉愁淹在水底下
一聲令下,5萬密云父老鄉親揮淚離故土,24萬畝良田被淹沒。看得見的水庫,揮不去的鄉愁。
“趴在冰面上,就能瞅見老家了,清楚著呢!能看到石頭壘的房子,斷墻,還有井。”萬明芝說。
對于1968年出生的萬明芝來說,100多米水底下的老家是陌生的。在她出生的10年前,父輩從現在水庫主壩往東七八里地的村中舉家搬遷。“先是在金叵羅村,后來在蕎麥峪住下來了。”萬明芝的二叔、80多歲的萬景林慢慢地說。他身體硬朗,說到搬家,手邊的煙半天沒有抽。“那時候的人都聽話,為了建水庫,說搬就搬了。”
修建密云水庫是為了緩解京津地區用水緊張問題,更重要的是為了解決潮白河的水患問題。流經北京東部的潮白河,上游是潮河和白河。據史書記載,潮河因其“水性猛,時作響如潮”而得名,白河則是因河岸沙白而名。潮、白兩河匯成潮白河后,河道平淺,又無堤防,常常泛濫成災。
萬明芝如今生活在白河主壩附近的蕎麥峪,行政區域屬于溪翁莊鎮,據說“溪翁莊”的名字就源于水患記憶。“我們是最后搬出來的,馬車拉著糧食、鋪蓋。”82歲的馮東賢老人鶴發童顏,思路清晰,他比畫著說:“碾子搬不走,很多家具也都扔下了。剛搬到尖巖的時候,就住在北邊的街上,也是人家給咱騰的地方,大家都是擠著住。”回想起老家,比馮東賢小一歲的劉顯朋打開了話匣子。“我們村過去是四山三水三分田。那山,現在在庫里還能看到一小部分。山上主要是栗子樹,長得密,上了山看不到太陽。三分水,能打魚;三分田,近500畝稻田。”劉顯朋記憶中的老家如詩如畫,有著魚米之鄉的富足和幸福。
據統計,1958年密云水庫建庫之初,庫區淹沒耕地16.9萬畝,加上筑路、修渠、移民建房和料場取土,共占用耕地24萬畝,相當于全縣耕地的三分之一。為保證密云水庫施工及攔洪,分兩批搬遷了庫區內65個村莊,進行清庫。不到9個月,5萬余人搬遷至5個公社的84個村。
忽然之間,一家房兩家住,一村地兩村種,移民和安置地原有村民都有困難。“陌生的人住到一起,難免馬勺碰鍋沿,就有口角。”尖巖村的鄭懷江當時雖然是個孩子,卻也記得爭吵時,被人懟是外村來的,氣得沒話說,只好遙望老家的方向。
1963年底,第一批3.4萬間安置房建成,庫區移民有了新家。萬明芝的父親、叔叔在蕎麥峪扎下根來。聽著大人們的念叨長大,她終于透過冬日的冰面窺到老家的模樣,“現在水位高了,看不見了。”她的笑容中有了幾分惆悵。
1974年,密云水庫蓄水水位達到153米,是水庫建成后水位最高的一年。庫邊一部分村莊房屋進水,密云再次決定將部分村莊遷移到水庫南部。從1974年到1976年,共有13個村近4000人遷往水庫南部的十里堡、西田各莊。經過幾次移民,密云90%的村都有移民戶。20世紀90年代,水庫周邊地區的人口嚴重超載。國務院決定將居住在水位155米以下和生活條件比較差的15000人搬遷出庫區。三次大移民,密云近7萬人搬離故土。
2018年初,穆家峪鎮新農村和劉林池村啟動“新劉棚改項目”。新農村是1958年的水庫移民村,當時只有712戶、2700人,居住在政府蓋的20間為一體的排子房里。60年后發展成為3150戶、6450人,還有3000多外來人口的大村。98歲的張長珍面臨再次搬遷,淚如雨下。搬家那天,她讓兒子把系在窗欞上的風鈴解下來,捐贈給村里籌建的鄉愁博物館,那是當年從水庫搬家時帶來的,她想讓子孫后代將來有機會認識它。
生計拴在水庫邊
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密云的產業結構和生產力布局與“保水”步伐同頻共振。“保水”如人們心底的一根弦,每次撥動就有一段難忘的插曲。
路循環往復,水四季變換,密云水庫邊的美景讓人流連。然而,景因情而異。
劉顯朋回憶,1962年大家在尖巖安定下來,但人均只有兩分多地,且多為荒坡野地。村里開始修建水渠、平整土地。水渠修在新村的北山上,綿延4公里。鄭懷江驕傲地說,那是尖巖村人的“紅旗渠”。尖巖村民開辟出400畝地種麥子,還可以間種玉米,第二茬種大豆,一年一畝地收1500斤左右糧食。在春耕秋收中,他們養兒育女,日子如流水般過去。
20世紀80年代,密云水庫逐漸停止農業灌溉。1985年,北京市將密云水庫確立為首都飲用水源地,密云的絕大部分區域劃入水源保護區。村民們鑿出來的引水渠徹底停用了,不能種地,只能謀其他生路。有人打魚,有人網箱養魚,還有人給搞旅游的個體戶打工,大家本能地過著靠水吃水的日子。1992年,萬明芝和丈夫搖著三米的船,一天兩趟在水庫打魚。萬明芝回憶,下午三四點下網,晚上八九點起網,到家10點,摘魚。凌晨3點出門,下第二次網,亮天起網,摘魚到上午10點。“魚販就在家門口等著,一手交魚,一手交錢。”萬明芝得意地說,“有一回,兩條魚賣了800塊!”
1996年起,水庫每年有6個月的禁漁期,勤快的萬明芝開始在外打工。那時候,在水庫邊的山上開了不少個體飯店,人們既能看到水庫的美景,又能吃到水庫魚鮮,個體飯店生意火爆。萬明芝笑說自己膽小,不敢貸款,沒搞網箱養魚。二叔萬景林帶著兒子萬明泉忙乎網箱養魚。二十出頭的萬明泉,年收入兩三萬。與此同時,尖巖村的鄭懷江和村民們籌資,在水庫大壩出水口發展網箱養魚,村里還因此辦起飼料廠等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