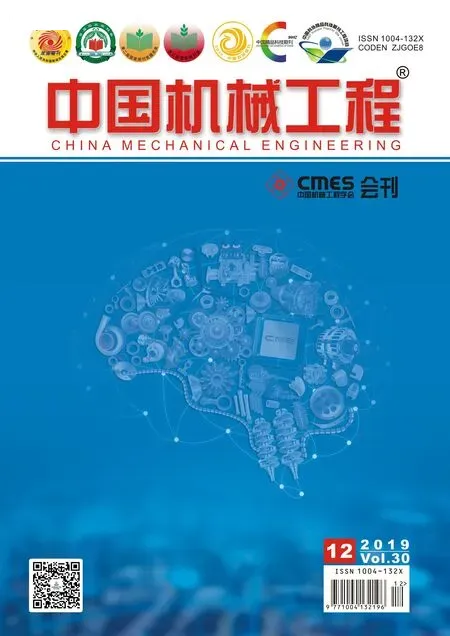海上風力機與船舶碰撞的動力響應及防碰裝置
韓志偉 周紅杰 李 春 丁勤衛 郝文星 余 萬
上海理工大學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上海,200093
0 引言
2016年全球風電新增的裝機容量超過54.6 GW,累計容量達到486.7 GW[1]。隨著海上風電的蓬勃發展,海上風力機逐漸增多,且多接近貿易繁忙的海運路線,故服役期內的海上風力機基礎易受船舶撞擊[2-4]。因此,探索有效的防護裝置以減小船舶碰撞的危害,為風力機的安全運行提供保障,具有重要工程應用價值。
諸多學者對海上風力機支撐結構的船舶碰撞問題進行了研究。RAMBERG[5]模擬了不同質量船舶在不同角度下對海上風力機導管架基礎連接點的碰撞,分析了不同狀態下的導管架屈曲特性。BIEHL等[6]模擬海上風力機單立柱三樁基礎的船舶碰撞過程,研究不同船舶速度下的結構抗撞特性及基礎損傷情況,分析碰撞過程中的能量變化與結構損傷。DING等[7]通過模擬船舶以不同速度撞擊重力式基礎海上風力機,分析塔架結構的剪力彎矩特性以及重力式基礎的應力應變。AMDAHL等[8]分析了單樁基礎風力機在不同速度船舶撞擊及風載荷作用下的塔架變形、塔頂位移響應。上述研究僅考慮海上風力機受撞損傷及動力響應,未對海上風力機結構的安全防護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在海洋工程結構受碰撞過程中,防護裝置主要運用在船-船碰撞、船-橋碰撞及船-石油平臺碰撞的場合,用于海上風力機-船舶碰撞的較少。LEHMANN等[9]設計的鋼結構防護裝置能吸收碰撞過程中的巨大能量,通過試驗與數值模擬驗證了防護裝置的有效性。文獻[10]在研究船舶碰撞橋墩的過程中,提出了新型組合鋼結構的防護裝置;文獻[11]指出,在船舶與海洋平臺碰撞的過程中,橡膠護舷可以減小碰撞力和結構的損傷。
本文借鑒傳統海洋工程結構安全防護裝置的研究設計經驗,針對單樁柱海上風力機,設計出4種型式的防護裝置,模擬船舶在不同速度下與單樁柱基礎的碰撞過程,分析其能量變化、塔架應力和撞深、接觸力及塔頂風力機的響應,來驗證防護裝置的性能。
1 理論基礎
1.1 控制方程
船舶與海上風力機碰撞運動控制方程為[12]

(1)

(2)

1.2 材料本構模型
1.2.1鋼的本構方程
風力機塔架和船首材料為Q235B,單樁柱基礎和防護裝置外殼材料為Q345,參數如表1所示。由LS-DYNA提供的非線性彈塑性材料模型[13]是基于Cowper-Symonds關系式建立的[14], 可很好地模擬單樁柱基礎撞擊作用下的材料特性,如下式所示:
(3)

1.2.2橡膠的本構方程
碰撞過程中,各向同性橡膠材料的變形都是超彈性材料的均勻變形[15]。橡膠材料應變能函數有兩種表達方式:由變形張量的3個不變量I1、I2、I3表示的應變能函數W(I1,I2,I3);由主伸長比λ1、λ2和λ3表示的應變能函數H(λ1,λ2,λ3)。變形張量的不變量與主伸長比的關系式如下:
(4)

表1 部件的材料屬性參數
(5)
(6)
λi=1+εi
(7)
式中,εi為主軸方向的應變;i為張量序號,i=1,2,3。
橡膠屬超彈性材料,其應變能函數由上述形式轉化為多項式形式后,由應變偏量能和體積應變構成:
(8)

對于多項式中的應變偏量,橡膠的初始剪切模量G0、初始體積模量K0都取決于多形式的一階系數,即G0=2(C10+C01),K0=2/D1,其中,C10、C01、D1為材料常數。
對于式(8),如果N=1,則僅保留線性部分的應變能,即Moony-Rivlin模型:
W=C10(I1-3)+C01(I2-3)+(J-1)2/D1
(9)
1.2.3泡沫鋁的本構方程
泡沫鋁材料的屈服應力函數為
(10)

泡沫鋁材料隔墊的具體材料參數如表2所示。
1.3 接觸定義
為更好地模擬船舶與海上風力機基礎的碰撞過程,避免初始接觸,將兩者初始間隔距離設為0.6 m。在LS-DYNA中,將船首與海上風力機防護裝置間設置為面面接觸,塔架與樁柱之間設置為

表2 泡沫鋁材料隔墊的材料參數
自動單面接觸,避免船體穿透基礎,橡膠、泡沫鋁和外殼采用固連接觸。
碰撞過程中,船首與防護裝置接觸時的摩擦力為
Fy=μ|fs|
(11)
μ=μd+(μs-μd)e-d|v|
(12)
式中,fs為節點法向接觸力;μ為摩擦因數;μd為動摩擦因數;μs為靜摩擦因數;d為衰減系數;v為接觸面間相對速度。
船首和防護裝置外殼之間的動摩擦因數、靜摩擦因數取0.2,衰減系數取0,橡膠與塔架的靜摩擦因數為0.9,泡沫鋁與塔架的靜摩擦因數為0.4。
2 研究對象與模型
2.1 單樁柱風力機
國內某海上風電場的風力機及塔架主要參數如表3所示。

表3 3 MW風力機部件主要參數
單樁柱海上風力機上部結構由塔架、輪轂、機艙和葉片組成,其中樁基入土深度為41 m。單樁柱式海上風力機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單樁柱式海上風力機模型Fig.1 Monopile foundation offshore wind turbine model
海上風力機底部往往采取水泥澆筑等加固措施。因此,在ANSYS/LS-DYNA中將樁柱基礎在泥土中的部分假定為剛性約束,忽略樁柱水平位移。塔頂部分較為復雜且網格劃分數量巨大,占用較多計算資源,為提高效率,采用集中質量方法,用固定質量點代替風力機頂部(葉片、輪轂、機艙)的質量。
2.2 防護裝置
為保證防護裝置受船舶撞擊后,不脫離單樁柱基礎,模擬中的防護裝置質量不能超過海上風力機總質量的15%[16]。防護裝置安裝在塔架下部,內部是內徑4.5 m的橡膠,外部是一層10 mm厚的鋼制防護殼,整體結構高6 m,質量70.7 t,占海上風力機總質量的9.6%,符合設計標準。泡沫鋁密度更小,故設計表4所示的4種型式防護裝置。

表4 防護裝置材料和厚度
對防護裝置進行網格劃分,橡膠和防護殼采用掃掠的網格劃分方法,防護殼單元尺寸為0.1 m,橡膠單元尺寸為0.2 m,有限元模型如圖2所示。

圖2 防護裝置有限元模型Fig.2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protective device
2.3 船舶模型
固定式基礎的海上風力機所處海域為近海,來往船只種類較多,本文選用較為常見的散貨船,船首型式為飛剪型,主要尺寸參數如表5所示,實體模型如圖3所示。模擬過程中,忽略碰撞船舶的變形,假定碰撞船舶為剛性體。

表5 船舶結構主要參數

圖3 碰撞船舶模型Fig.3 Collision ship model
碰撞船舶主要分為船首、船身和船尾,通過LS-DYNA中的關鍵字*ELEMENT_MASS控制船舶整體的重心和質量。為更好地分析防護裝置對塔架主體結構的保護作用,本文模擬2 000 t、5 000 t的船舶以1 m/s、2 m/s、3 m/s的速度與單樁柱海上風力機的碰撞,船舶行駛速度沿x軸正方向。
碰撞過程中,船舶與海水的相互作用不可忽略,故通過流固耦合模型或附加質量模型表示船舶與海水的相互作用過程[17-18]。船舶與海水相互作用的耦合計算復雜且耗時[19-20],因此本文中的船舶與水的相互作用選用附加質量法。
在船舶有限元模型網格劃分中,單元厚度為20 mm,網格劃分單元尺寸為0.2 m[21]。
3 結果與分析
3.1 無防護裝置
3.1.1全局能量分析
船舶撞擊單樁柱海上風力機的過程中,船舶的初始動能轉化為船舶和塔架的內能(變形能)、船舶的剩余動能,以及接觸摩擦產生的滑移能、顯式分析中采用縮減積分產生的沙漏能、塔架在阻尼作用下產生的阻尼能。數值模擬計算中,一般以沙漏能應小于總能量的5%作為判斷數據準確性的依據[14]。圖4分別為5 000 t船舶以不同速度v撞擊塔架下端全局的能量曲線圖。

圖4 5 000 t船舶撞擊塔架的能量曲線圖Fig.4 Energy curve of 5 000 t ship impacts the tower
由圖4可知,沙漏能低于總能量的1.5%,表明有限元模型合理,計算結果準確。由圖4a可知,碰撞過程中,結構變形能最大值達到3.93 MJ,碰撞結束后,結構變形能在2.72~2.80 MJ之間波動;碰撞系統動能減小至接近于0后,反彈至1.29 MJ,然后在海水阻尼作用下緩慢減小。由圖4b可知,碰撞過程中的結構變形能最大值達到3.63 MJ。由于防護裝置中的橡膠的超彈性作用,動能先減小到0.52 MJ,然后迅速回升,此時橡膠受沖擊壓縮后反彈撞擊船舶,減弱了對塔架主體的傷害。
3.1.2塔架結構分析
圖5是船舶沖擊單樁柱基礎碰撞區域的應力云圖(船舶碰撞區域的正視圖)及塔架撞深截取的云圖。由圖5可知,船舶速度增加時,結構損傷程度也隨之增加。撞擊速度v為1 m/s時,塔架最大應力在碰撞區域,且未發生變形;撞擊速度為2 m/s、3 m/s時,船舶碰撞區應力迅速下降,碰撞區域中心出現應力最小值,開始產生明顯變形;撞擊速度為4 m/s時,塔架的變形δ最大,最小應力集中區域范圍擴大,說明此時的塑性區域吸能特性使應力集中區域的能量釋放。

圖5 塔架下端結構應力及撞深Fig.5 Stress and depth of tower structure
圖6所示為不同速度下 5 000 t船舶碰撞單樁柱海上風力機的接觸力曲線,為更直觀分析接觸力曲線,以速度4 m/s行駛的船舶為基準,并將接觸初始點調至相同起點。

圖6 不同速度船舶撞擊接觸力曲線Fig.6 Contact force curve of ship impact at different speeds
由圖6可知,碰撞初始階段的船舶接觸力曲線高度重合,且處于線性階段,此時的碰撞屬于彈性碰撞;隨著船速的增加,接觸力曲線快速分離,曲線的非線性波動特征顯著,接觸力曲線每次由波峰至波谷的過程存在力的卸載,表明船首與塔架變形損傷過程在不斷變化;4 m/s速度時,接觸力在1.5~1.9 s的卸載最顯著,1.9~2.6 s的接觸力并沒有降低,結果說明,此時的塔架發生了較大的變形,初始動能主要轉化為船舶的結構變形能,符合圖5所示,隨著船舶速度增加,塔架受撞擊后的深度增加。
船舶以4 m/s速度碰撞時,0.50~0.54 s內,船舶開始與風力機塔架碰撞,接觸力線性增長,此階段的碰撞為彈性碰撞,塔架主要產生彈性變形;0.54~1.44 s時,接觸力總體呈上升趨勢,最大值為13.9 MN,此階段碰撞為彈塑性碰撞;1.44 s后,曲線具有明顯的非線性波動特征,直到碰撞結束(3.80 s),此階段的碰撞為塑性碰撞。對比分析每個階段碰撞持續的時間可知,塑性碰撞的持續時間2.44 s明顯長于彈性碰撞的持續時間0.04 s和彈塑性碰撞的持續時間0.9 s。
3.2 橡膠防護裝置
3.2.1塔架結構變形能分析

圖7 塔架下端結構變形能Fig.7 Structural deformation energy of the tower
圖7所示為2 000 t船舶以不同速度撞擊海上風力機時,塔架受碰區的結構變形能。由圖7可知,碰撞過程中,有防護裝置的最大結構變形能都小于無防護裝置的,表明防護裝置吸收了碰撞能量,減少了塔架的變形;隨著船舶速度的增加,有防護裝置的塔架在船舶速度分別為1 m/s、2 m/s、3 m/s的結構變形能相對于無防護裝置分別減少了35.9%、26.6%和14.6%,說明該防護裝置對于低速船舶的效果更好。
3.2.2接觸力分析
主從算法在求解的過程中,在垂直于主面的方向上施加一個作用力(接觸力)以阻止從屬節點的穿透。由圖8可知,無防護裝置時,在碰撞開始階段,接觸力曲線線性增長且斜率較大,此時的碰撞屬于彈性碰撞;此后,曲線的非線性波動特征逐漸顯著,這表示船首構件和塔架的變形或受損,此碰撞為彈塑性碰撞;增加防護裝置后,塔架也存在由彈性變形到彈塑性、塑性變形的階段,但碰撞持續的時間都在延長,在船舶速度為1 m/s、2 m/s、3 m/s時,最大接觸力分別減少了45.6%、45.0%、36.1%。

圖8 不同速度船舶撞擊海上風力機接觸力曲線Fig.8 Contact force curve of ship impact on offshore wind turbine under different velocity
3.2.3塔架應力云圖
由圖9可知,船舶以2 m/s速度撞擊無防護裝置塔架時,應力最大值達到278 MPa,超過屈服極限235 MPa,而船舶以3 m/s撞擊有防護裝置的塔架時,應力僅有193 MPa,由此可知,防護裝置能很好地保護海上風力機基礎結構并吸收船舶初始動能,減少碰撞載荷,避免應力集中。

圖9 塔架應力云圖Fig.9 Von Mises stress of tower
3.3 三種防護裝置的對比
為分析橡膠、泡沫鋁及兩種材料組合的防護裝置性能,模擬5 000 t船舶以1 m/s速度正面撞擊塔架下端。圖10所示為3種型式防護裝置下,海上風力機的動力響應。3種防護裝置中,由塔架下端的結構變形能、接觸力、塔頂位移及塔頂加速度響應參數對比分析可知,防護裝置C即橡膠和泡沫鋁組合,抑制塔頂動力響應的效果更好。

圖10 3種防護裝置的響應對比Fig.10 Response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3 protective devices
3.4 防護裝置材料鋪層順序響應的對比
橡膠有很好的超彈性,泡沫鋁有高阻尼減震性能及良好的沖擊能量吸收率。為探究防護裝置鋪層順序對撞擊過程中風力機響應的抑制效果,設計型式C、D兩種防護裝置,模擬工況為5 000 t船舶以3 m/s速度正面撞擊塔架下端。圖11所示為C、D防護裝置下,海上風力機的響應特性。D型防護裝置的結構變形能、接觸力、加速度響應稍小于C型防護裝置,對塔頂位移響應抑制的效果明顯。

圖11 2種防護裝置的響應對比Fig.11 Response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2 protective devices
4 結論
(1)無防護裝置時,撞擊過程中的塔架應力很快超過材料的屈服極限,撞深隨船舶速度增加而增加。
(2)船舶速度在1 m/s、2 m/s、3 m/s時,A型防護裝置的結構變形能分別是無防護裝置的22.13%、23.80%和42.58%,最大接觸力分別是無防護裝置的54.38%、54.95%、63.92%,碰撞持續的時間都在增加。
(3)由響應參數的對比分析可知, C型(橡膠和泡沫鋁組合)防護裝置對響應的抑制效果較A型、B型更好。
(4)D型防護裝置對塔頂位移響應的抑制效果明顯,但在結構變形能、接觸力、加速度響應與C型較為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