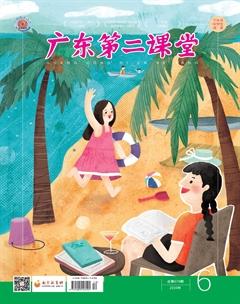讀書(shū)不負(fù)少年心
羅杵增
我在鄉(xiāng)下長(zhǎng)大,從小喜歡讀書(shū)。
慢慢在小鎮(zhèn)里上了中學(xué),發(fā)現(xiàn)自己更喜歡讀“古時(shí)候的書(shū)”,比如《論語(yǔ)》,比如《道德經(jīng)》,還有《李白詩(shī)選》《古詩(shī)三十六首》這樣的集子。小鎮(zhèn)安逸,資源卻少,身邊并沒(méi)有同好,只靠著摸索,能在書(shū)店遇到一本《論語(yǔ)》已是萬(wàn)幸,出版社、版本什么的,根本沒(méi)這些意識(shí)。書(shū)里的內(nèi)容,很多地方都在半懂不懂間,看了注釋反倒更迷糊了,也找不著人請(qǐng)教,加之性子疏懶,背不下來(lái),要怎么讀下去呢?只好想了個(gè)偷懶的笨辦法:抄書(shū)。
我中學(xué)的時(shí)候,抄過(guò)《論語(yǔ)》《道德經(jīng)》。坐在書(shū)桌前,正兒八經(jīng)地裁好白紙,想象著古時(shí)候線裝書(shū)頁(yè)的樣子,自己畫(huà)上線,然后從右往左,豎著抄。
然而我終究沒(méi)有在這段時(shí)期讀好它們,反而對(duì)讀過(guò)的詩(shī)印象深刻,不需要注釋也能猜到大概,仿佛自己從詩(shī)中看到詩(shī)人,聽(tīng)到他的聲音,明白字詞背后的幽微。
人總是忍不住手癢,讀著讀著就想寫。那時(shí)也不懂平仄押韻格律,只是一個(gè)感覺(jué),大致平仄相間就對(duì)了,但“平仄”又是什么呢?可能是普通話里一二聲屬于平聲、三四聲屬于仄聲?然而讀得越多越迷茫,常發(fā)現(xiàn)在應(yīng)該仄聲的位置是個(gè)第一聲或第二聲的字。這么說(shuō)來(lái),難道不需要講究平仄嗎?好像也不對(duì)。自己寫的東西,好像是“詩(shī)”,又好像什么都不是。
這個(gè)問(wèn)題困擾了我整個(gè)中學(xué)時(shí)代,一直找不到答案,關(guān)于詩(shī)的心思漸漸就沉下去了,輕易不會(huì)泛起漣漪。直到上了大學(xué),遇上召南詩(shī)社的師兄,在兄長(zhǎng)的指引下,才真正開(kāi)始讀書(shū)。也直到這時(shí),才明白以前自己寫的都不是“詩(shī)”。
所謂“真正開(kāi)始讀書(shū)”,首先是系統(tǒng)地去進(jìn)學(xué)。最初接觸到的,是中華書(shū)局的《四書(shū)章句集注》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杜詩(shī)鏡銓》,兩個(gè)都是繁體豎排,我曾幻想過(guò)它們的樣子,拿到手時(shí),不自覺(jué)捧著輕輕翻開(kāi),整個(gè)人都嚴(yán)肅起來(lái),決定要一口氣讀完它們,但事實(shí)并沒(méi)那么配合。
繁體字是我碰到的第一個(gè)難題,很多字我都連蒙帶猜,估摸著它們“翻譯”成簡(jiǎn)體的樣子。其次最難受的是豎排,以前自己抄的時(shí)候,更多的其實(shí)是在享受這種“與眾不同”帶來(lái)的快感,真輪到自己來(lái)看這些書(shū),眼睛一時(shí)都不知道擱哪才好,讀了上行找不到下行。
這種處處卡殼的狀態(tài),讓人很不舒服,忍不住要懷疑自己“是不是這塊料”,但它很容易適應(yīng):配合《古漢語(yǔ)字典》之類的工具書(shū),硬著頭皮讀下去,不知不覺(jué)間就習(xí)慣了。
對(duì)于四書(shū),我只在《論語(yǔ)》用過(guò)力氣。有一年的春節(jié)前夕,好友方潤(rùn)生發(fā)信息跟我說(shuō):最近在家?guī)桶謰尭苫睿w會(huì)到他們的艱辛,才漸漸讀懂了《論語(yǔ)》。我正在大街上,人來(lái)人往的,看到這句話忽然想仰天長(zhǎng)嘯一聲,那瞬間有豁然開(kāi)朗的感覺(jué)。夫子在《論語(yǔ)》里面說(shuō)的,都是需要我們?nèi)ド眢w力行、一一印證的,而非空頭的大道理。
《孟子》并沒(méi)有多讀,可能跟個(gè)人性格有關(guān),不喜歡辯論。總覺(jué)得道理是即是,非即非,不以辯論結(jié)果為轉(zhuǎn)移,雖然孟子感慨說(shuō),“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但《孟子》多長(zhǎng)篇辯論,終于是缺少緣分讀進(jìn)去。至于《大學(xué)》《中庸》,用力則更少了。
說(shuō)到《論語(yǔ)》,后面還讀了錢穆先生的《論語(yǔ)新解》,那時(shí)于白文記得不牢,只好重新用老辦法,繼續(xù)抄書(shū)。不過(guò)具體的做法有所調(diào)整:繁體豎排無(wú)句讀、只抄白文,抄完再回頭斷句。
人漸漸接觸世事,心就容易躁,抄書(shū)常常走神,不時(shí)有抄錯(cuò)的,隨手劃掉接著抄。一天忽然想:既然要抄書(shū),心不在焉到連篇錯(cuò)字,時(shí)間精力豈非虛擲?若連抄書(shū)這點(diǎn)小事都做不好,那應(yīng)該是白讀書(shū)了。從此抄書(shū)前便洗干凈手,靜下心來(lái)再開(kāi)始,慢慢就好了很多。
直到現(xiàn)在我仍保持著抄書(shū)的習(xí)慣,不過(guò)近年來(lái)抄得更多的是前人的詩(shī)集。上了大學(xué)開(kāi)始學(xué)詩(shī),雖從《杜詩(shī)鏡銓》開(kāi)始,但自覺(jué)并未讀進(jìn)去。可能是年紀(jì)還小,涉世未深,而老杜的詩(shī)句常如玄鐵重劍,沉是沉了,卻得不到相感。后來(lái)讀陳沚齋先生選的黃庭堅(jiān)、黃仲則詩(shī),及吾粵詩(shī)宗黃節(jié)先生的詩(shī),受到很大震動(dòng),原來(lái)唐代詩(shī)人之外,宋代、清代及民國(guó)的詩(shī)人,作品寫得如此好。或瘦勁或深情,或兼有風(fēng)神骨力,讓我眼界大開(kāi),仿佛在跨過(guò)平仄這道門檻后,直接就被領(lǐng)進(jìn)了恢弘雄奇的世界里。
這時(shí)單純的背誦抄寫,已經(jīng)不能滿足我了,開(kāi)始學(xué)著分春館的調(diào)子擁鼻吟哦,甚至放聲諷詠。走在路上時(shí)常常會(huì)恍惚,直不知今是何世、身是何人。這么說(shuō)似乎玄了,但確是我的個(gè)人體驗(yàn)。此后再下筆去寫,筆下的詩(shī)句,也漸漸有了樣子。
不知覺(jué)間,歲月已如冰底之水,自我第一次碰到《論語(yǔ)》及《李白詩(shī)選》至今,二十來(lái)年的光景,悄然就流走了。年少時(shí)的幻想,早如煙云般消散殆盡,但從讀書(shū)中獲得的力量,卻一直支撐著我堅(jiān)定地走向遠(yuǎn)方。
- 廣東第二課堂·初中的其它文章
- 隨園往事
- 包裹起來(lái)的善意
- 讀懂母親①
- 夏日的約定
- 玉龍雪山行
- 我的畢業(yè)大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