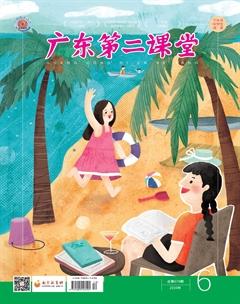端午憶舊
萬福友
小時候過端午,人們都叫過節。
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家鄉在五華。那時過節是沒有粽子的,我們沒有包粽子的習慣。但祖母和母親會做釀粄給我們過節。釀粄是一種用糯米和粘米做的食品。做釀粄要先做好餡料,餡料根據自己口味而定,我們家通常是白糖和炒過的花生、芝麻,或者是煮熟的眉豆,放入少量沙姜。然后,把糯米和粘米按照一定比例泡好,用碓舂米,用篩子篩出細細的米粉。在米粉中加入適量的水和紅色食用染料,不停地揉搓、壓扁,就做成一個個粄模。最后,在粄模里加入餡料,封口,放到大鍋里蒸熟,釀粄就做好了。釀粄有點像北方的餃子,但個頭要比餃子大兩倍。釀粄是端午的應節食品,可以作為親友間拜訪的手信和回禮。家境稍好的人家,餡料就用豬肉,一口咬下去,香香的油粘在嘴唇上,幸福極了。
與除夕、元宵和中秋節都不一樣,端午節過的是中午。中午之前,我就要把祖母提前準備好的艾草插到大門的左上方和右上方。既然是端午,午飯自然是不能馬虎的。釀豆腐是重頭戲,不過由于天氣熱,很多人家會改成釀苦瓜。此外,再殺一只雞,或者買一斤豬排骨,或者別的什么菜,端午便過得算不差了。記得我讀小學時,端午節學校就只上一個上午的課。老師自己也要回家過節,為了準備過節,很多班級的老師往往上午十一點就讓學生回去了。
我總是很期待過節。端午不像過年,大人不會給壓歲錢,但有好吃的飯菜啊!有釀粄,有客人來往,還可以跟要好的同學、兄弟一起玩鬧。大街上,雖然沒有標語,沒有張燈結彩,但人們臉上都帶著喜氣,連平時很兇的人,也變得和氣起來。
那時候,我家住在高祖父或者是更上一輩的天祖父建好的“上五下五”客家圍屋“蘊德樓”里(“上五下五”是客家圍屋的一種樣式,上下堂各四個房間,各一個廳)。當時祖母還健在,父親母親正當盛年,還有我們兄弟姐妹六人。全家九口人,生活其實過得很不容易。過節時,一年里的“春荒”還沒有過完,生產隊分的少得可憐的糧食早就化成了田里的肥料。也有例外的就是,生產隊一般都會種一些用于救命的產量極低的早稻,剛好就可以在端午節前收割,遇到好太陽,這個端午就有了新糧過節。但那時自己還小,不太懂得家里的不易,只記得母親口頭上“早年早節”的話——意思是過年過節,吃飯不能太晚。母親總是早早就開始忙碌,籌辦過節用品,像前面所講的做釀粄呀,買豬肉呀,等等,保證在端午節中午十二點之前,一家人可以團團圓圓圍在餐桌前吃飯。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過節,在縣示范農場工作的叔叔也回來了,除了買了兩斤豬肉,還帶了好多苦瓜。那時,祖母、父親、母親、叔叔阿嬸這些大人無疑都是很快活的了,我卻很不高興——好好的豬肉,全給釀進了苦瓜里去!以至于那個端午,我對向來都愛得視之如命的豬肉,居然能做到一塊都不動。
等吃過午飯,父親會很隆重地沏一壺八鄉茶,享受節日的第二波;母親和祖母則忙著收拾清洗一大堆碗筷鍋盆。而我們兄弟姐妹,就各找自己的玩伴去,或者看著大人喝茶、聊天、打牌,或者去游泳。池塘邊長著茂密的竹林,竹林自然成了懸掛我們的“萬國旗”的好地方。剝光衣服后,一個個就“撲通”“撲通”地跳進水里,開始一年中的第一次游泳。這時候母親往往不會反對我們游泳,因為:第一,池塘里的水不再冷,我們不容易手腳抽筋;第二,比我們大的少年這時也紛紛下塘玩水,萬一有事,也會有人照應;第三,老家彼時有這樣的說法,端午那一天開始,夏天真正到了,下塘游水就不再犯忌。更何況,那一天據說是不可以睡中午覺的,否則就會崩田坎。
至于粽子,我只是聽祖母說過,小時候見都沒有見過,更不用說吃粽子了。長大后,隨著讀書和工作地點的變動,也吃起粽子來。第一次是在華南師范大學讀書的時候,常在不用上課的周日早上,還躺在床上呢,便聽到“有咸肉粽賣”。那是一位20歲左右的姑娘,用單車載著一個竹制的籮筐,里面全是粽子。粽子2毛錢一個,我偶爾買一個解饞。
后來到了深圳,有一次,一位大學同學的姐姐做了粽子,同學打電話叫我過去提了好多回來;還有一次,一位族嬸也捎信來,要我們去她家拿粽子……去年端午節前,得知附近相熟的店做了很多粽子,妻子嘗過后覺得好,一下子便買了20只——原來不知不覺間,我們也習慣在端午吃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