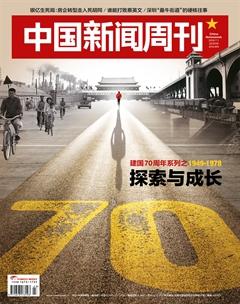云南紅土地上的農民致富經
夏男

今年新種的雪蓮果地。
從2019年農歷春節開始,彩云之南就再沒有一朵云彩飄過,持續的高溫和少雨讓云南高原上的紅土地逐漸干黃開裂。
旱情一直延續到了5月底。一場萬眾期待的降雨終于在5月的最后一天降臨在了這片紅土地之上,淅瀝的雨水,濕潤的土地,瞬間復燃了農民們的勞作熱情。
農民們戴上了斗笠,紛紛朝農田走去,90后的年輕新農人舒躍文也在其中。
站在農田前,舒躍文緊皺的眉頭終于舒展開來。一個多月前種下去的雪蓮果,因缺水,半數都還沒抽芽,但是雨水過后,他知道紅土地上的雪蓮果新苗將一簇簇地破土而出,不久后雪蓮果碩大的綠葉就能遮蓋住這片紅色的土地,散發出新的生機,帶著云南省文山州丘北縣農民共同的致富夢想,一起等待著10月收獲的到來。
脫貧,迫在眉睫
從2011年確定至今,云南省如今仍有88個貧困區縣沒有實現脫貧,這其中包括文山州的8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市),位于文山州北部的丘北縣就在其中。
這個貧困縣第一次正式走進人們的視野,要追溯至2013年。作為湖南衛視大型親子秀節目《爸爸去哪兒》第一季第三個外景拍攝地,丘北縣普者黑村自此一夜出名,但鏡頭外的人們可能怎么也不會把這片有山有水有荷花的世外桃源與貧困聯系在一起。
擁有典型喀斯特地貌的丘北縣,山區、半山區、巖溶地貌、石漠化等問題突出,怪石嶙峋的土地就如同一個個天然的漏斗,當地農民就是打再深的井,也難以找到水源。靠天吃飯,成為當地農業生產的普遍現狀。
據統計,目前丘北縣共有貧困行政村91個,建檔立卡貧困戶17468戶82629人。與中國的許多農村一樣,丘北185萬畝耕地上,雖然常有各種普惠政策落地實施,但結果卻是脫貧成效并不顯著。因為貢獻主要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農民,始終處于價值鏈條的底端。農業仍然是受流通環節制約最嚴重的行業,土地、人力甚至產品,在產業鏈中的價值并不高。
上海援滇干部聯絡組文山小組組長、丘北縣副縣長黃海濱表示,要想在2019年實現整縣脫貧摘帽,紓解丘北縣農業發展的困局,需要為丘北的農特產業探索出一條 “新業態”的脫貧之路。
由拼多多打造的創新扶貧助農新模式“多多農園”試點項目給云南帶來了新的希望。
據拼多多市場部負責人介紹,“多多農園”要實現的是原產地“最初一公里”和消費端“最后一公里”的直連,通過產業新模式,讓農戶成為全產業鏈的利益主體。? ? ? ? 就在今年的4月26日,拼多多還與云南省人民政府簽訂了五年的戰略合作協議,按協議要求,拼多多5年內要在云南省落地100個“多多農園”,主要涉及云南的優勢產業,比如像茶葉、核桃、雪蓮果、花椒、菌類等特色產業。

經過近2個月的溝通和考察后,膩腳鄉年輕村民舒躍文和施進剛被遴選為當地“新農商”帶頭人。
雪蓮果就是文山丘北縣“多多農園”項目的主打產品。
? ?“拼”出來的網紅爆果
雪蓮果,一個被稱為“人間仙果”的菊科草本植物,原產于南美安第斯山脈,至今已有500余年的食用歷史,因其富含低聚果糖和酚酸,具有腸道調節、免疫力調節、降血脂、減肥和保養皮膚等保健功能而頗受歡迎。
云南作為中國內地最早引入種植雪蓮果的地區之一,雪蓮果曾一度被當地農民寄予了發財致富的厚望。
但豐滿的夢想與骨感的現實總是同行而至。當年的盲目擴種、高廢果率和小眾的消費市場,以及從田間地頭到消費者的餐桌盤間繁多的交易及運輸環節,讓首批“嘗鮮”的雪蓮果云南種植農戶鎩羽而歸。
經此一役,被農民當作是脫貧致富法寶的雪蓮果,就此被“打入了冷宮”。
轉機出現在2016年底。
在消費升級和電商平臺農產品“拼購”模式崛起的背景下,具有電商意識的一批云南新農戶開始在拼多多平臺售賣雪蓮果,一度沉寂的雪蓮果,突然有了要火起來的前兆。
截止到2018年底,早先被棄種的雪蓮果在拼多多電商銷量的巨大拉動下一躍成為網絡爆紅水果之一,僅2018年全年,雪蓮果在拼多多平臺就賣出了480萬單,近2萬噸的銷量,直接帶動銷售收入達8000萬元。雪蓮果自此也成為文山州丘北縣既煙草、三七之外新的農貨標簽,種植面積從6萬畝一舉擴大到了2018年底的9萬畝。
這樣的反轉,來源于市場需求對生產供應關系的倒推。
據拼多多副總裁井然介紹,“多多農園”是通過借助人工智能和社交分享手段,通過分享讓貨找到合適的人,進而精準助推了云南雪蓮果的銷售。
除此外,拼多多還正在為包括雪蓮果在內的農產品加速打造“天網”和“地網”,“天網”即是依托分布式人工智能的優勢,基于消費者的需求,打造的中央農貨處理系統,可以對覆蓋農產區的地理位置、特色產品、生產周期進行有效的歸集,在各個農產品成熟期匹配給消費者,使傳統的農產品消費突破時間和空間,真正實現小農戶無縫連接大市場;“地網”則是通過5年時間的建設,覆蓋全國主要農產區,為4.43億并且仍在高速增長的拼多多用戶服務。而其最終目標,則是要實現消費端“最后一公里”和原產地“最初一公里”的直接連接,為消費者提供平價高質農產品的同時,更快速有效帶動深度貧困地區農戶脫貧致富,并實現產業化發展。
把利潤留給農民
有了銷量,雪蓮果種植農戶就能致富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
作為整個產業鏈條中最初始端的種植農戶和最終端的銷售平臺,舒躍文與“多多農園”一起算過一筆賬。
雪蓮果地頭的收購價平均為0.5元/公斤,代辦費0.1元/公斤,物流成本1元/公斤,耗材、人工0.6元/公斤。拼多多平臺銷售價格以4元/公斤居多,經銷商利潤在1.8元/公斤左右,付出勞作成本和時間成本最高的農民成為了整個環節收益最低的人群,始終處于價值鏈條的底端。
這種情形并不僅僅體現在文山雪蓮果產品上,“多多農園”保山市咖啡豆項目也面臨著同樣的難題。
據數據顯示,中國咖啡豆消費量從2006年的2.59萬噸,上升到2017年13.45萬噸,年均增長率達20.75%,為全球平均增長率的10多倍。按理說中國咖啡消費市場的迅速增長理所應擔的能帶動咖啡種植戶的收入增長,但事實卻是相反的。
根據金融數據研究服務平臺JingData測算,咖啡產業鏈上游種植環節生豆價值貢獻約17.1元/公斤,中游深加工環節烘焙豆價值貢獻為83元/公斤,下游流通環節價值則暴增至1567元/公斤,三個環節利益分配占比為1:6:93。提供土地、人力及咖啡豆的上游農戶環節,留存利益少之又少。當地很多農戶更是一輩子都沒有喝過一杯星巴克,雖然他們直接為星巴克中國供貨。
“做多多農園的項目,歸根結底是想建立一套全新的模式、機制,并且有效地推廣復制。這個模式和機制里面,目標最終是實現人才的鄉土化、產業持久化、利益農戶化,實現消費帶動,產業促進,人才孵化。”井然坦言,他們希望通過推動這些和上游生產者緊密結合的模式,讓更多(農)人受益。
“新農商”機制應運而生。
“新農商”機制是以檔卡戶為集合的合作社為主體,建立品牌,培育新模式,這也是“多多農園”最大的挑戰。
在該模式中,拼多多不再只是單一的提供銷售平臺和數億的人口流量,而是需要縱向深入,向農戶提供資金、技術和渠道的全方位支持,大規模培育本土青年成為“新農人”帶頭人,從扶植到扶智,讓后者按合約持有分紅權限,剩余利益全部歸屬檔卡戶。
“通過‘新農商機制,拼多多將重點探索如何讓農人變農商,讓農村有現代化企業。只有讓農戶成為產銷加工一體化的主體,才能實現人才鄉土化、利益農戶化。” 多多大學負責人藍天表示。
2019年6月,丘北縣膩腳鄉新農商公司正式成立,4個貧困村141位建檔立卡貧困戶,成為首批簽約新農商。“多多農園”還通過“贈股”的方式,讓檔卡戶無償成為股東,公司的所有運營利潤,都面向全股東分紅。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仇煥廣教授分析認為:“‘多多農園是需求推動供給的典型,它切實命中了‘人才留存和‘利益分配這兩個當下農產區最核心的問題。如果‘多多農園能完成預設目標,不僅將締造企業參與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的標桿,更將推動更多農產業發生巨大變化。”
擁有基層干部和電商運營的經驗的90后舒躍文,被選為新農商公司的帶頭人,他激動地表示:“現在有拼多多手把手的來幫我們做電商,我們村的雪蓮果產業一定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