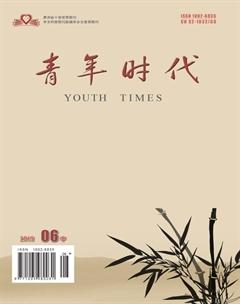金文與《詩經(jīng)》戰(zhàn)爭詩的比較研究
徐夢飛
摘 要:運(yùn)用比較法、例證法,從詞匯、內(nèi)容、體裁等方面,對《虢季子白盤》等金文和《詩經(jīng)》中與玁狁的戰(zhàn)爭詩進(jìn)行比較研究。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由于流傳方式以及敘事角度的不同,兩者之間有諸多地方的不用,但由于記載的都是與玁狁之間的戰(zhàn)爭,又有其相同之處,將兩者進(jìn)行對比研究能發(fā)現(xiàn)諸多問題。
關(guān)鍵詞:金文;《虢季子白盤》;《詩經(jīng)》;玁狁
一、引言
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可見,古人對于祭祀和軍事是相當(dāng)重視的,這在古代典籍中多有體現(xiàn),而金文中也有不少關(guān)于戰(zhàn)爭的描寫,《虢季子白盤》便是其中一篇。銘文共111字,記敘了夷王十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在洛水的北岸攻打獫狁,殺敵五百,俘虜五十人,立下赫赫戰(zhàn)功,受到王宴請和賞賜的事。
《虢季子白盤》記敘的是與獫狁之間的戰(zhàn)爭,王國維在《兮甲盤跋》中說:“彝器中紀(jì)伐獫狁事者三,一合肥劉氏所藏虢季子白盤,一上虞羅氏所藏不期敦,一即此盤也。(按:兮甲盤)。”然而,據(jù)考證,除王氏上述所說三個青銅器外,還有多友鼎,也記載了關(guān)于討伐獫狁的戰(zhàn)爭。這四篇銘文記敘內(nèi)容不同,然記敘風(fēng)格、記敘方式多有相似,又都是記載與獫狁之間的戰(zhàn)爭,在研究時可相互借鑒。
《詩經(jīng)》中多戰(zhàn)爭詩,在這些戰(zhàn)爭詩中,有四首詩談到了獫狁,分別是《采薇》、《出車》、《六月》以及《采芑》。這四首詩分別從不同角度描述了與獫狁之間的戰(zhàn)爭。
《詩經(jīng)》作為傳世文獻(xiàn),青銅器銘文作為出土文獻(xiàn),受時間以及各種因素的影響,其語言文字等已有了很大差異,且《詩經(jīng)》與金文的敘事體裁的不同,又導(dǎo)致兩者的敘事風(fēng)格以及側(cè)重點(diǎn)不同。然而兩者同樣記敘討伐獫狁的戰(zhàn)爭,又使其內(nèi)容、語言等有相似之處。利用這種相似中的差異,我們可以對兩者進(jìn)行比較研究,從而解決各自的疑問之處,如金文中“折首執(zhí)訊”的“訊”字考釋為“訊”字,便是參考了《詩經(jīng)》中“執(zhí)訊獲丑”一句。因此,進(jìn)行出土文獻(xiàn)與傳世文獻(xiàn)的比較研究仍然很有必要。本文將以《虢季子白盤》為主,結(jié)合其他三篇銘文,從語言、內(nèi)容、風(fēng)格幾個方面,同《詩經(jīng)》中的四篇戰(zhàn)爭詩進(jìn)行比較研究。
二、例證分析
(一)內(nèi)容比較
金文與《詩經(jīng)》不管從敘事角度、敘事方法還是敘事內(nèi)容來說,都很不相同,但又有其相似之處。下面就內(nèi)容的敘事人稱、時間、意象幾方面來分別進(jìn)行比較。
1、人稱方面
上文中提及的四個青銅器銘文中,敘事均用第三人稱,具體是何人并不確定,但卻是器主在制作青銅器并刻銘文時委托的那人所寫。由于是第三人稱,在敘述戰(zhàn)爭情況以及戰(zhàn)后器主受到君主賞賜以及為何而作此器物的原因時都較為冷靜客觀且面面俱到,又由于受器主影響,在敘述中對器主也是大加稱贊,記載其所立的戰(zhàn)功以及得到的榮耀。但是個人感情流露并不明顯。
而上述《詩經(jīng)》中的四篇戰(zhàn)爭詩,在敘事時既有第一人稱的用法,又有第三人稱的用法,但根據(jù)內(nèi)容來說,進(jìn)行敘事的人應(yīng)該都是戍守邊疆的士兵。其通過詩歌所表達(dá)的情感也有不同,有描述行軍之苦,渴望早日歸家的,如《采薇》:“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有憂愁外患,希望輔佐君王的,如《六月》:“玁狁孔熾,我是用急。”;有崇拜自己的將軍,稱贊其戰(zhàn)功的,如《采芑》:“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當(dāng)然也有兼具上述三方面的,如《出車》:“王事多難,維其棘矣。”足以看出士兵的思想感情復(fù)雜,感情流露明顯。其所見所感與寫銘文的人不同,因而所寫內(nèi)容的側(cè)重點(diǎn)也多有不同。
2、時間方面
金文中對時間描寫較具體,其中《兮甲盤》記錄的時間“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最為詳細(xì)。“既死霸”指農(nóng)歷每月二十三至晦日這段時間。《虢季子白盤》所記時間卻是虢季子白受賞賜后作寶盤的時間,根據(jù)“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推斷戰(zhàn)爭應(yīng)發(fā)生于頭一年的歲末,至于《多友鼎》和《不期簋》的年代就不太好確定到哪一年了。
《詩經(jīng)》四首詩中,對時間的描寫就遠(yuǎn)不如金文具體了。只有《采薇》、《六月》兩首詩提到戰(zhàn)爭發(fā)生的月份,《采薇》發(fā)生在農(nóng)歷十月份,“曰歸曰歸,歲亦陽止”,“陽”,指農(nóng)歷十月;《六月》發(fā)生在農(nóng)歷六月份,“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至于年代,只有從參加戰(zhàn)爭的人物推算大約年代,但這也只能推算出是哪個王朝間發(fā)生的事。
3、意象方面
金文多側(cè)重于對戰(zhàn)爭過程以及戰(zhàn)后賞賜進(jìn)行介紹,因此主要意象有以下幾方面:
(1)地名。多指敵人侵犯地區(qū)以及與敵人作戰(zhàn)地區(qū),如下:筍地:“癸未,戎伐筍”(《多友鼎》);?地:“甲申之晨,搏于?”(《多友鼎》);龏地:“或搏于龏,折首卅又六人”(《多友鼎》);楊冢:“至于楊冢,公車折首百又十又五人”(《多友鼎》);西俞:“獫狁廣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不期簋》);高陶:“女以我車宕伐獫狁于高陶”(《不期簋》)。
(2)戰(zhàn)利品。多寫明戰(zhàn)利品之具體數(shù)目,如下:敵人首級:“折首五百”(《虢季子白盤》);俘虜:“執(zhí)訊五十”(《虢季子白盤》);兵車:“孚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多友鼎》)。
(3)賞賜。配有四馬的戰(zhàn)車:“王睗乘馬,是用左王。”(《虢季子白盤》);弓箭:“睗用弓,彤矢其央。”(《虢季子白盤》);鉞:“睗用戉,用政蠻方”(《虢季子白盤》);馬匹、駒車:“王易兮甲馬四匹,駒車。”(《兮甲盤》);田地:“易女土田”(《多友鼎》)。
《詩經(jīng)》四首詩,多是根據(jù)邊疆士兵行軍途中所見所感而作,因此詩中意象也多與士兵的生活和作戰(zhàn)場面有關(guān),主要意象有以下幾方面:
(1)地名。焦獲:“玁狁匪茹,整居焦獲。”(《六月》);鎬地、方地、涇陽:“侵鎬及方,至于涇陽。” (《六月》);太原:“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六月》);朔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出車》)。
(2)作戰(zhàn)用品。戰(zhàn)車:“戎車既駕,四牡業(yè)業(yè)。”(《采薇》)、“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六月》);戰(zhàn)馬:“戎車既駕,四牡業(yè)業(yè)。”(《采薇》);弓箭、箭袋:“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采薇》);軍服:“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六月》);旗幟、飄帶:“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六月》);戰(zhàn)鼓:“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采芑》)。
(3)植物。薇菜:“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采薇》);棠棣:“彼爾維何?維常之華。”(《采薇》);楊柳:“昔我往矣,楊柳依依。”(《采薇》);黍稷:“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出車》);卉木:“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出車》);芑菜:“薄言采芑,于彼新田”(《采芑》)。
(4)動物。鱉、鯉魚:“飲御諸友,炰鱉膾鯉。”(《六月》);草蟲、蚱蜢:“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出車》);倉庚:“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出車》)。
(5)其他。雨雪:“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采薇》);書信:“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仆夫:“召彼仆夫,謂之載矣。”(《出車》);俘虜:“執(zhí)訊獲丑,薄言還歸。”(《出車》);命服:“服其命服,朱芾斯皇。”(《采芑》);鉦人:“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采芑》)。
通過金文和《詩經(jīng)》中的主要意象的對比能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在敘事時側(cè)重點(diǎn)不同,金文著重記錄戰(zhàn)爭發(fā)生的始末,對于地名、戰(zhàn)利品以及戰(zhàn)后賞賜等記錄詳細(xì)。而《詩經(jīng)》卻多是行軍戰(zhàn)士的所見所感,側(cè)重于對日常生活以及訓(xùn)練場面的描寫,也因此詩中意象較為豐富。
(二)詞匯比較
下面根據(jù)《虢季子白盤》行文順序來比較研究金文與《詩經(jīng)》中詞匯方面的異同:
1、不顯:“不顯子白”一句,“不”通“丕”,大。丕顯,為顯赫之義。此句意為:顯赫的子白。而《采芑》中亦有與此用法相似的一句:“顯允方叔”。“顯允”后同樣接人名,且語氣與《虢季子白盤》相同,都有贊美主人公(子白、方叔)之義。《毛詩正義》中未對“顯允”一詞進(jìn)行解釋,但卻有將這一詞解釋為“高貴英偉”義的,這就與“顯赫”義相差較大。
“顯”義自不必說,“允”字《說文》、《爾雅》中皆釋為“信”,《玉篇》釋為“當(dāng)”,《增韻》釋為“肯”,皆無“大”義。然而比較《虢季子白盤》與《采芑》兩文的內(nèi)容、語氣以及詞匯用法,“不顯子白”與“顯允方叔”語義應(yīng)相同,則“顯允”也應(yīng)是“顯赫”義,將“顯允”解釋為“高貴英偉”便有欠妥當(dāng)了。“赫”即“大”,則“丕”、“赫”、“允”在此處意思應(yīng)可互通,都為“大”義。
2、搏伐:“搏伐獫狁”一句,“”,同“搏”,搏斗。“伐”即“進(jìn)擊征伐”。《六月》中與此用法相同的是:“薄伐玁狁”一句。《正義》未對“薄伐”進(jìn)行解釋。而查“薄伐”義,一般直接將其釋為“征伐”。《出車》中:“薄伐西戎”一句,當(dāng)與此用法相同,《正義》釋為;“移伐西戎”、“薄往伐西戎”。則“薄伐”即“移伐”,與“搏伐”義相同。因此,“薄”亦應(yīng)同“搏”,為“搏斗”義。
3、孔:“王孔加子白義”一句,“孔”,副詞,非常。“孔又光”字釋為與“顯”字義相近也正是由于“孔又光”與《大雅·韓奕》: “不顯其光”義近。因此,“孔”當(dāng)與“不”義近,為“大、甚”之義。
《詩經(jīng)》中亦有與此用法相同的“孔”字,如:《采薇》:“玁狁孔棘”,《六月》:“玁狁孔熾”,《正義》:“孔,甚。”亦可與此互證。
4、央:“彤矢其央”一句,“央”,鮮明。《出車》:“旂旐央央”,毛傳:“央央,鮮明也。”《六月》:“白旆央央”,毛傳:“央央,鮮明貌。”則“央央”與此句“央”用法相同,則單字“央”可釋為“鮮明”,重言“央央”亦可釋為“鮮明”。日后做研究也應(yīng)注意這一點(diǎn)。
此外,金文與《詩經(jīng)》的文章體裁有所不用,《詩經(jīng)》的體裁是詩歌,因此具有詩歌的顯著特點(diǎn)即押韻,而金文體裁類似散文,一般不具有押韻的特點(diǎn),但《虢季子白盤》中句末之“盤、方、陽、王、光、王、央、方、疆”等卻具有押韻的特點(diǎn),將其結(jié)合《詩經(jīng)》來進(jìn)行研究,可用于研究上古韻部。
參考文獻(xiàn):
[1]劉翔,陳抗等.商周古文字讀本[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7.
[2]李學(xué)勤.十三經(jīng)注疏·毛詩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
[3]王國維.兮甲盤跋[A].觀堂集林[C].北京:中華書局,1959.
[4][漢]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