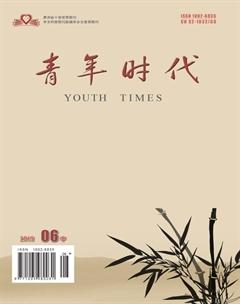巴山蜀水·川戲新語
張鵬飛 王佳毅
摘 要: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應對傳統川劇文化進行活化設計研究,如何使空間設計創新又不失識別性呢?公共空間設計創新怎么樣才能實現文化輸出呢?針對以上問題,將以川劇劇種主題空間設計作為切入點,對傳承與發展傳統戲劇的方式進行革新;以傳統戲劇演變形式變換空間;并采取多維角度架構多層次的豎向空間進行組合呈現,達到預設新韻川劇更加精準的文化空間體再現。
關鍵詞:川劇活態傳承;空間動態革新
近年來非物質遺產的生存環境遭到破壞,傳統戲劇類非物資文化遺產面臨失傳的危險;川劇文化面臨著“人才斷層、新劇創作乏力、名角稀缺”等主要問題;川劇還面臨著受眾面薄弱的危機;何以打造以繼承傳統為底色,致力于探索創新型空間為補給口的問題尤為凸顯,這為促進傳統戲曲文化傳承與發展尋求了一定的目標定位。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不斷提高,廣大群眾對于美好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提高,川劇作為國家第一批非遺文化,悠久的歷史底蘊與其獨特的戲劇表演方式也深受大眾喜歡,傳統戲曲舞臺也逐漸回歸群眾視野。
川劇,起源于唐朝,盛興于明清。由形式多樣的戲劇類型逐漸演變成以昆腔、高腔、胡琴腔(皮黃)、彈戲和民間燈戲形成的五種主要戲劇腔調,經長江流域帶蔓延開來,正是在這種戲曲文化間相互激蕩的長河中,日久逐漸形成共同的曲調風格,直至清末時期將民間地方“川戲”改稱為“川劇”。
川劇觀演空間歷史的演變:最開始游走于田間院壩,題材多是關于勞動人民在田間自娛自樂的一種活動形式;川劇最常見的一種演出形式是坐落于臨時空地的多頻換演,后逐漸演化成地方戲曲,并在有特定意義的節日進行演出;同時戲劇也成為宗祠廟宇承接紅白喜事、祭祀豐收等重要節日表演的劇種之一;隨時間的推移,川劇進而在地方戲臺的演出逐步規模化,私人化;由于川劇特定的歷史淵源,由原啟在各地水路交通進行巡演;發展到較為正式的公館會所輪番場演,因此各個地方的戲曲文明匯聚在四川這塊盆地上開花結果,綻放出多姿多彩的川劇戲曲劇種文化;直至改革開放以后的現代性劇院,應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精神層面的追求探而未止,傳統戲曲將開始重新回歸現代舞臺;對于未來川劇觀演空間形式的定位將會走向何方,也風韻了川劇文化本身多變性格更多的隱音秘語,給演員與觀眾在相應角色的扮演上書寫了更加復雜的多重關聯性,也為傳統戲劇并駕現代科技技術成果,孕育出了多種未知情態果實而積淀新的話語。
基地位于重慶渝中半島東水門區塊,該場地北望東水門大橋,東接城市主干道,西臨長江流域,場地占地面積約為8000㎡,高架橋及碼頭貫穿整個場地交通便利,場地內地勢落差懸殊,地貌地形復雜。東水門是古代重慶碼頭文化起源與川劇戲曲文化蓬勃發展演進的重要見證,有極高的文化價值,旅游價值及藝術價值。原有區域周邊具有典型的民居建筑群落、戲劇文化發源地、城市文化中心等資源。場地東北側為湖廣會館;東臨東水門古城門與長江,歷史底蘊濃厚;周邊旅游資源豐富,周圍環繞解放碑、朝天門、洪崖洞等著名景點;而場地內地勢落差較大,有眾多的高切坡與五廢地塊,場地地形地貌人為破壞性比較大無自然綠色景觀,周圍人群所涵蓋的比例大于場地環境承載量。
對于上述的條件與問題,設計的整體策略將采用橫縱交叉式來分析推導表現,橫向思維主要比擬戲劇幕景式漸現,第一幕字水始幕,第二幕入相觀心,第三幕巴山蜀水,第四幕川蜀靈音,最后一幕為朝辭彩云,縱向主要從文化屬性、承載空間、表現形式、聲景營建四方入手.網格式對應推導,將川劇文化屬性中鳴音的器物、臉譜元素、起源發展的文化脈絡、唱腔與不同屬性觀演空間變化、戲曲服飾等相關內容沉淀,分別作用于斜切谷兜式場地、覆土式場地、高山流水地拔式場地、中心正負相向層疊式場地、登高望遠崖邊式場地地形中,營造出不同的空間效果,巴山蜀水殤引導出整體空間文化脈絡與主入口集散的功能;利用覆土的遮隱塑造冥思思索地帶,猶如閑庭而靜知的情感帶入;行徑至空間第三幕時,是對川劇文化時間段的編排鳴奏,有意引導觀者駐足交流體驗,更好的對傳播川劇文化埋下伏筆;在步入整個劇幕的高潮時,必先是讓觀者達到身行腦憶的姿態,徑憩吟賦的狀態,輾轉回望繼續尋覓,霎時步入眼簾的是帶有川東濃音的戲會縈環景象,分散于視野之上、中、下各具一格,層層疊映而出場,有傳統的戲樓、互動式的臨時參演戲臺、地下布景式的圍合戲臺,觀摩體驗戲劇人員背后曲調生活等相關的溯源延展;推進到基地的最后一幕,也是川劇最精粹、最戲曲化的綜合性文化動脈,也是整個川劇活化研究的重要展示空間所在所載,連接兩者的紐帶是賦有重慶多位步道塑形成景的特色方式而成,不僅領略揚長山道的寂靜與道然,也是使觀者身心得到短暫的舒緩;位于基地的最高峰即容一覽眾山小的態勢,從場名之間就感受到戲劇散發的獨特魅力與深厚的文化底蘊,靜靜矗立在暮后黃昏時分,清晰的建筑外部形態逐漸流露出巨大疊層式的單面坡屋頂與單立切面的錯位交織,筆者試著從傳統的營建民居中找尋地域的影子,將其夸大表現,也是對川劇依附在場所空間的一種精神象征。
基地第一幕為“字水始幕”,字水為重慶的本源,第一幕作為巴山蜀水殤的啟帆,意義直至川戲是中國傳統戲曲劇種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情源。而川劇由昆區、高腔、胡琴、彈戲、燈調五種聲腔組成,因此空間將通過五種聲腔的交相融匯,延展至五種聲腔所鳴音的器物屬性,利用其相互間的共性與差異性作為空間構成的形態元素來進行編制組合呈現,且回應字水始幕的歷史訴求與地域文化的再現奠定基石。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命門,當行徑到一個命門的時候,看似前方就是揭開答案的命鎖,或已經嘎然而止了,其實輾轉回望,眼前的命數已經重置變換;然川戲的精髓就在于其多變性,轉瞬即逝,從不循規蹈矩,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文化情節使筆者派生出將川戲對于人生觀、世界觀的感知與遐想坐落于此空間場域中,進行渲染表現。
入相觀心作為第二幕的連續,是將空間呈現一種沉浸式的體驗與觀知,通過濃縮重慶山城錯綜復雜的梯步來進一步講演川戲在特定空間中的文化主題再現。
帆起潮動,作為中國戲劇中最具地方特色的戲劇劇種——川劇,由水路派生而來,揚帆起舵,途運跌跌撞撞猶如激流中的磐石迎風阻擊,故此區塊采用上下聯貫的曲水承載漂浮多味的流觴而出。從入相觀心的尾端框引出第三幕巴山蜀水之賦文,并采用高山激蕩的水流傾瀉而下,寰宇江風,聽雨駁岸,既是對川劇的感思也是表達對其文曲的敬畏,側身輾轉移步到印刻在堅石上的過往歷史與劇中人物的實體雕像景隅,筆者一改本是沉重的深思回顧,加入觀者與文化字塊的對話,與扮演著的對手戲來烘托格調,使其呈現可觸、可感、可知、可游的多條選擇方式進行川劇的弘揚與傳播。
基地第四幕為川蜀靈音,中心區塊分為三個部分,即上部為傳統戲臺區,是輸出整個場地文化的主要精神脈搏,承載文化的構筑體主要采用傳統的川東民居聚落形式演變并加以形態改造而來,印染出特定的川劇文化主題;中部區塊為臨時表演區,由傳統的太極圖案異變而來,形成了曲云流水的靈趣畫面,成為基地整體鳥瞰的視覺焦點與中心,且采用地臺式的構筑形態增加其豐富的視聽與感知的多重體驗;第三個部分為地下沉浸式劇場,利用視錯覺曲線引導觀眾漸隱漸現的步入劇場,通過現代的表演方式,不僅豐富了區塊間表演的多重形式而且也是革新了傳統戲劇劇場形式的單一性,最終提煉出一種多層次、多方式、多角度的綜合豎向空間組合體呈現,也是更好的推動了川戲的傳播與交流。
基地第五幕為朝辭彩云,作為全幅最后的起色墨點也是貫穿了川劇主旨的始終,將容納榫卯式的丁字格局冠領不同的空間方位,采用紅,黃雙色趣味浸染流動,達到視覺間交相碰撞,賦予空間更多的巴渝味道與地域性,通過地景分流、中空樓閣、屋頂遠眺進一步講述空間主題性的次序。空間布局有三個豎向界面組成,分別為一層的入口接待區、休息島、文創體演區、動感幕景放映區;中層空間作為整體空間輸出與輸入的重要介質,主要為服飾器物集中展示區、樓宇精讀觀覽區、戲劇游廊式角色扮演互動區;第三層主要為聚氣、闡鳴,靜坐的空放場,激發觀者對環境的無止境變換來緩解都市的快節奏步調,也是登高觀望吐納曲調的高頻磁場,使其在統一的文化屬性上增強不同的地域背景并加以綜合表達,最終致力于多位的呈現同時又不失川劇特有的戲曲格調與場所精神的關懷。
川劇的編導與空間組合體的編織有異曲同工之處,之所以說是因為曲調是流動的建筑場域,而建筑同時又以靜態的方式推演出曲聯的跌宕起伏,使觀與演在無形中熟知劇種的演出方式與了解角色間劑量的如何配比,同時也是表演者據景物情感的自然流露,將傳統戲劇文化多元化、多類型、泛群眾化推向高潮,總而言之傳播與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非物質遺產文化不僅是增強國家的文化軟實力,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對繼續推進戲曲內容的豐富度,提升創新型空間載體付出一定的系統研究與提案。
參考文獻:
[1]蘭青.中國傳統音樂概論:戲曲與說唱音樂.沈陽:東北大學出版社 2012-08-01.
[2]袁鳳東.巴山風情:巴渝文化特色與形態.北京:現代出版社 2015-08-11.
[3]胡元斌.天府之國:蜀文化的特色與形態.北京:現代出版社 2015-08-11.
[4]賈麗媛,張旭.川劇的藝術特色.攀枝花學院學報(綜合版),200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