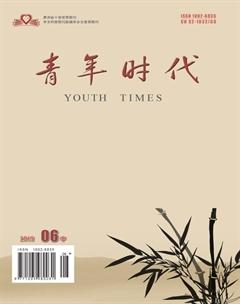慈善工具創新與慈善事業發展
夏靈芝
摘 要: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互聯網的普及,慈善工具不斷創新,吸引了更多的民眾參與到慈善事業中來,慈善事業蓬勃發展。但是慈善工具創新給慈善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出現了眾多隱患,如利益與慈善道德組織使命的權衡、慈善風險降低導致的慈善冷漠等等,最終都會導致慈善亂象的產生,反而破壞了慈善公信力的建設和慈善事業的發展。
關鍵詞:慈善工具;慈善組織;信息披露
一、問題的提出
借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慈善組織的慈善工具不斷創新,慈善事業蓬勃發展。據《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7)》[1]數據顯示:2016年,社會捐贈總量達1346億元,在捐贈主體上,盡管企業仍是我國社會捐贈的最主要力量,但是借助慈善工具的便捷化,民眾的捐贈規模不斷擴大、參與比例比上年增長5%,達到16.38%。同時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等相關法律的制定與實施,慈善事業的法律框架也更加完善。
但頻發的詐捐、騙捐丑聞讓慈善組織不斷遭受公眾信任的拷問。慈善工具的創新給慈善事業帶來活力的同時,也給慈善事業帶來了隱患,慈善工具的便捷轉移了個人承擔的慈善風險,但是卻使得公眾容易出現對慈善項目持續關注的冷漠,隱蔽在新媒體媒介下,使得信息的真實性難以分辨。本文主要歸納了目前慈善事業中出現的幾種主要的慈善工具創新形式,并分析其對慈善事業發展的影響。
二、相關概念
(一)慈善
羅伯特·佩滕提出的慈善是“為公眾謀福利的志愿行為”,即通過志愿行為給予三“T”:金錢(treasure)、時間(time)、智力(talent)來實現兩種目的:第一,減輕他人(與自己沒有血緣或者法律關系)的痛苦,救苦救難,包括提供食物、處所、治病等;第二,改善社區的群體生活質量,包括促進社區的文化、教育和娛樂等。[2]這兩種目的都具有明顯的道德維度,而這種道德維度便是慈善最重要的特征。
(二)慈善組織
慈善組織是居于政府和社會之外的第三部門,主要致力于慈善事業的發展和協助政府解決社會問題。本文認為慈善組織是指以開展慈善活動為宗旨,以服務社會公益為目標,具有公益慈善性質的社會組織。慈善組織開展的慈善活動既包括賑災濟困、安老助孤、幫殘助醫等傳統慈善活動,也包括致力于促進科學事業發展、環境保護、社會公益設施建設以及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其他社會公共和福利事業活動。[3]體現《慈善法》倡導的一種“大慈善”概念。
三、慈善工具創新形式
當前,根據各主體在慈善募捐的參與程度進行慈善工具形式的劃分,參與主體可分為直接參與主體與間接參與主體兩類。直接參與主體主要為募捐發起人、平臺、捐贈人,該類主體直接參與到善款的轉移和流通中;間接參與主體包括政府等執法部門、社交媒體、其他社會公眾等,該類主體更多的承擔監督和輿論導向的作用,并不直接介入善款的流通,故不在圖1中展示。根據《慈善法》的相關規定,當受益人為不具有公募資質的個人或組織時,需要與具有公募資質的慈善組織聯合發起募捐,并且募得善款將交由慈善組織賬戶進行撥付,這種情形下實質的募捐人為具有公募資質的慈善組織;當受益人為具有公募資質的慈善組織時,其兼具募捐人與受益人雙重角色,不僅通過平臺籌集善款,而且其相應的慈善活動直接受益于善款的籌集和使用。
在目前的主要慈善工具創新中,根據發起募捐主體的不同分為三種形式。
形式1:慈善商業化運營,對應圖中①路徑。慈善商業化運營是指慈善組織改變傳統的募款和運作模式,跨界到商業領域進行市場化運作。公募慈善組織的機構運行相對完整,在民政部門的直接監管審核下,擁有直接發起慈善項目的資質,也是承接慈善商業化運營模式的最主要機構。主要有四種具體模式:一是慈善組織直接進行商業化運營,參與市場活動,通過銷售捐贈品和公益商品對弱勢群體進行幫扶,如慈善超市、壹基金的“羌繡幫扶計劃”;二是慈善組織進行投資或在募資時涉及商業活動,實現資金的保值和增值,例如慈善信托、慈善債券等;三是慈善組織與商業企業在線上或線下進行合作,如農夫山泉的“一分錢”捐贈項目等。四是進行慈善營銷,將市場營銷的方法運用到公益項目中,借助新媒體和快捷支付方式進行慈善項目營銷,如針對漸凍人之一病患群體的“冰桶挑戰”。
形式2:慈善項目聯合募捐,對應圖中②路徑。根據《慈善法》等相關規定,不具備公募資質的組織和個人不得進行公開募捐,但可以與具有公募資質的慈善組織進行聯合募捐。截止2017年底,全國共有登記在案的慈善組織2442家,其中具有公募資格的僅有61家,非公募組織與公募組織聯合募捐是目前慈善項目推廣實施的最主要途徑,且在具體慈善項目執行時,公募慈善組織具有絕對的主導地位,既是慈善項目的申請者,又是募得資金的持有者與資金使用的監督者,非公募組織需要與公募組織簽訂書面協議協商善款的撥付,并承擔監管和信息披露職責。
形式3:個人求助。在③路徑中,分為個人募捐和個人求助。個人募捐是指個人通過公募組織平臺中進行聯合募捐,受《慈善法》的規制。而個人求助主要是基于本人或近親屬的需要,直接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發布募捐信息求助。個人求助在《慈善法》中并未明確管理,“羅爾事件”被定性為個人求助,無法從慈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中進行評判,只能從慈善的道德約束層面對羅爾進行批判譴責。
四、慈善工具創新對慈善發展的影響
依托互聯網新媒體技術,慈善工具不斷創新,使傳統慈善組織與捐贈人的雙方關系逐步演變成為慈善組織、平臺、捐贈人的三方關系,同時將傳統政府與慈善組織的閉合監督模式轉變為政府、第三方監督、媒體與社會公眾的多元化監督。在慈善工具的連接下,慈善組織、平臺、捐贈人、政府、媒體、其他社會公眾共同構成了目前慈善事業的關系鏈。
(一)慈善工具創新促進慈善事業的發展
第一,慈善工具的創新豐富了慈善事業的募款形式。使多元主體能夠便捷快速接觸到慈善項目,借助新媒體和快捷支付方式形成了小額化、低風險的指尖慈善模式,提高普通公眾的參與度,促進慈善組織與大眾的交流,使慈善項目日常化、生活化,有利于培育公眾的慈善觀念,從而提高社會的慈善意識和和諧美好社會文化。
第二,慈善工具的創新有利于完善慈善組織的運行機制。慈善商業化運行是解決資源短缺困境和行政化弊端的有效途徑之一,在保證慈善目的不受影響的情況下,積極參與市場化運作有利于完善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向現代化慈善轉型,從而促進慈善組織的長遠可持續發展。
第三,多元參與推動慈善組織的信息披露與監督。慈善工具的創新使多元主體進入慈善領域,以路徑②為例,非公募組織所提交的慈善項目首先需經公募組織審核,而后交由民政部門審核,在平臺完成募款后,按法律規定每隔一定時間在公益平臺、門戶網站等媒介公開信息,接受平臺、政府、媒體和社會公眾等的監督審核,倒逼慈善組織在慈善項目執行中加強信息披露的全面、真實、及時,改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推動慈善組織透明度和公信力的提高。
(二)慈善工具創新的隱患
第一,利益與慈善道德組織使命的權衡。慈善商業化帶給慈善組織效率提升的同時,也面臨利益與慈善組織使命的權衡。2011年始所爆發的慈善丑聞使得慈善商業化的前景不容樂觀。慈善組織偏離公益宗旨,成為利用善款謀私利的工具,嚴重損害了慈善組織的公益性和純潔性。除慈善貪污丑聞之外,慈善組織如何正確有度地參與市場活動,營利與虧損的成果慈善組織能否承擔都有待商榷。以慈善超市為例,作為在全國廣泛推行的,以銷售捐贈品,雇傭弱勢群體,收益用于慈善項目運作的慈善模式,其背后是政府在租金、雇傭費用等多方的支持,并未實現真正的組織自負盈虧。利益與慈善使命的抉擇,營利與虧損的壓力,使得一般性的慈善組織對慈善商業化的選擇還處于謹慎觀望狀態。
第二,慈善募捐亂象,詐捐、騙捐事件頻發。在慈善項目發起初始,慈善組織和個人通常會完整迅速的披露信息,但是當款物達到一定規模后,盡管《慈善法》規定了慈善組織信息披露的相關內容和時間限制,慈善組織和個人募捐者往往不能及時披露善款籌集進度和使用信息。另外,網絡信息的快速傳遞與虛假信息的泛濫造成慈善募捐的亂象,詐捐、騙捐真假難辨。
第三,慈善風險降低導致公眾的慈善冷漠。指尖慈善等形式的小額化慈善捐贈降低了捐贈人承擔的慈善風險,即使遇到騙捐詐捐等事件,相當一部分公眾由于個人的善款數額較小,并不會對騙捐詐捐進行反饋或者或許關注追究,反而助長了募捐的亂象,如此循環,最終導致的是公眾被欺騙后冷漠心態的蔓延,“善心”的耗盡,最終影響慈善組織和慈善事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楊團等.中國慈善發展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2,17-24.
[2]何莉君.慈善為何——讀《理解慈善——意義及其使命》[J].開放時代,2009(04):149-154.
[3]石國亮.慈善組織公信力的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行政管理,2014(5):9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