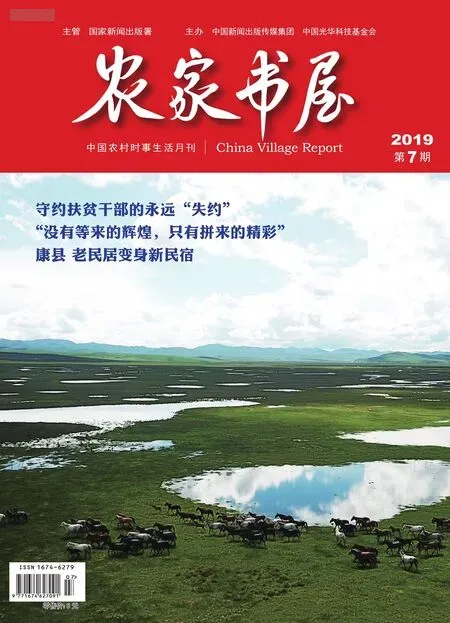造物為榮,從社會剛需到精神信仰
——讀《工匠之國:日本制造如何走向卓越》
□禾刀
職人,日語名詞,過去泛指傳統手工業者,現在偏向于對擁有精湛技藝的手工藝者的稱呼。《工匠之國:日本制造如何走向卓越》從對日本職人歷史發展、培養制度、文化信仰、技術傳承等方面的深刻講述,到對12位現代“匠人”與12種古老而不朽的手工藝的詳盡介紹,呈現出一個嚴格與歡樂同在、傳統與現代并存的職人世界。
造物為榮的歷史基因。日本職人文化源自江戶時代,當時的日本職人主要有三大特點:一是“寬永元年(1624),在德川政權日益鞏固之際,為營造日光東照宮,集中了全國大量的職人”。權力頂層的需求往往伴隨著嚴苛的質量懲戒機制,職人必須使出看家本領,精益求精。二是頻繁的重建,刺激了社會對職人的旺盛需求。日本房屋普遍采用木質結構,加之處于地震多發帶,易受火災和地震損毀。因此,大量的重建使職人得到了大量的鍛煉機會。三是職人扎堆產生的聚合效應。當大量職人聚集時,必然產生競爭,從而倒逼職人的技術不斷進步。
職人的門檻很高。要成為職人,先得通過師傅的“面試”,然后經過長達數年的耳提面命和嚴格考核,獲得師傅的“鑒札”。有意于此的家庭,往往在孩子九歲左右時將其送到師傅門下,從而開始長達“數十年的扎實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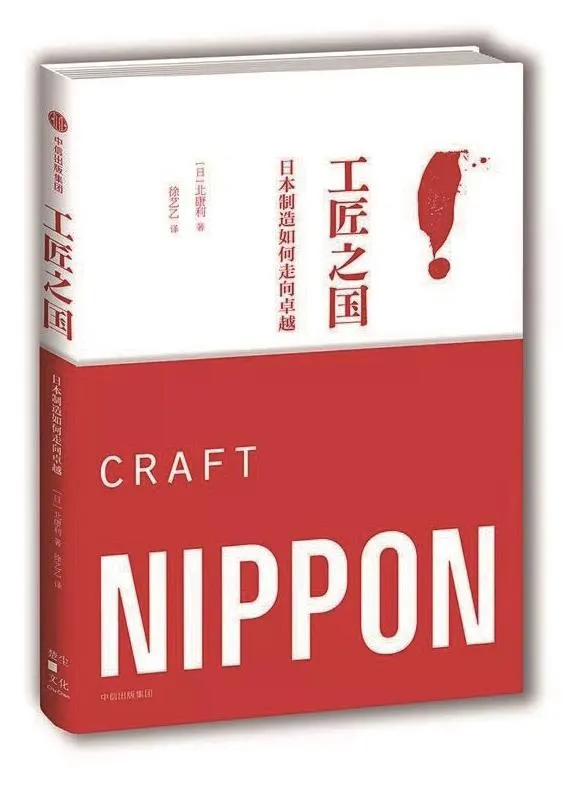
職人技藝如此精湛,收入理當可觀。但事實上,除了“幕府御用的職人頭領”,一般職人家庭均較為清貧,因為幕府對職人設置了不同檔次并規定了日收入的上限。
職人能忍受物質上的低回報,主要是因精神層面得到權力的認可。“鑒札”就像職人從事社會工作的一張極為特別的“駕駛證”。發放鑒札的要求越嚴,歷經數度寒暑終于“出師”的職人便越有成就感,加之“幕府時代以來,(地方)曾經數度發出無鑒札者不得被雇傭的公告”,這既是對職人的嚴格要求,同時也寓意權力對職人社會地位的認可,進而使得“造物為榮”蔚然成風。
職人至上的上下同欲。今天,日本的職人精神發展體現了兩個維度,一是傳統手工業界的職人精神依舊光彩照人,一是現代工業制造與職人文化融合后發生蝶變。
書中介紹的日本12種古老手工藝,均具不可比擬的特色。這些特色并非一成不變,在傳承過程中浸潤了歷代職人的改造心血,從而使這些手工藝歷久彌新。
日本對傳統手工藝和職人的鼓勵主要依托“人間國寶”和“現代民匠”制度。前者傾向于對傳統手工藝的保護與推廣,一旦被認定,就可得到政府一定資金的援助。后者側重于職人本體的精神表彰,從1967年至2006年“已表彰了4538人”。
職人技藝過去采用家庭式傳承。1873年,“開明教育家近藤真琴在他經營的私塾攻玉塾中嘗試設立了手工科”,從而開啟了社會化培養職人的大幕。
然而,日本制造業也曾一度難覓職人精神痕跡。“二戰”后,百廢待興的日本急欲振興工業,無奈產品質量堪憂,幾成劣質品的代名詞。令人費解的是,本書對此段歷史并未認真挖掘,不知是否因為改變這一狀況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著名的質量管理大師、來自美國的戴明博士。
被業界稱為美國“棄兒”的戴明博士推出的“質量管理十四法”以及“戴明環”,為世界質量管理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更主要的是,他幫助日本產品質量打了翻身仗。1951年,日本創設戴明質量獎,至今已有超過160個日本企業獲得該獎,其中包括世界知名企業豐田公司等。在戴明的帶動下,日本企業創造了全面質量控制(TQC)等為國外企業爭相學習推廣的質量管理新法,涌現了石川馨、田口玄一等一批享譽世界的著名質量管理專家。
戴明博士的成功,某種意義上正是日本上下同欲,共同致力于傳統職人精神接受現代化改造的結果。
職人精神的中國鏡鑒。日本人相信,“只有職人的技術才是國際競爭力的源泉”,所以他們“以‘造物國家’的復興為目標”,加大了政府對職人的扶持力度。一方面,“仿效德國‘我的明星’制度”,制定了涉及金屬、機械、電子、建筑、造園、裁剪等多方面的國家技能檢查測定制度,讓職人技藝標準顯性化剛性化;另一方面,大力開展評比“日本造物大獎”和“有活力的300家中小企業”活動,既“表彰那些對工作產生重大促進作用的團體或個人的發明”,也獎勵“秉承了江戶時代以來的‘造物’精神的傳統企業”。
沐浴在濃厚的“造物為榮”文化氣息中,日本逐漸形成了以敬業著稱的“職人氣質”。有調查表明,“日本職員的努力是常人的一倍以上”,日本職員的敬業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我國正在大力弘揚工匠精神。作為一衣帶水的鄰居,中日歷史上的匠人有不少相似之處。起初都是最好的工匠竭力為皇帝服務,所不同的是,中國歷史上的這些匠人很少像日本江戶時代那樣聚集扎堆。同時,日本權力階層始終大力推崇職人精神,而戴明博士先進質量理念的引入,更是實現了對日本傳統職人文化的改造。
近年來,我國民間特別是農村匠人群體正遭遇急劇衰落局面。雖然國家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等角度加大了保護力度,但相較于日本,保護手段還顯單調,力度也略顯單薄。還有,雖然我國早就引進了包括戴明在內的許多優秀的管理體系,但匠人精神并不穩定,經不起考驗。
始終如一,深耕不輟,坐得住冷板凳,這正是我國當前最急需的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