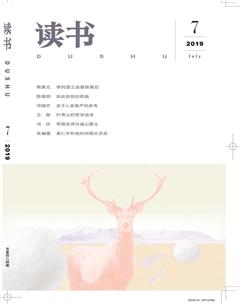濤聲徹耳逾激昂
梁啟超《變法通議 ·論不變法之害》與《少年中國說》(以下或簡稱《少》篇)都是近世名篇,后者因收入中學課本,影響更大,其開篇即與前篇有異,曰:“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而在前文中,對老大帝國說,卻是認可的:“印度,大地最古之國也,守舊不變,夷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國歷千年,而守舊不變,為六大國執其權,分其地矣 ……中國立國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邁突厥,而因沿積敝,不能振變,亦伯仲于二國之間。”前者作于一八九六年,后者作于一九○○年,相隔四年,一受一拒,迥然有別,原委何在呢?近檢梁氏年譜與《飲冰室文集》,覺得這與梁氏環境變化相關。其時,梁啟超流亡日本已一年多了,甲午戰爭后日本社會充斥對清朝的輕蔑與歧視,“老大帝國 ”是常用的蔑稱,如日人漢詩有言:“邦土山川徒老大,鳥雀無聲四百州。”(末松星舍:《靈鷹行》)“老大頑愚兮四百州,姑息偷生兮伴食輩。”(伊藤貞治:《心耿耿行》)“老大無成皆如此,四百余州亦困弊。”(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五日《每日新聞 ·詩月旦 ·大象斃》)一個流亡者,天天面對異邦人歧視的眼光,其民族認同感與自尊可能會變得更加敏感,之前他已撰文反駁此論,如其一八九九年《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言:“支那二千年來之歷史,其人民皆富于統一的思想,雖有紛分割據,恒不及百數十年,輒復合一 ……又千年以來,被他族之統治者,雖數數見,然決不與統治之他種同化,而恒使彼統治者反而同化于被治之人。”《論中國人種之將來》又言:“他日于二十世紀,我中國人必為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有可預斷言者。”“他日變更政體,壓力既去,其固有之力皆當發現,而泰西人歷年所發明之機器,與其所講求之商業商術,一舉而輸入于中國,中國人受之,以與其善經商之特質相合,則天下之富源,必移而入中國人之手矣。”《少》篇初刊于《清議報》三十五期,注明的發行日期是光緒二十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其《汗漫錄》記他于前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離開日本,經十天海上航行后到達檀香山,近一個月后才安頓下來。考慮到檀香山與日本的郵程與刊物編印時間,本文最遲應作于前年十二月下旬,即初達檀香山一月之內。這一期是庚子年編發的第一期,《少》篇作為 “本館論說 ”的第一篇,也有新年祝詞之意。他需要向讀者報告自己在新環境里的新感受,本期還發表了他的航行日記《汗漫錄》首章,也是此意。他身為清廷通緝的政治犯,入境時冒用了日本人姓名與護照,且不懂英語,人生地不熟,本感寥落,其時,檀香山當局又因防疫之事正施行排華限華之事,其民族自尊心倍受煎熬,開篇的義憤之情或與此相關。因此,海外體驗應是產生《少年中國說》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此文的重要背景。
他拒絕老大帝國說,是因為他認為自己已不屬于過去的中國人,而是未來的中國人。梁啟超自小具有很強的求知欲與學習能力,十二歲中秀才,十七歲中舉人,十八歲時拜秀才康有為為師,探究新學,二十三歲隨康有為入京發動 “公車上書 ”運動,二十四歲時任《時務報》主編,發表《變法通議》,聲名大噪。二十五歲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二十六歲赴京參與 “百日維新 ”,是其時最有吸引力的思想家與宣傳家。流亡日本后,馬上又創辦《清議報》宣傳變法,再次站到輿論的頂峰。在日本的十四個月里,他切身感受到變法維新給日本帶來的巨大變化與進步,廣泛汲取了近代啟蒙主義自由民主理念,開始從更高的層次與更宏闊的知識視野思考中國問題。其離開日本時以日本為第二故鄉,就是針對思想收獲而言。在結束“惡補 ”階段后,自感學力精進,急欲與人分享自己的新思想,《少年中國說》中的激情也如同一個跋涉者在回顧身后深壑巨嶺時的欣喜歡叫。
關于這一點,將《變法通議》與《少年中國說》比較即可見出,《變法通議》言:“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其思想核心在于改變教育制度與官制,而于整個國家制度與社會層面并未涉及。其時梁啟超二十四歲,僅能借助各種中文譯作了解西方與日本,對現代政治制度尚缺乏具體與整體的感知。到日、美之后才認識到 “家天下 ”的集權制是造成中國脫離于世界現代文明進程的根本原因,據此《少》篇對未來中國提出了新定義:
欲斷今日之中國為老大耶?為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
這時他已拋棄了傳統的先國后家、先君后臣觀念,從國家結構層面認識到民權的意義,形成了比較現代的國家理念。這應是他的新理念,在兩個月前的《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與中國前途》中才開始展示了這一新思想:
國家者,以國為一家私產之稱也。古者國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長者,若其勇者,統率其族以與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為國,其權無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勢,他家代之,以暴易暴,無有已時,是之謂國家。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認識到這些,他覺得已為老大帝國找到了病根與除疾良藥,必欲疾呼告人而后快。有此信念,對未來中國充滿期待,自然對異邦的老大之說厭惡不已。如文中所說:
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為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漸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為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在他看來,所謂的老大帝國是將死之國,理想的中國則在未來,
這是一新型之國,具有現代民主制度,相比其過去古老的歷史,她仍是一少年之國。這樣的中國,“前此尚未出現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他為已感受到的正在成長的少年中國而歡呼,對前景充滿希望,這種自信既基于新形成的現代國家理念,也源于對當時流行的進化論的執念。
其次,梁啟超在日本的社交群體也發生了變化,來日之前他主要追隨康有為,又年少老成,交往者多長于他。在戊戌變法前后曾結交李鴻章、張之洞這些老臣,變法失敗使之深感這些老官僚無望。到日本后,他多與同輩或者更年輕的學生生活一起,先與康門弟子十二人在江之島金龜樓義結金蘭,組成保皇黨十三太保 “少年團 ”。后來,他在湖南時務學堂的學生蔡鍔、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鐘浩等由國內又跑來跟隨他。這是一批更熱血的學生,多半在自立軍起義中犧牲了,蔡鍔則成為再造民國的大英雄。梁啟超與他們朝夕相處、同甘共苦的海外生活,是一種全新的體驗。這群學生對自己的信任,對追求真理的執著,完全超越了世俗風氣,讓他看到了希望,這才有了《少年中國說》所言: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茍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茍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這里不只是區別老少者生理與心理特征,而是表達了一種喜少
厭老的情緒。這種厭老情緒不只是針對舊官僚舊體制,可能還含有他對自己老師的微妙之情。康有為大梁十五歲,是他的學術思想引路人,其在學術上的特立獨行對梁啟超啟發甚大,其以今文經學思維建孔子托古改制之說,倡導變法,也深深影響了梁啟超,但是,康的創新到此為止了,基本沒能越出儒家經學范圍,其自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后不復有進,亦不必有進。”頑固地堅持保皇保教的主張,屢屢指責梁氏言涉革命。昔日崇拜的老師竟成了難以跨越的障礙,梁氏頗覺煩惱。所以,文中的老少對比,既是出于對時興的進化論的理解,又是有心講給老師聽的。
或許就是因為已宣示了這一差別,他后來才與老師展開了更激烈的論爭,如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致康有為信言:
來示于自由之義,深惡而痛絕之,而弟子始終不欲棄此義。 ……夫不興民權,則民智烏可得開哉?其腦質之思想,受數千年古學所束縛,曾不敢有一線之走開,雖盡授以外國學問,一切普通學皆充入其記性之中,終不過如機器砌成之人形,毫無發生氣象。……故今日而知民智之為急,則舍自由無他
道矣。中國于教學之界則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異想;于政治之界則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異言。此實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藥無效,必以萬鈞之力,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熱其已涼之血管,而使增熱至沸度;攪其久伏之腦筋,而使大動至發狂。經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幾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
兩事僅隔一個多月,可見,在與一群熱血青年同處共學的過程中,他的思想跳脫了師門羈絆,并在獨立中獲得了更大的自信。
他很早就崇拜日本幕末維新志士,曾作《記東俠》介紹僧月性、僧月照、西鄉隆盛等人,在日本,他以吉田晉為名,就是取吉田松陰、高杉晉兩名的合成,表示要以這一對青年師生為榜樣。在離開日本時,他作《別西鄉隆盛銅像一首》,自注曰:“像在上野公園,吾于行之前一日,獨詣其下,頂禮而去。”詩云:
東海數健者,何人似乃公。劫余小天地,淘盡幾英雄!
聞鼓思飛將,看云感臥龍。行行一膜拜,熱淚灑秋風。從歷史進程看,西鄉是一個扭傳歷史走向的大英雄,而從個人角度看,西鄉又是一個失敗者,但對梁氏來說,西鄉是他們 “東海數健者 ”的群體偶像,從西鄉、高杉等維新志士身上,他認識到社會變革必須要有年輕人的沖擊力與熱血精神。《汗漫錄》記其臨行時,“是夕大同學校干事諸君,餞之于校中。高等學校發起人諸君,餞之于千歲樓。席散,與同學諸君作竟夕談于清議報館 ”。他也寫詩告別,曰:
丈夫有壯別,不作兒女顏。風塵孤劍在,湖海一身單。天下正多事,年華殊未闌。高樓一揮手,來去我何難。(《壯別》)
諸子相從,多逃家艱辛而來,今皆自隱其名。于余之行也,咸有戀戀不舍之色,以此慰之。患難相從我,恩情骨肉親。變名憐瑪志,亡邸想藤寅(吉田松陰又名藤寅,早年因與同志結漫游,逃亡其邸,被削籍)。愧我乏恒德,半途又離群。丈夫各獨立,
毋為吾苦辛。(《再示諸門人一首》)他以意大利愛國者瑪志尼與吉田松陰并舉,以吉田流亡之事自況相勉,可以想象,當時這群年輕的大丈夫們一定是豪氣沖天,作為老師,要告別已生死相依八個月的學生,一定百感交集。一個月后,寫作新年寄語,心目中設定的第一讀者就是這些志同道合的學生。
再次,這篇文章中還帶有他在旅美航行時與初至檀香山的遐思與激情。《汗漫錄》序言:“去年九月以國事東渡,居于亞洲創行立憲政體之第一先進國,是為生平游他國之始。今年十一月乃航太平洋,將適全地球創行共和政體之第一先進國,是為生平游他洲之始。于是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學為國人,學為世界人 ……天地悠矣,前途遼矣。”他以此行為人生的一個新起點,在船上作長詩《太平洋遇雨》言:
世界風潮至此忽大變,天地異色神鬼瞠。輪船鐵路電線瞬千里,縮地疑有鴻秘方。四大自由(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行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銷為日月光。……物競天擇勢必至,不優則劣兮不興則亡 ……海云極目何茫茫,濤聲徹耳逾激昂。
梁啟超有意采用破格體,以齊散交雜的句式展示了一個年輕人不斷求索的思維狀態,表達了他在認識新世界后的興奮與思考。在他看來,世界不僅物質技術有了極大的發展,社會意識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急切感受到中國正處在不優則亡的競爭危機中,在蒼茫變幻的時代大潮中,他希望能以年輕的熱血,喚醒國人。詩文對照,不難見出這篇名文中正含有他在海上航行中激昂的思緒:
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這種雄視天下的自信、昂揚奮發的激情以及文末一段銘文式鋪排,與其在海上所作的詩是一致的。
到了檀香山后,梁啟超對美國政治又有了更真切的感受,《汗漫錄》言:“此都(檀香山)十年以來,經三次革命,卒倒舊朝,興新政府 ……觀于此,而知法國大革命之風潮,其影響所及,披靡全歐者數十年,決非無故也。觀于此,而識改鑄國民腦質之法矣。”他由一島之變感知到世界風潮,認識到推動國民自覺意識的必要。他又由夏威夷王國之亡感慨:“自古之亡國,則國亡而已;今也不然,國亡而種即隨之,殷鑒不遠,即在夏威 ……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天下萬世之公理也。”這種優勝劣汰的民族危機意識,也深深滲入到《少年中國說》一文中:
夫以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為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折,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喏,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為鄰之時,然后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畀于其手。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今之所謂老后、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以此為國,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戊戌變法一項主要內容就是廢除以經學為中心、以八股為內容的科舉,興辦現代學校,檀香山之行后,梁益發認識到這種教育與官制會將中國帶入死途。緊接其后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以 “少年中國之少年 ”為筆名發表《呵旁觀者文》言:
今之擁高位,秩厚祿,與夫號稱先達名士有聞于時者,皆一國中過去之人也。……若吾輩青年,正一國將來之主人也,與此國為緣之日正長。前途茫茫,未知所屆。國之興也,我輩實躬享其榮;國之亡也,我輩實親嘗其慘。欲避無可避,欲逃無可逃,其榮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慘也非他人之所得代。
他將那些麻木自閉的高官名士稱為過去之人,以吾輩青年為將來中國的主人,正是對《少年中國說》的發揮。
誠如郭沫若所言:“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 —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而《少》篇又可以說是影響最著者之一。如,陳三立一九○三年春作《雨中過安慶有懷姚叔節》言:“中國少年姚叔子,為誰費盡短燈檠。”陳三立曾協助其父陳寶箴在湖南推動變法,邀請梁啟超主持時務學堂,因變法失敗父子被革職,所以,他對梁啟超一直很關注,自然熟悉這篇激動人心的文章,也以 “中國少年 ”一詞入詩;又,徐一士記:“時
(楊)度作《湖南少年歌》,甚雄放,如云:‘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啟超既自號 ‘少年中國之少年 ,度復歌 ‘湖南少年 ,是二人者,均當時新青年中之卓卓者也。”此事在《少》篇發表后三至四年;在其發表近二十年后,一批新興知識分子成立 “少年中國學會 ”,李大釗于《少年中國》會刊上發表《少年中國與少年運動》,梁文印跡甚明。梁啟超自己也曾言:“有《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過渡時代論》等,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細繹史料,解得其中的海外之味,可具體把握其中的情感脈絡,更深入地領會這篇鴻文的歷史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