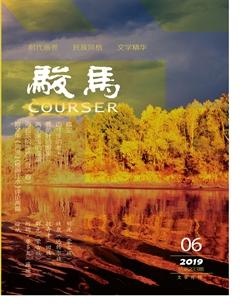邁寸步的老人
昳嵐
旭躇這個名字有點咬嘴,我費了好大的精力,才把他從歲月深處撈了出來。他一出場,就站成了一個壯壯的風景:較高的身材,一身黑色長衫,脖子上總是繞著一條長長的米色毛線圍脖,弄得脖子又粗又短,頭就像坐在半圓里,是這樣一種形象。村里人都稱呼他“旭躇烏沓其”(旭躇老頭)。
第一次見他是在家里,他跟嬤說要買琥珀香煙,嬤說:“這不是磕磣我嗎?抽點兒煙還買什么?我不賣煙。”
旭躇老人說:“不……不是,我們……經常抽,不……是一點,是……長期……”
他竟然結巴!越著急,越說不好,本來很紅潤的臉膛憋得更紅,甚至頭也跟著使勁。同來的煥巴老漢也幫忙說:“你的琥珀香色紅味好,是愛勒里最好抽的煙,誰的也比不上。”
“那我也不賣給你們。”
嬤沒有賣給他們,而是拿了一尺壓得很實的“霍日當各”(一株煙頂尖上的一對葉子),又外加上一些散的“襪勒當各”(底煙),說摻和著抽吧,對煙太沖,摻點底煙柔和一些。
兩個老漢高興著,千謝萬謝告別。嬤說,抽完了再來拿哈。
當他們起身往外走時,我又愣住,旭躇老人竟然是在挪著寸步行走,一步邁出去,的確也就寸步左右,但速度很快,促促促地一個勁兒倒步。
怎么會是這個樣子?我心里有點難過。
而煥巴老漢和他的人一樣,走路也是圓乎乎地邁著圓步。
他們的家就在我家西邊,隔著很大的院子,很小的一間房,由于那邊地勢較低,那房子就顯得更小,也少有生機,兩個孤老頭,一生沒有婚姻子嗣,就住在一起,相互照應。
后來常見旭躇老人,是在我家后面去往村里的東西向的路上,總是那身黑色的長衫,長長的圍脖,走路寸寸移步,老遠望去,像一個很壯的黑色矗立物。
一天晚上,我跟著嬤,去二姥爺家聽書,坐到炕上一看,西炕上那個重要的位置,不是原來那位比較清癯的說書人,是旭躇老人坐在那里。說書人還沒來嗎?我掃了一下南炕北炕,沒有。一會兒,說書開始了,竟是旭躇老人!他從懷里掏出一個紅色的小包,打開來,取出一本舊舊的發黃的書,書的四角都沒了棱角,他清清嗓子開始念誦。竟然,他竟然一點不結巴啦!我又是一驚,好奇加重,注意力全集中在他紅潤的臉上嘴上。他念一段,說一段。念得什么,我一個字不懂。原來,他念得是滿文,說的是達斡爾語。很奇怪,為什么他念書說書的時候一點不結巴呢?在他說達斡爾話時,我聽見了這樣發音的幾個字“傘過演義,他把“三國”念成“傘過”。
這一發現,我對老人生出新的興趣,覺得他是個突然能掏出寶的人。一天,小阿卡又要出去玩時,聽他說出“旭躇烏沓其”名字,就高興地跟了去。
跨過大門的橫木,往后走五十米繞過我家的杖子(籬笆),再往西一拐,五六十米,就到了那間小房。走進屋里,不見慣常人家的西窗,除去一鋪北炕連著不寬的西炕,地就剩了一米多點的空間,旭躇老人坐在炕頭,正在一張烏溜溜的小飯桌上寫字,旁邊放著那本四角都損了邊的厚書,又給了我一個意外。我湊上去,想看看他桌上的東西。小阿卡說不要亂動。但旭躇老人說,沒……事,來看看,認……識認識。
他說的語聲很親切,但是表情嚴肅。紅潤的臉膛好像總是很熱的樣子。
我使勁伸出頭去,看看那書,噢!是什么字啊?竟不是方塊的橫豎撇捺,那些字仿佛是一根樹枝上長出了許多小杈,很長,旁邊還不時出現個小點。
“這是什么字耶?”我非常好奇。
“蠻記筆替各。”老人說。
“蠻記筆替各”是達斡爾語,即“滿文”之意。很多說書的晚上,都是以“蠻記筆替各埃拉貝”即以翻譯滿文來講。過去,由于達斡爾人沒有文字,所學文字都是滿文課本,讀書寫字也都使用滿文。清朝時期達斡爾人16歲就服役兵丁,做官朝廷,隨軍征戰南北,全民族受用皇糧,生活習俗、房屋建筑、語言等多有相似。在我母系蘇哈拉家族的祖上,赫赫有名的蘇都熱·孟額德,掌握七種語言,是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翻譯家。也因為蘇都熱氏族多有朝廷為官者,在稱呼爸爸上,隨了滿族人的稱呼,稱為“阿瑪”。小時候村里的達斡爾人都稱呼爸爸為“阿查”,只有蘇哈拉家族稱呼“阿瑪”。那時,常聽嬤和老姨、舅舅們說,阿瑪怎樣怎樣……現在,我的表弟們,說起父親,仍然稱呼“阿瑪”。
在民國時期,念過國高的達斡爾人,學的都是滿文,我們村里,有三位老人會讀滿文,旭躇老人就是其中一位。那天他正在一個有些粗糙的大本子上抄那本《三國演義》,筆筆抄得相當認真。那長長的字看上去秀氣,豎直,從上到下,像一個個細高的女人。
以后我就常跟小阿卡去他那里,小阿卡愛聽故事,愛問為什么,每次去那兒,不是看他在讀著滿文書,就是在寫那長長的字。卻也會停下來,從花鏡上邊抬起眼睛看過來,說:“額訥克庫(這小子)又來了,今天你又要問什么?”
小阿卡的問題總能得到解決,他的手上也總是離不開書,上課時偷著看書,吃飯時也把書放在腿上,邊嚼邊看。不知他從哪里弄來了一本本大書小書還有畫本,大書大都沒頭沒尾,他天天埋在書里,有時耽誤了活兒,嬤也不說。在那些漫長的冬夜里,無數個燈光搖曳的夜晚,嬤總是坐在燈前縫“其卡密”靴子,一種毛朝外的動物皮毛靴子,里邊能續很多烏拉草,專門給那些數九寒天在野地林子里的人穿用。這樣的夜晚,小阿卡就捧著書,念給嬤聽。他念的書,都是那個時代的讀本,如《烈火金剛》《紅巖》《青春之歌》《烈火春風斗古城》《金光大道》《西游記》《紅樓夢》《苦菜花》《迎春花》《鋼鐵是怎樣練成的》,還有《家》《春》《秋》等等,也都成為我后來所讀的書。至于像《七俠五義》《大八義》《小八義》《奇門遁甲》之類的書,小阿卡就自己偷著去看。
那天,旭躇老人又掏出一個寶。他從炕里的枕頭旁邊,拽出一個“kia-ji”,一個扁長形的小匣子,從一頭抽開蓋子,里邊竟裝著很多筆記本,看樣子都是他抄寫的字。他把正在抄寫的本子放進匣子里,然后合上抽出的蓋子。
這個發現,又增加了我對老人的神秘感,就像他的兜里揣著很多你無從知曉的什么東西,趁你不在意時,突然掏出一個,令你驚奇。
一天,嬤讓我去老姨家住,我也沒問什么欣然而去。我很愿意去同伴或姨家住個新鮮。第二天早晨,小阿卡早早過來,告訴老姨說姥姥走了,去世了。我才知道,讓我躲出來的原因。
其實姥姥是健康的,輪流住在公社上班的大舅老舅家里,由于老舅一次執行禁賭任務時,槍支走火誤傷賭徒而導致當場死人,便從公安干部一夜之間成為囚徒;大舅也因涉嫌什么正在接受審查,嬤便把姥姥接到家里盡孝。姥姥是位典型的從舊時代過來的人,喜歡著長衫和袖珍馬甲,即使暑熱天氣,也穿著長衫飄曳。有時就聽嬤說:“嬤你換個短衫吧,天太熱。”可姥姥不,她說:“不穿哈日么(到膝蓋或更長的長衫)像個沒有尾巴的家雀。”
這樣,姥姥那袖珍的身相,就顯得更小,凹陷的雙眼顯得更大,拍拍袍子前后,搖搖曳曳的,又出去了。而額頭上系的一條寸多寬的發帶,只有熱天才摘下來,一邊涼快去。其實那樣的發帶是達斡爾女人保護額頭的,歲月賦予為頭飾。不過她也沒有因為自己是鄂溫克人而非顯出什么不同。實際上也沒什么太大區別。達斡爾、鄂溫克本來以表親相稱,生活中始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猶如日子里的水乳相融。
春天,喜歡戶外活動的姥姥,柳蒿芽剛長出寸多高時,終于擺脫了一季的貓冬,忍不住一個人采青去了。生長柳蒿芽的地方不遠,村東的河邊就長滿了那種葉背灰綠色的野菜。那天陽光很好,春風柔柔地撫摸著滿地的翠綠,姥姥覺得全身的肌骨都在和她一起躍動,就自然唱幾聲“扎嗯達勒”。正采得愜意,突然聽見有人喊她,抬頭看去,是老朋友,在不遠處說:“這里柳蒿芽可多了,你快來呀。”姥姥說:“你什么時候來的,我怎么沒看見你?”便向她走去,隨即低頭采一把看到的野菜。但那朋友看著不遠,卻走不近她。就說:“你等等我呀。”她說:“你快走吧,就在前邊……”姥姥就跟著走,但怎么走也走不近她,姥姥生出狐疑:奇怪,怎么就走不到她跟前?
不好!姥姥突然猛醒,立刻轉身回返。這時那朋友也轉過身來,跟上。姥姥驟然大喊:“我看你過來?”手中的菜刀使勁兒指過去,一邊后退著,一邊不斷仗著膽子大聲威脅:“你要是過來我就扎死你。”這樣姥姥深一腳淺一腳,一會兒退走,一會兒正走,出了林子。到了路上,障礙少了,姥姥的步子也快了,胳膊和刀子始終沒有放下。終于走上大路,姥姥索性跑了起來,看見大壩了。過了大壩就是愛勒,她喘噓著,踉蹌著終于走到村頭的第一戶人家,多音家。進了屋就靠倒在炕墻上,慘白的臉,倒著氣,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從那姥姥就開始生病,一病不起。
我跟小阿卡回到家里,一進大門,就見院子里停著高高的脊形棺木,紅紅的,倒也沒有令人害怕的地方。倒是這么高大的東西,姥姥那袖珍的身材能占多少呢?不過我不相信姥姥會待在那里,說不定她依然搖曳著長衫去南邊的甸子溜達去了,或者長衫一撩蹲在草地上,聞著四季的草香……
如此想時,就覺得姥姥長衫一搖一擺地真去前邊的甸子了,或在甸子邊的老涂家,跟嘎榮嬤說著一大堆鄂溫克話。老涂家夫妻一兒一女,一家人都和姥姥一樣袖珍身材,說話的音調都一個樣子,忍在嗓子眼里,細簌憐憐的,不舍得敞開放出寶貝聲音。兒子嘎球是小阿卡的同學,黑亮亮的眼睛跟他爸爸一樣,好像總有擦不凈的鼻涕,一跑一提褲子。那年秋天,甸子西邊的苞米地秋收后苞米稈仍然站在地里,下午放學后我便玩一樣去撿苞米。我不敢一個人走進里邊,怕偌大的苞米地淹沒了我還沒有苞米稈高的人影,就在靠路邊的幾條壟中尋找。一會兒,就見嘎球從東邊穿過甸子來了。似乎他手氣很好,一進地就撿到了一穗苞米。不過一會兒,他把那穗苞米扔進我的小筐里,又從攥著的小手里拿出一張又舊又皺的一毛錢,塞給我,還沒等我作出什么反應,他就轉身走了,磕磕絆絆的。第二天我剛進地,還沒撿到一穗苞米,他又來了,磕磕絆絆邁過橫的壟溝,手里竟然又有一穗小苞米,黃紅泱泱的,扔進我的筐里,又拿出一張那樣皺褶的紙幣伸過來。“我不要啊”,我有了準備,躲閃著說。可他不聽還是扔進我的筐里,轉身高一腳低一腳走了,兩個胳膊不時在腰上往上夾一下……
我正在胡亂想著,往屋里走,想確定一下姥姥是不是在炕上,迎面屋子里出來幾個人,竟然旭躇老人也在其中。這位神秘的老者,我又看見他了。他手里拿著幾頁卷著的紙,寸步促促促走到靈柩前面,雙膝著地跪下來,其他的人也都依次跪在他的身后,男人雙膝著地,女人單跪,開始進行“ki-sale-bei”(達斡爾記音符號,祭祀之意)儀式。旭躇老人先領著大家向那高大的脊形棺木磕了三個頭,實際就是點了三下頭而已。然后他展開手里的白紙,清了一下嗓音,念起來,仍然是念了一遍滿文,然后是達斡爾語。
蘇都熱家族的祖老太
正寢的靈魂請聽清
七十多高齡你已過
光彩美好度了一生
獲得七十有八高齡后
孫男弟女一大群
種種教導后代的道理
大家心懷感恩記下了
姑娘姑爺的孝順下
溫柔周到服侍了你
度過了安心的晚年
兒有重事脫不開身
請你不要挑他們理兒
蘇都熱哈拉霍卓日額特沃
Sudur-ha-laho-zor-et-woo
蘇熱蘇木思歌吐昆索恩索
Su-resmusgtu-kunsoon-so
大勒恩那似杜勒吉
Dal-nasdul-ji
……
旭躇老人的臉孔更加紅了,口出的言詞竟然像朗誦詩歌一樣,和仄押韻,朗朗上口,橫掃哀傷氣氛。肅穆中的人們,耳朵都集中在那美妙的詞匯里,好像身處的不是送一個即將赴黃泉者的場面,而是在傾聽著一曲天籟般的靈魂之歌,那ki-sale-bei儀式,將一個古老的喪葬習俗隔開了平素的粗糙,截然相反斯斯文文表現出來。人說那是一個族群的文化窗口。可那時,誰知道他們進行的正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延續呢。
接下去,這樣的儀式又進行了兩次,每隔一段時間,旭躇老人便領著大家說出一段祭文,每一次的語言都不盡相同。我除了聽出跟平時的發音不同,幾乎什么也沒有聽懂。沒想到,小阿卡的愛問好學,竟然問到了旭躇老人的小屋里,這是我后來才知道的事情。他把那些聽起來串串連接、重疊相扣、富有彈性魅力的祭文,從旭躇老人的嘴里摳了出來,裝進了自己的腦袋,并還問到了旭躇老人在其他“ki-sale-bei”場合所說的祭文。老人說,那都是臨場發揮的,見景造詞。
見景造詞,太有才了。
記錄那些美妙的詩詞,是多年以后的一個偶然機會,受感于那種美妙詞語的誘惑,或許還有一種此儀式即將絕跡保護的良知,做了幾次采訪。我喜歡那些絕妙的詞賦和美麗上口的韻律,也愿意共享資源。
會說ki-sale-bei祭文的,村里還有一位讀滿文的老人,名叫柳果爾,他面部清癯,身材中等,典型的秀才模樣,求雨祭祀、說祭文皆能,也是村里具有特殊文才的長者,備受人們的尊敬。我趕上的一次求雨,就是柳果爾老人主持的。相比旭躇老人,又是一種氣質。因他家住較遠的北街,平時極少見他。而旭躇老人就在西邊的那個小房子里,來回邁著寸步促促促,走在園子后邊東西向的路上,覺得他的日子就是走在路上,不然就在他那烏溜溜的小桌子旁,與書為伴。
看上去雖然走路不暢的老人,卻能遠行。夏天掛鋤時節,或冬閑無事的時候,愛去酒鎮,三十多華里的路,邁著寸步出行,執著不停地往前走。夏天早去晚歸,冬天可能住上一宿,也許不住。到了酒鎮,目標直接飯館,吃上一頓燒賣,或兩根麻花,一碗湯,就飽足了,也歇了。大車店便宜,兩毛錢一條位置,住一宿,第二天返回,挺好。我上初中后的一個冬天,放寒假回來,沒看到老人,便問小阿卡,阿卡說他已經沒了。我愣然,怎么會呢?
那天旭躇老人仍然徒步去了酒鎮,吃了燒麥、面條,一盤翹青椒(炒青椒),照舊往回走,晚上回來時,天色已經漆黑,同屋的煥巴老人,聽門嘎吱吱地響了一會兒,門才拉開。隨著一股白哈哈的寒氣,老人幾乎把自己摔進門里,進屋就吭吭哧哧地說要用涼水泡腳。煥巴老漢說你凍了,要用涼水泡腳?旭躇老人說凍了。他就給他端來了一盆冰涼的涼水,幫他脫鞋。可那鞋已經脫不下來了,跟腳凍在一塊兒,就連鞋一起泡在水里,泡了半天,鞋泡下來了,腳還沒化,繼續泡,又泡了半天,泡醒了,那腳變成紫色……
聽得我心里一直發冷打顫,不知他怎么一寸一寸從那冰雪的路上挪回家來。一位不甘寂寞的老人,他以寸步去丈量那三十多華里的冰凍之路,來消減歲月的老邁無聊,寧可把時光凍結在運動的寒冬,也不愿懶在溫暖的屋里。那雙腳雖然解凍,但慢慢地腫脹發炎,最終爛掉,人也隨著雙腳去了。
旭躇老人念了一輩子的祭文,用那些美麗的詞匯引導安慰了很多亡靈,而到他過世的時候,已經沒有人會說祭文了,柳果爾老漢比他先走了一步,也許,他已經不需要祭文了,為別人所做的引導安慰,都成了他上路的引路悼歌和資糧。
書呢?我想到了他的那些書本。
小阿卡說,他曾去了那個小屋,找他的小匣子,沒有找到。問煥巴老漢,他說他也不知道。
小阿卡便生起懷疑,不會是煥巴老漢當引火紙都給燒了吧?
能嗎?他也是個知書拿字的,是愛勒里第三個懂得滿文的人,能舍得?
有啥舍不得?不像現在能當個文物展覽起來,那時誰還學滿文?都成了淘汰的東西,放哪兒都沒有用。
是啊,小阿卡說得不無道理,那時的人們,紙張也是缺的,用處很多。孩子們念過的書,用過的作業本,都能發揮到極致的用處,現代人想都想不到的。那么旭躇老人的書和那一匣子手抄本,會在哪里呢?寧愿讓它變成青煙升了空去,追隨老人,也不愿它用在其他的不潔凈之處。
懷著失落的心情,走出那間小屋,小匣子沒了,里邊的滿文本子沒了,那厚厚的磨得頓了角的大書也不見了,小小的狹窄屋子,竟然變得空蕩寂寥,它們和他們都不知去向。
我關上那個輕飄的門,一抬眼,一片白白的雪在陽光下晶瑩閃爍,遠遠的,愛勒向西去的大路那頭,有個黑色的點在移動,那是誰呢?我停下眺望,會不會是旭躇老人的影子……
我慢慢地轉回身來。
責任編輯 烏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