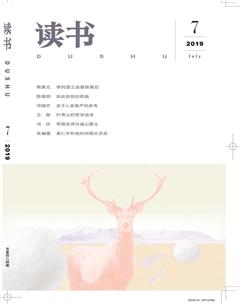林語堂的三重身份
徐兆正
在《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一書中,錢鎖橋先生將 “修正我們已經(jīng)習(xí)以為常的有關(guān)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結(jié)構(gòu) ”,作為 “對林語堂一生著述進(jìn)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理解 ”的前提,并非難以理解。作者深知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文化批評的語境內(nèi)彰顯林語堂文學(xué)實踐的意義 ”的必要性,為此才構(gòu)筑了一個重新討論現(xiàn)代中國知識結(jié)構(gòu)的場域。
在他看來,以胡適與魯迅為代表的 “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結(jié)構(gòu) ”所生成的話語實踐,深刻影響了中國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因此,對兩人的思想遺產(chǎn)進(jìn)行重估,始于檢討中國現(xiàn)代化進(jìn)程遺留下的諸多問題(如“新的文明 ”的許諾并未在傳統(tǒng)儒家文化崩潰之后兌現(xiàn),反倒是留下了近乎迷信的科學(xué)崇拜,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不復(fù)為 “本”),而落實在兩人思想觀念的同一之處:兩人同為新文化運(yùn)動的領(lǐng)軍人物,盡管側(cè)重不同,在“再造文明 ”的問題上卻不約而同地顯示出殖民主義話語的滲透,“假如按后殖民式批評家的說法,魯迅對西方傳教士話語的霸權(quán)性質(zhì) ‘視而不見 ,胡適從來就不承認(rèn)有殖民主義這回事 ”。
由是在第一章的結(jié)尾,作者便為我們勾勒了置身中國現(xiàn)代性歷程中的林語堂,他的話語實踐在胡適與魯迅組成的坐標(biāo)中所兼具的三重特質(zhì):首先,他們都是自由主義的批評家;其次,在針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做出批評時,林缺少胡適、魯迅兩人話語中的激烈形態(tài),換言之,自其介入新文化運(yùn)動以降,他所走的始終是一條允執(zhí)厥中的道路;最后,林語堂八十一年的生平行止,有三十五年在海外。這種海外經(jīng)歷與由此而來的視野,似乎使得他比通常意義上的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多出了一段,林的著譯涵蓋了他身體力行對兩種文明的轉(zhuǎn)換,令他在此一基礎(chǔ)上能夠?qū)?“整個現(xiàn)代文明(中國現(xiàn)代性問題為其一部分)”有所發(fā)言。作者認(rèn)為,這一點(diǎn)在整個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群皆罕見其匹。
正是從這三個方面,作者基于歷史經(jīng)驗本身,展開了 “對林語堂一生著述進(jìn)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理解 ”,而這項工程的現(xiàn)實目的也足夠昭然:從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中將 “失蹤者 ”林語堂打撈出來,他當(dāng)時的聲音何以消弭于浪潮固然在被討論之列,但展示這一另類話語實踐,其一,或可為中國文化找尋重生之道;其二,亦可 “為中國于全球時代現(xiàn)代性之路鋪墊新的范式 ”。
一 自由主義批評家
一九三○年,林語堂聯(lián)合《中國評論》同人,在滬創(chuàng)辦 “自由主義普世派俱樂部 ”。俱樂部成立一年之后的聚會上,林做了題為《什么叫自由主義》的演講,他說:“外國人的風(fēng)俗、法律和宗教乍一看上去毫無道理,但是新的自由主義的態(tài)度就是要努力在這種無理中找出道理,這種態(tài)度是人類歷史上新近的發(fā)展,毫無自然本能來維系之。只有通過正確的教育,擁有強(qiáng)大的包容心,再加上精神的努力,我們才會對外國人的習(xí)俗培養(yǎng)出一種自由主義的態(tài)度。”此間對自由主義的定義,與胡適在不同場合的表述(欣賞與容忍他者)不謀而合,反觀魯迅對自由的認(rèn)知,則更多地指向了反抗專制。在中國現(xiàn)代性的初始階段,其知識結(jié)構(gòu)內(nèi)部便分化出兩種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這令人想起林肯在一八五八年呼吁南北方團(tuán)結(jié)時說的話:A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cannot stand(破裂之屋難自立)。然而,即便在三十年代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的活動里,我們也很難看到團(tuán)結(jié)。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僅僅是一個被暫時保持一致的目標(biāo)艱難維持的松散同盟。其目標(biāo)大同小異,唯暫時性始終如一。具體到林個人的話語實踐,主要關(guān)系到三件事。盡管他關(guān)于自由主義的認(rèn)識更切近胡適,但這三件事幾乎都與魯迅有關(guān),因此,林語堂和魯迅的關(guān)系變化—他在為魯迅所寫悼文中有云:“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于其間也 ”—也就 “可給我們探索此遺產(chǎn)之意義提供一個切入口 ”。
第一件事涉及林語堂二十年代參與《語絲》的活動。如我們所知,《現(xiàn)代評論》和《語絲》這兩份雜志皆創(chuàng)刊于國民革命漸趨高潮的一九二四年底。《現(xiàn)代評論》的撰稿人多是北大英文系的教授,他們一般留學(xué)歐美;《語絲》的撰稿人則是北大中文系學(xué)者,泰半有日本留學(xué)的經(jīng)歷。雙方教育背景與政治理念的差異,在北京女師大事件中被放大且點(diǎn)燃了爭論的引線。《語絲》派和《現(xiàn)代評論》派固然抵牾相對,在《語絲》派內(nèi)部其思想亦未必完全契合:周作人根據(jù)他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提出了作為創(chuàng)作風(fēng)格與政治姿態(tài)同一的 “費(fèi)厄潑賴 ”(fair play)精神;魯迅則在一九二六年,于其另創(chuàng)的《莽原》雜志上發(fā)表《論“費(fèi)厄潑賴 ”應(yīng)該緩行》,主張 “痛打落水狗 ”。林語堂對周氏兄弟的分歧表示同情,他既稱贊 “啟明所謂 ‘費(fèi)厄潑賴 ……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也只好努力鼓勵 ”,也為魯迅的文章畫了一幅《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以示理解。“費(fèi)厄潑賴 ”與貢斯當(dāng)提出的 “現(xiàn)代自由 ”(the liberty of the moderns)相去不遠(yuǎn),但是如作者所說,“‘費(fèi)厄潑賴 原則與 ‘打狗 精神之爭最初起源于林語堂提倡國民應(yīng)該 ‘談?wù)?”,也就是說他同樣未曾偏廢貢斯當(dāng)所謂的 “古代自由 ”(the liberty of the ancients)。
第二件事涉及林語堂在武漢、上海期間撰寫專欄,創(chuàng)辦雜志的活動。一九二六年張作霖進(jìn)入北京,開始對革命者展開鎮(zhèn)壓,至此大批知識分子選擇南下,其中就有即將出任廈門大學(xué)文學(xué)院院長的林語堂和受林語堂之邀一同加入的魯迅。只是魯迅到了翌年一月便離開廈門,三月林語堂也選擇前往武漢,八月又赴上海。前一時期對周作人以 “費(fèi)厄潑賴 ”為名的容忍精神的認(rèn)可,在武漢擔(dān)任《國民新報》主編期間則轉(zhuǎn)向了對魯迅 “國民性批判 ”的支持。《給玄同的信》、“薩天師語錄 ”等文為林語堂一生反傳統(tǒng)最峻急的時刻。不過,這種將建構(gòu)現(xiàn)代中國寄托于 “性之改造 ”的思想,很快就被林語堂賦予獨(dú)特形式。“大革命 ”的結(jié)局令中國的民主之路受阻,它致使 “在三十年代,乃至其一生,林語堂都要兩面作戰(zhàn),抵抗 ‘雙重危險 ”。前文所說獨(dú)特形式,指的便是林語堂將麥烈蒂斯(Meredith)的“俳調(diào)之神 ”與中國儒道文化里的寬容達(dá)觀加以融合,從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幽默 ”。這既是他對 “費(fèi)厄潑賴 ”精神的復(fù)歸,也是林語堂就踐行自由主義 —“現(xiàn)代自由 ”與“古代自由 ”——通盤思索之后做出的回應(yīng)。某種意義上,幽默糾正了他前一時期關(guān)于傳統(tǒng)的獨(dú)斷,也是林語堂為爭取言論空間、堅持社會批評創(chuàng)造的獨(dú)特方式。可是就像魯迅對 “費(fèi)厄潑賴 ”的態(tài)度一樣,他于此時林語堂熱衷談?wù)摰?“幽默”同樣難表贊同。伊卡洛斯墜落的隱喻不只暗示了三十年代的林語堂將另尋現(xiàn)代中國的出路,也暗示了二十年代是林語堂與魯迅兩人一生中為數(shù)不多 “思想親密 ”的時刻。
第三件事是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的成立,這是魯迅、胡適與林語堂三人為自由主義理念的最后一次合作。一九三三年一月起,林語堂和魯迅恢復(fù)了中斷三年有半的交往。錢鎖橋?qū)@次聯(lián)合的看法非常有趣:“它一開始就是一個十分尷尬的結(jié)合。雖然他們似乎都同意推動國民政府治下的人權(quán)保障和法制文化,但一開始他們其實都有各自的目的和主張。”就廣義的自由主義而論,正因為爭取自由的態(tài)度如此涇渭分明,林語堂又一次面臨當(dāng)初那種 “兩面作戰(zhàn) ”的窘?jīng)r:他“參與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向法西斯右翼爭人權(quán),但他馬上發(fā)現(xiàn)他不得不又要與布爾什維克左翼作抗?fàn)?”。在我看來,于林語堂身上反復(fù)出現(xiàn)的這一二律背反,恰恰也是他關(guān)于自由主義的核心認(rèn)知:否定前者并不意味著同情后者,反之亦然。誠如他在一九三六年撰寫的《中國新聞輿論史》一書中的自況:“我提倡幽默,兩派都不參與,感覺自己一個人在黑暗中吹口哨。”
二 民族主義者
林語堂對現(xiàn)代中國知識結(jié)構(gòu)的貢獻(xiàn),除了自由主義的關(guān)切以外,以思想傾向論,民族主義的傾向同樣貫穿了他的一生,而且林語堂的民族主義顯然要比他的自由主義復(fù)雜得多。作者關(guān)于這一部分的論述,位列本書題旨的核心地帶。
一八九五年,林語堂生于福建漳州的一個基督教家庭。他的出生年份處在兩千多年的政治體制行將破產(chǎn),而中國也開始義無反顧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之際;他的家庭則是 “現(xiàn)代性在中國推進(jìn)的一種特殊形式 ”。這兩者從一開始就規(guī)定了林語堂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關(guān)系,有別于大多數(shù)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一九一一年,從廈門的教會學(xué)校尋源堂畢業(yè)后,他的家人送他前往上海的圣約翰大學(xué),先是一年預(yù)科的學(xué)習(xí),接著是四年大學(xué)生活,一九一六年他以優(yōu)秀生的身份畢業(yè)。這種獨(dú)特的教育背景,使得林語堂在一九一六年赴北京之后即遭遇到“文化反差 ”。錢鎖橋從兩方面分析了這一現(xiàn)象:一方面,謂之與中國現(xiàn)代性共生顯然另有一層含義,此即從時間與空間中導(dǎo)出的心理因素,讓林語堂對于現(xiàn)代性的接受早于國家而具備了得天獨(dú)厚的優(yōu)勢,即契合了新文化運(yùn)動中全盤西化的部分;另一方面,從新文化運(yùn)動自身的邏輯出發(fā),全盤西化必然還要延伸到對中國本土文化的重估上來。當(dāng)此之境,這一文化系統(tǒng) —對林語堂而言是亟待認(rèn)同與理解的事物 —在新文化運(yùn)動的自我設(shè)計里,卻是旨在攻訐和擺脫的對象。能否堅持這一邏輯,令他倍感疑惑。但最讓他感到尷尬的,還是當(dāng)他身邊的知識分子開始旗幟鮮明地 “反傳統(tǒng) ”時,他甚至無以界定 “傳統(tǒng) ”的內(nèi)涵與外延:他根本就不具備談?wù)摳母?“傳統(tǒng)”的資格。正因如此,置身新文化運(yùn)動的風(fēng)暴眼內(nèi),林語堂意識到自己亟待要做的,便是去彌補(bǔ)自身的知識結(jié)構(gòu)漏洞,“探尋自己作為中國學(xué)人的文化根源 ”。
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年,林語堂出國留學(xué)。在哈佛攻讀碩士學(xué)位期間,他上過兩門白璧德的課程,而白的中國學(xué)生大多是 “學(xué)衡派 ”的成員。附帶說一句,倘若我們仔細(xì)比較白璧德與其中國門徒的思想,就會發(fā)現(xiàn)兩者實際上并不一致。白璧德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告誡,乃是基于西方現(xiàn)代性的教訓(xùn)提出的,他的那些 “學(xué)衡派 ”門徒則僅僅遵照了白璧德 “反對和傳統(tǒng)切割的態(tài)度 ”,而遺忘了作為雅努斯的現(xiàn)代性的另一面,即中國現(xiàn)代化的程度與西方不可同日而語(這是中國必然要現(xiàn)代化的根底所在)。兩相來看,反倒是林語堂完整地踐行了白璧德關(guān)于 “兩個文化傳統(tǒng)在人文層面互相印證,共同構(gòu)成人類的永恒智慧 ”的觀念:他當(dāng)然明白自己的老師指出的以 “進(jìn)步 ”之名棄絕傳統(tǒng)的愚昧(為此才反復(fù)給不斷激化的文學(xué)與文化革命降溫);但他也理智地意識到這場需要被糾偏的革命自有其合理性。及至一九二一年林語堂到萊比錫大學(xué)師從孔好古,閱讀《皇清經(jīng)解》和《漢學(xué)師承記》等漢學(xué)經(jīng)典,用德語撰寫博士論文《中國古代音韻學(xué)》,便是他間接給新文化運(yùn)動的 “疑古 ”風(fēng)氣降溫之舉。一九二三年留學(xué)歸國之后,林語堂已不同于那些高歌猛進(jìn)的知識分子,他開始不諱言 “與傳統(tǒng)告別 ”思潮中非理性的因素,然而,這也不妨礙他繼續(xù)是新文化運(yùn)動中的一員。林語堂與一般主張充分現(xiàn)代化的知識分子的心理順序相反而實際方向一致。毋寧說,他是以 “學(xué)衡派 ”的方式介入了新文化運(yùn)動,以此促進(jìn)了 “傳統(tǒng)中國 ”與“現(xiàn)代中國 ”的融合。
在歐美留學(xué)期間,林語堂以 “不在場 ”的姿態(tài)延續(xù)了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何以現(xiàn)代的思考,其思考的成果在他回國之后立刻付諸實踐。第一件事,便是介入 “整理國故 ”的運(yùn)動。在作者看來,胡適發(fā)起這項運(yùn)動,名義上承接了晚清學(xué)人的研究,但實質(zhì)上 “它是整個新文化運(yùn)動解構(gòu)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 ”,“其主旨是要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去魅 ”。去魅,也就是令傳統(tǒng)文化不復(fù)為文明之本,降格為現(xiàn)代科學(xué)方法操練的場域。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提出的新文化事業(yè)的四大組成部分 —研究問題,輸入學(xué)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并非有什么邏輯層遞的關(guān)系。在國故成為現(xiàn)代方法實操對象的意義上,與其說兩者有必然聯(lián)系,還不如說 “輸入學(xué)理 ”與“再造文明 ”之間更為密切。針對這項運(yùn)動,林語堂發(fā)表《科學(xué)與經(jīng)書》,一面呼應(yīng)了胡適的號召,另一面也對胡適過分看重 “輸入學(xué)理 ”提出了批評。在此文中,他還展望了中國語言學(xué)發(fā)展的前景,而這將是他余生在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用力最勤的事業(yè)。關(guān)于這方面,本文僅略作交代:首先,林語堂留學(xué)歸國之后,延續(xù)其博士論文的方向發(fā)表了一系列論文,同時創(chuàng)建北大研究所國學(xué)門方言調(diào)查會,提出對中國各地方言加以調(diào)查記錄,由此擴(kuò)大了古音韻學(xué)與語文學(xué)的研究范疇;其次,他反對漢語改良運(yùn)動中過分激進(jìn)的主張,即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之后,進(jìn)一步實現(xiàn)漢字的徹底拉丁化。林語堂從理論與現(xiàn)實兩點(diǎn)入手,指出較為合理的做法是在文字上對漢字進(jìn)行簡化,在注音系統(tǒng)上對威氏拼音系統(tǒng)稍作修改(林語堂晚年曾極力贊揚(yáng)大陸實施簡化漢字的舉措,且發(fā)表文章敦促海外華人效仿學(xué)習(xí));最后,林語堂在海外期間發(fā)明了中文打字機(jī),晚年又獨(dú)自編創(chuàng)了一部漢英大詞典。凡此種種,均可見其意見與志業(yè)的一貫。總的來看,林語堂的民族主義除了肯定本國文明融入現(xiàn)代性的必然,思慮本國文明何以現(xiàn)代化的道路,也有它否定性的維度,后者涵蓋了林語堂從重審自身教育背景起始的一系列對殖民主義話語加以反抗的行動,直至其最終提出關(guān)于作為“文明 ”的中國與作為 “民族 /國家 ”的中國同現(xiàn)代性關(guān)系的闡釋。
三 普世主義批評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討論現(xiàn)代性時,林語堂顯然有兩套話語:其一是批判已經(jīng)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國家的現(xiàn)代性(如美國),其二是對尚未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國家的現(xiàn)代性予以肯定(如中國、印度)。在一九三九年《吾國與吾民》的再版中,新增了題為《新中國的誕生》的第十章。這篇長文是林語堂就后者所做的最為充分的闡釋。于此文,他明確提出了中國現(xiàn)代性的源頭是十九世紀(jì)以降,作為文明的中國不得不面對其他文明這一事實。因此,當(dāng)中國面臨被瓜分甚至生死存亡的考驗時,傳統(tǒng)中國就需要讓位于現(xiàn)代中國,中國現(xiàn)代化的道路由此便是不可避免的。此后他對西方社會的現(xiàn)代性多有抨擊,兩者實不矛盾。林語堂對現(xiàn)代性的肯定,只是基于以下事實:既然在現(xiàn)代性的浪潮下,只有作為民族 /國家形式的中國才能存在,而文明以前者的成立作為自身存在的根據(jù),那么中國的當(dāng)務(wù)之急,便不是批判效率至上導(dǎo)致的異化,而是承認(rèn)現(xiàn)代性是一次拯救。明確了這一點(diǎn),亦可很好地理解一九二四年泰戈爾訪華期間,林語堂對他那頗可玩味的態(tài)度。當(dāng)泰戈爾來到中國時,圍繞著科學(xué)能否回答人生觀的 “科學(xué)與玄學(xué) ”之爭已持續(xù)一年之久,因此泰戈爾關(guān)于 “東方精神文明 ”的高度贊揚(yáng)便給了張君勱以支持,而吳稚暉則嘲諷泰戈爾的思想是
“貼上佛教詩歌來抵抗敵人的機(jī)關(guān)槍 ”。據(jù)作者在此書提供的信息,林語堂雖然不贊同吳稚暉的論調(diào),但同樣無法忍受泰戈爾認(rèn)為印度無須尋求獨(dú)立解放的政治態(tài)度。之所以說這種態(tài)度值得玩味,便源于他在兩種現(xiàn)代性話語之間做出的區(qū)分,也就是說,在一個尚未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國家內(nèi)部,其知識分子的首要擔(dān)當(dāng)是將它的文明建立在政治獨(dú)立的根基之上,而非如泰戈爾那樣舍近求遠(yuǎn)地批判西方現(xiàn)代的科學(xué)物質(zhì)主義。不同于此前林語堂側(cè)重于民族主義對西方現(xiàn)代性展開批評,當(dāng)他的基點(diǎn)偏向自由主義時,對應(yīng)于兩種話語樞紐,西方現(xiàn)代性亦呈示雙重面目,此即殖民主義話語與工具理性壓倒價值理性的兩分。在這兩者之間,林語堂的一系列言論著述,皆有著清晰的邏輯線索,
后者既是對前者的拓深,也是前者在特定時空下的延續(xù),而僅此一點(diǎn)就足以使他成為魯迅、胡適之外中國現(xiàn)代知識結(jié)構(gòu)的第三個坐標(biāo)。錢鎖橋先生認(rèn)為,林語堂一九三九年發(fā)表《真正的威脅:不是炸彈,而是思想》的文章,標(biāo)志著林語堂重回自由主義的立場,而他的 “批評焦點(diǎn)也從 ‘中國哲學(xué)家 的角度轉(zhuǎn)向?qū)φ麄€世界現(xiàn)代性的普世批評,其批評議題集中于世界范圍內(nèi)的戰(zhàn)爭與和平 ”。在林語堂看來,正是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奉行效率至上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衍生出了強(qiáng)權(quán)、貿(mào)易、種族等相關(guān)政策,而這一點(diǎn)在整個西方世界呈現(xiàn)出整體性的邏輯同一 —甚至在同盟國與協(xié)約國之間也未見得有何差異。此時的林語堂已將現(xiàn)代性的弊端具體界定為 “地緣政治學(xué) ”。基于這樣的認(rèn)識,他關(guān)于現(xiàn)代性的最后探索,也開始涉及新的領(lǐng)域:探索一種和平哲學(xué),這種哲學(xué)能確保世界文明在未來免遭現(xiàn)代性的滅頂之災(zāi)。
毋庸置疑,林語堂晚年回歸基督教,而基督教思想成為他和平哲學(xué)的一部分,與其陷入對西方現(xiàn)代性的批評困局有著緊密關(guān)聯(lián)。無論是以強(qiáng)調(diào)價值的儒家人文主義去調(diào)和強(qiáng)調(diào)事實的 “十九世紀(jì)膚淺的理性主義 ”,以佛教的因果報應(yīng)理論去抑制西方的帝國主義(《中國印度之智慧》),還是從美國的圣賢作品中挖掘平和中庸之道(《美國的智慧》),抑或創(chuàng)作一部烏托邦小說,以文學(xué)的形式勾勒和平哲學(xué)的輪廓(《遠(yuǎn)景》),他的著述都沒有產(chǎn)生太大回應(yīng),也無力改變嚴(yán)苛的現(xiàn)實。他認(rèn)為和平哲學(xué)始于人們開始思考和平,這就要求將人作為有人性的人來理解,而不是作為 “經(jīng)濟(jì)人 ”對待,然而個體的自由依然在現(xiàn)實前節(jié)節(jié)敗退。他預(yù)測 “美國式和平 ”將會在兩極對抗中勝出,但這種預(yù)知的勝利又令他深感失望。質(zhì)而言之,林語堂意識到了一個比美國的政治環(huán)境還要嚴(yán)峻的事實:僅僅依靠人文主義(東西方的智慧),完全無力緩解普世的現(xiàn)代性困境,即現(xiàn)代性的極端形態(tài)“地緣政治學(xué) ”對個體自由與世界和平構(gòu)成的威脅。也因此,林語堂在一九五九年出版了他深思熟慮之后寫成的自傳《從異教徒到基督徒》,宣告自己 “重新發(fā)現(xiàn)耶穌 ”。
不妨簡單梳理一下林語堂與基督教關(guān)系的諸階段:他的成長環(huán)境與教育背景,先天決定了他在一九一六年到北京以前同基督教的親密無間;自林語堂到清華任教,在日漸覺醒的民族意識的觀照下,原本融洽的關(guān)系出現(xiàn)裂痕,直至破裂。基督教直接導(dǎo)致了林語堂對
“民族主義欲望 ”的認(rèn)同 —盡管是以非常奇怪的方式。三十年代去國之后,林語堂延續(xù)了這種信仰上的斷裂,并且一直持續(xù)到他最終承認(rèn)人文主義無力糾正現(xiàn)代性弊端的時刻。某種意義上,林語堂對基督教態(tài)度的幾經(jīng)變化,包括促成他最終 “重新發(fā)現(xiàn)耶穌 ”的,“并非表明林語堂的宗教信仰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而毋寧理解為是在某一時刻置身不同立場的特定選擇。“重返基督教 ”標(biāo)示的,正是林語堂痛感現(xiàn)代性沉疴遍地而發(fā)乎心底的抵抗,但也是最后的抵抗。晚年的林語堂相信構(gòu)建一個理想的未來,不僅需要東西方的智慧相輔相成,也有賴宗教智慧和異教智慧(人文主義)的共同啟示。在其政論集《匿名》結(jié)尾處,他謹(jǐn)慎地引申了耶穌的名言,寫道:“假如我們想要一個未來世界,其間人只是一個工具,只能 ‘為國家獻(xiàn)身 ,我們可以做到;假如我們想要一個未來世界,其間窮人和出身卑微者不會受到壓迫,我們也能做到。世界必須做出選擇。”
《費(fèi)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