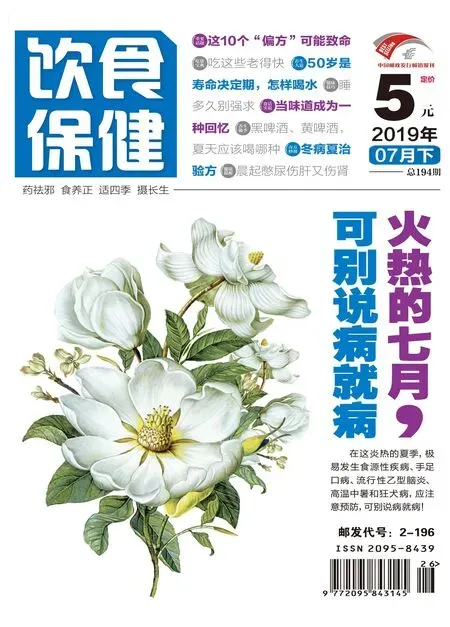當味道成為一種回憶
珊安文

說到吃,才發現自己這方面的貧乏。以前嗜辣,無論什么菜,撒上些朝天椒碎末就很滿足了,如果能再撒些蔥絲,那就更是覺得好吃得不得了。直到后來去了深圳,慢慢適應口味清淡、不撒辣子的廣東菜,才逐漸體會到原汁原味的妙處。
每當我想到家鄉贛州時,還是不免要回憶起曾經愛吃的小食。
清晨,離家不遠的菜市場對面有許多小食可充作早餐,如果起得早,可跑步過去,一邊逡巡,一邊挑選。沿著馬路邊,可依次看到有人卷起袖子,拿著長筷,面前支一口大油鍋在炸油條。油鍋旁有一張大面板,搓面的往往是女人。只見她十指靈巧地將面團拉成長條,輕輕一捻后放入油鍋,不一會兒,沉沉浮浮的條狀面便膨脹成了一條條金黃色的油條。和賣油條一樣支著口鍋的是賣蔥油餅的,鍋稍小,支在三輪車上,也有塊略小的面板,正好在上面將調好的面粉和成圓餅狀,賣蔥油餅也需要兩個人,一人煎餅,一人收錢兼照顧爐火。剛煎好的蔥油餅散發著很好聞的蔥香,印象太深了!
據說原為四川小吃的千層餅,也錯把他鄉當故鄉了,如今這種小吃在贛州遍地開花,其實它和蔥油餅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它們一個是素的,只放蔥花,另一個是葷的,里面夾了肉餡。穿過熱騰騰的包子饅頭鋪,就是我最喜歡的鍋盔餅攤了,那是由一個個子不高的男人守著的,在他的面前擱了一摞鍋蓋大小的煎餅,有厚有薄,隨顧客喜好挑選,厚的綿軟柔韌,薄的酥脆焦香。那個男子每天只做那么多,從不高聲叫賣,但往往是不到七點半就賣完了。再往前走,還能發現一種養眼的小食——燙皮,那是用小磨將米和韭菜磨漿做成綠色的外皮,內里裹著酸菜、豆干、辣椒、蘿卜干等,小小的一塊,放到嘴里咬一口,涼而滑的外皮,還有韭菜的芳香,特別開胃。賣薯粉的架勢就有些大了,一個薯粉攤子加數張桌子和椅子,就占了一大塊地。薯粉是家鄉人常吃的食物。
先拿部分紅薯粉煮熟,再和生薯粉調漿,然后用漏勺漏進開水鍋里,煮熟后有點像面條。各家漏勺的孔有大有小,所以做出的薯粉也有粗有細。要吃的時候,將薯粉在沸水鍋里過一過,撈起瀝干,撒上紅辣椒、綠蔥段,最后放入各種調料并滴幾滴麻油,一碗好吃的薯粉就做好了。薯粉攤子有時還會兼賣春卷,圓形的薄面皮疊得規規矩矩,里面裹了餡,餡也是各家不同,但最多的仍是韭菜、豆干、辣椒等混合料。把春卷放油鍋里炸成金黃色,盛出便可吃。運氣好的時候會遇到賣豆腐花的,挑擔的常常是一位腰身佝僂的老婆婆,那一邊一只的木桶,皆用白布遮得嚴嚴實實。掀開白布,便能看到一只桶里盛著白玉脂般的豆腐花,另一只桶里盛著切好的蔥絲、辣椒末,醬油、芝麻油等調料。如果有人要買,老婆婆俯身用一只鐵勺熟練地在豆腐花上削一薄片,再削一薄片,一片一片地削入碗里,那桶豆腐,還是平整如初,而碗里的豆腐花卻盈盈地滿了。喜吃咸的,便澆上調料,撒些蔥絲辣椒末,最后還要滴幾滴麻油……喜食甜的,老婆婆會將蜜糖水壺遞與食客,任他自己愛澆多少澆多少。說到豆腐花,便讓我想起了用仙人草煎汁做成的涼粉,這一白一黑相反的顏色,竟然有著同樣的質理,而且都是顫巍巍的盛在木桶里,只不過一個會在早晨賣,一個是在炎炎夏日的午后出現。這種涼粉有些與眾不同,它極黑,有濃重的草藥味,用刀劃碎后,撒白糖或淋蜂蜜拌勻,便可大啖一番。
讓我最懷念的還數艾米馃。二三月間,艾草在田畦上長出了毛茸茸的嫩葉,我們挎著小籃,在田間尋覓。當艾草裝滿了小籃的時候,指頭已染上了一層青色,聞一聞,是青草苦澀的香。回家后,母親把采回的艾草洗凈,放入沸水鍋里煮出一鍋濃綠,然后再和入面粉揉搓,等到搟皮包入餡料捏成餃子狀后,放進蒸籠里大火蒸熟。等熱騰騰的白氣散盡了,但見一只一只青黑色的艾米馃乖順地躺在蒸籠里任人拾取。
當味道成為一種回憶時,對家鄉的懷念就以小食的出現而具體化了。記得某年春寒,我在老街附近徘徊,離街不遠的是一道長長的古城墻,老街上是年深月久的青石板,濕漉漉地泌出些水氣,兩邊都是木制結構的老屋,門大多虛掩著,從門縫里就能看到鮮活的百姓人家。我忽然看見有一戶門口擺出了一個大簸箕,并且用白布遮了,旁邊立著的玻璃柜里盛了些過年時才能見到的油炸馃子。我看這像是做買賣的,便上前掀起了白布,原來這是一簸箕青黑色的艾米馃。屋里的女人看見有人上前,便出門說是自家做得太多了,吃不完才想著賣些出去。我買下的那艾米馃,足有半個手掌大,捂在手里像只小暖爐。我這樣一路吃回家去,居然感覺它才是這一年吃過的最好小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