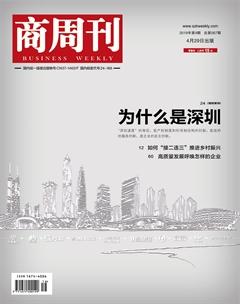特區的制度試驗
張軍

深圳在經濟管理體制上進行的種種變革和對新體制的試驗一開始就對中國經濟改革有了全局性的價值。深圳今天依然算是中國最市場化的經濟體,像華為、中興和萬科這樣的公司出現在深圳而不是上海,一點都不奇怪。
我清楚地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后,包括在90年代初的一段時間里,總能聽到一些聲音,特別是經濟學者對深圳經濟特區的比較負面的評價和批評。在本節,我想討論一下深圳的試驗在挑戰原來的計劃管理體制和試驗新的體制方面所做的貢獻。在我看來,這個貢獻應該是深圳特區對中國經濟轉型的最大貢獻。而有意思的是,30年來在對深圳的批評和質疑中大多數針對的卻是它的產業結構和增長模式,忘卻的是它在體制試驗上的貢獻。
在我自己的書柜里藏有多本關于深圳特區的研究著作。很多我的學生曾經在我的書柜里發現這些有關經濟特區的文獻資料時都會覺得奇怪,那個時候我怎么會對經濟特區感興趣呢?其實,在復旦大學讀書期間,我并沒有把深圳特區作為我的研究題目,一直到了90年代初去英國薩塞克斯大學( Universitv ofSussex)之后,才對經濟特區試驗和沿海發展戰略有了一些接觸,因為那個時候我的指導老師華大偉( David Wall)先生正在從事關于中國特區和沿海發展戰略的研究。我后面還會再來提到這些事情。總之,因為有了這樣一個需要參與特區和沿海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的機會,我才不得不收集了一些早期的研究文獻。現在看起來,調查和記錄深圳特區體制創新試驗的文獻是非常珍貴的資料了。
我想,在當時的政治和經濟局限下,深圳特區建設的一開始就必然遭遇整個經濟管理體制的制約。盡管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廣東省制訂了特區條例,但要執行這個條例,則需要創新體制,打破原來的管制,需要得到特區之外的舊體制在很多方面的容忍,讓位和配合。深圳仍然要與它的上級主管部門,乃至中央部委打交道。所以,深圳在經濟管理體制上進行的種種變革和對新體制的試驗一開始就對中國經濟改革有了全局性的價值。事實上,深圳今天依然算是中國最市場化的經濟體,像華為、中興和萬科這樣的公司出現在深圳而不是上海,一點都不奇怪。
深圳在經濟管理體制上的改革和創新涉及很多方面。首先它需要創新融資制度;需要改變原來體制的投資管制;需要進入競爭機制;需要改革外匯管理體制;需要突破原來的土地管理和經營模式;需要允許和建立勞動力市場;需要政企分開;需要改革和建立新的行政官員治理;需要有地方的立法權;需要改變計劃經濟的工資決定和福利分配機制;需要改變商品的計劃定價體制;需要引進新的激勵模式。而深圳在這些方面對新體制的試驗對中國其它地區的經濟體制改革和開放進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我們今天在中國經濟中觀察到的許多新體制和流行起來的新規范,幾乎都能在25年前的深圳找到它們的影子。
一個很好的例證大概就是我書柜里藏著的谷書堂先生主編的《深圳經濟特區調查和經濟開發區研究》的這本書了。這本書1984年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主編在前言中這樣說: “今年四月,黨中央、國務院又作出重大決定,繼續擴大開放地區,把天津市列入了新開放的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之中。因此,如何結合天津的實際情況,學習、借鑒深圳經濟特區及其所屬的蛇口工業區的經驗,更好更快地興辦開發區,實現對外開放,便成了人們普遍關切的問題。基于這種客觀情勢,我們也先后分兩批去深圳和蛇口,對其開發建設、經濟管理體制、引進外資和技術、計劃與市場、對內聯合、勞動和工資、產品內銷和外銷、引進外資銀行、物價和人民生活,以及典型企業等多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實地考察。”
作為一個特區并必然會受到香港成功經驗的影響,深圳在突破舊的體制和探索新的體制方面做了很多的試驗和改革。我在這里不想逐一討論,只是選擇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點評,希望能“以偏概全”。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記述深圳在體制上的這些改革試驗,是因為過去20年來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中總是能找到深圳早期試驗的影子。讓我擇取以下幾個片段:
第一,對建筑工程廢除官方包辦的敝習,引進和采取公開招投標制度和承包制( contracting)。今天中國在基礎設施和公共工程建設中早已建立起來了這樣一個國際規范的、透明的竟投標合約制度,可是它最早是在深圳的蛇口工業區被嘗試的。根據調查,嘗試這樣新的體制加快了工程的建設工期和建筑的速度。例如,在實行招投標制度之后,六層住宅樓從200天施工的時間縮短為100天。高層建筑從原來25天一層的速度減少到了3 5天。競爭招投標制度也進一步派生出更加細致的分工和專業化的合約結構,即承包公司內部再進行的逐級下向的發包制度( subcontracting),而且承包出去的不僅是工程,還承包造價和質量。經濟學家對這樣的發包制度是有成熟的理論分析的。“承包”(或者包工)這種市場合約體制今天成為中國在建筑施工領域的基本制度規范。
第二,人事制度改革。在人事體制方面,深圳蛇口工業區最早的試驗涉及的只是屬于經濟學和管理學上所講的“人力資源管理”的范疇。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政府部門的主管的任命在蛇口工業區都從過去的上級主管部門的直接委派改革成聘任制度,取消職務終身制度。聘書上寫明的是職責、權利、待遇、解聘和續聘等內容,公開透明。一般任期為兩年。這樣的改革試驗顯然加快了管理部門的人力資本的更新速度,為職業經理人市場的建立和后來向公司治理模式的轉型奠定了基礎。
第三,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中國自從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之初就實行“統包統配”的固定用工制度。它的經濟學性質被形象地描述為“鐵飯碗”和“大鍋飯”。深圳的勞動就業制度的試驗是1980年左右從在蛇口的外資和合資企業中開始的。之后推廣到整個深圳特區。1982年深圳根據蛇口的經驗制定了《深圳市勞動合同制暫行辦法》,把勞動合同制作為特區的主要用工形式。眾所周知,勞動合同制的引入需要有完全社會化的新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持,所以深圳率先在全國建立起了由勞動保險公司統籌辦理的“社會勞動保險基金”。由這個基金來解決勞動合同執行中因為解雇和辭退等原因造成的職工困難補貼和退休金的來源問題。基金由企業和職工按月交納。在這個制度的試驗中,深圳采取了“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雙軌過渡的方式,以避免就業體制轉軌引起的社會成本過高的問題。實際上,這個試驗對其它地區改革勞動就業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經驗。
第四,工資決定機制的改革。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必然也要求改革原來的工資決定機制。蛇口工業區最早的工資決定是按照十類工資區的標準支付基本工資和基本工資的1 1 5倍的工業區補貼。盡管在當時這個工資水平大大高于內地,但依然是延續計劃體制的做法的。而且到了1982年前后,其弊端越來越暴露出來。根據南開大學經濟學家對蛇口工業區1 3家企業的工資改革的調查,1983年10月蛇口開始對工資決定機制進行改革,主要是實行多元工資制度。根據他們的調查,蛇口工業區改革后的工資由基本工資加崗位、職務、職稱工資,再加邊防津貼和副食品補貼,最后加浮動工資四大部分組成。根據1984年3月的統計,在工資總額中,基本工資占30.50-/0,兩項補貼占10 30-/0,崗位、職務和職稱工資占37 2%,而浮動工資占22%。
在這個工資結構中,基本工資、邊防津貼和副食品補貼是基本固定的,因此真正可變的是工資的另外幾項內容,即崗位、職務、職稱工資和浮動工資。而且,蛇口工業區的崗位、職務和職稱工資被細分為15個等級,最高158元,最低30元。浮動工資是浮動的,其來源有三:(1)按照人均工資提取每月14元的獎金;(2)每月16元從基本工資和崗位、職務和職稱工資中提取的浮動部分;(3)從利潤留成中提取的基金。
第五,關于土地批租制度的引入。這是中國經濟30年來能在財政分權的狀況下實現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制度。也是隨著問題的暴露最近幾年在中國的學術界最有爭議的一個制度。
對于深圳特區而言,土地批租制度的引入顯然是為了解決融資問題的需要。據說,就在1979年4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向鄧小平匯報廣東關于單獨管理和特殊政策的設想時,曾經提出中央給予資金上的支持,但是小平的回答是“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而吳南生1980年到深圳負責特區的基本建設(所謂的“四通一平”)時,除了來自銀行的3000萬元貸款,能想出辦法的也就是土地收入了。他們在開發羅湖小區時曾經估算,土地按照每平方米5000港幣計算,可用作商業用地40萬平方米的總收入可以達20億港幣。
第一步,深圳特區先嘗試了有償使用國家土地的制度。1982年,深圳最終起草頒布了《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暫行規定》,率先對劃撥土地進行了有償、有期使用的改革。規定還說明了各類劃撥用地的使用年限及土地使用費的標準。其中,工業用地最長年限為30年;商業用地20年;商品住宅用地50年;教育、科技、醫療衛生用地50年。
第二步,在1987年之后,深圳部分借鑒了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率先在特區試驗了土地出讓或者批租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取得土地的投資者或者開發商,為了獲得一定年限的使用權,需要交納一筆出讓金。1987年的下半年,深圳特區曾分別將三塊土地先后以協議、招標和拍賣的方式出讓使用權,獲得的地價款2000余萬元。
在總結土地有償使用和土地出讓試驗的經驗的基礎上,《深圳特區土地管理條例》于1988年1月3日正式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相分離。政府擁有土地的所有權,但土地的使用權不但可以出讓,而且可以轉讓,抵押,出租。就在同年的4月,中國的《憲法》進行了再次修改,其中將“土地使用權可以轉讓”寫入了《憲法》,等于追認了深圳土地制度改革的合法性。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地方政府的土地批租制度開始在特區之外被廣為采用,成為各級地方政府的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土地批租制度”是香港的譯法,其對應的英文為“the land leaseholdsvstem”。在這個制度下,批租只涉及土地的使用權,不改變土地的所有權。業主取得的只是某一塊土地在一定年限內的使用權,以后業主之間能轉讓的也僅僅是土地的使用權。而當批租期限屆滿,承租人就要將這塊土地的使用權連同附屬其上的建筑物,全部無償地歸還給土地所有權人。
深圳率先實行的這個土地使用權與所有權的分離在土地國有制的局限條件下對于城市土地要素的使用和配置效率的改善當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也幫助實現了土地的級差地租。我記得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曾對這個土地的“兩權分離”在中國經濟體制當中扮演的角色給予過很高的評價。根據張五常的解釋,事實上,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權體制,特別是1994年的分稅制度下,中央與地方共享的增值稅的來源主要就是與土地批租不可分離的新增投資和生產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財政分權下形成的激勵模式似乎與一個“租金分成”的模式很類似。
我在這里并不想花篇幅去進一步評價這個土地批租制度以及它帶來的問題。當我要在統計上獲得地方政府的土地批租的收入數據時,我發現并不容易。雖然1 994年至今,土地批租的收入全歸地方政府所有,但我的學生給我查找的數據卻多是涉及土地的稅費收入,而并沒有批租的收入。的確,從統計上看,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批租所獲得的收入并不能完全從政府的稅費收入和財政預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事實上,在中國與土地有關的各種名義稅種和稅率中,即使包括最大的土地增值稅,來自土地的各種稅費也最多占到地方預算財政收入的5%8%,而土地批租的收入是不列入地方政府的預算收入的。例如,在2006年中國的城鎮土地使用稅和土地增值稅還不到250億元,當然也就不會超過當年3萬億稅收收入的80-/0。
但是,來自土地出讓的收入到底會有多大呢?有各種不同的估計。因為地區和城市的不同,現有的估計值落在財政預算收入的15%35%的范圍內。對于相當一部分的中國縣市而言,可能用于基礎設施投資的財政資金中有60%70%是來自土地出讓金的。這就是為什么人們今天往往把土地出讓金戲稱為地方政府的“第四財政”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