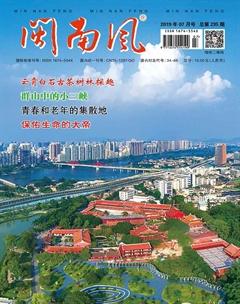撫慰日常生活的呼吸
柯國偉

一
何謂日常,就是平常、循規蹈矩,司空見慣。而日常生活,就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機械式的、沒有大驚喜的重復生活。
就像我在將近三年的時間里,過著一種極其類似的生活。在一個小縣城,編一份縣報,做一個小記者。每周一、周二忙著編報紙,直到周二晚上定稿,完成每周一期的編排任務。這兩天,我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有時,還要臨時外出采訪,回來后馬上寫稿,完成一篇報道。
編完自己的版面后,我們4個編輯還要交換各自版面校對文字,以免因為閱讀慣性的疏忽,出現錯誤。而校對并沒想象中的輕松,在校對新聞版面時,很多通訊員的文字表達不清楚,詞不達意,修改文章不只是改一個詞,而是整句話、整段話都要刪改,并幫他們補上一兩段,自圓其說,有時還要為他們重寫新標題。遇到一些長文時,常常要把幾千字的文章縮減掉一大半,進行分塊,重新連成一篇有邏輯性的文章。這是我們繁雜的編輯工作,不過,看著各自編出的新版面,何嘗沒有心靈的滿足感和成就感?
我們其實就是這個文字王國的王者,可以定奪文字的一切。及至最后,對所有八版文字用軟件進行掃碼,勘別錯誤。掃碼軟件會提供可疑錯詞讓我們鑒別,有些詞并沒錯,因為放在具體語境中,因此需要人工校對。完成這一切后,打包這期報紙電子版,發送給印刷廠,宣告完成一期報紙的工作。這是另一種生活的存在感和心靈意義所在,我們通過這樣的方式,品嘗攻堅克難的勝利滋味和自己辛苦得來的勞動成果。我們的勞作存在于沒有硝煙的文字思維里,在虛擬的想象空間里建造、構圖新的影像世界。
周三到周五,有時采訪,沒采訪時開始考慮下期版面。沒有主題專版時,我編排“傳統文化”和“祖地文化”兩個版面。然而網絡時代的快速發展,使報紙閱讀迅速式微。辛苦編出的報紙,卻不一定有多少人閱讀。但只要報紙存在,就有它的價值和作用所在,一定會有少數的群體仍在關注,只要把它做好就行。我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來閱讀,但存在本身就有某種特征的象征意義。
在編排過程中,我仍感受到吸吮文化的快感。在編輯“傳統文化”時,我總尋找自己喜歡也符合讀者口味的古代文化,給自己帶來被動的傳統閱讀,這猶如一種精神堅守,就像這紙質媒介。我在領悟古人思想的同時,也在滋養自己的靈魂向上提升,向更高潔的方向飛奔而去,這讓我看到現實的許多浮華與虛妄。而“藝苑”,帶給我愉悅的藝術視覺享受和心靈美感,不論是書法、繪畫,還是剪紙,它們靈動的線條、奇崛的造型、豐富的內蘊,都是種種藝術的心靈語言在訴說。這是意外的饋贈。忽然想,我們不能只把饋贈想象成權利、地位、財富等實在的物質光環,更應該把人的自我滿足感、價值感、尊嚴感當成自我追求的更高目標,如此,方能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到屬于自己的、有存在感的生活。我們也才能活得有價值感,而不是虛妄無為,渾渾噩噩。
當我們真不能改變什么時,不必懊惱,卻可以做好自己,寂靜呼吸。人自身深切的自我反省何其重要,要審慎,細微,在起心動念處,就該清醒地自我覺照。
二
三年的報社工作,讓我不時有些忙碌,靜不下來。有時,出去采訪,會到晚上11點多才回家;有時,拿著相機下鄉拍照一整天,回來就一身疲憊,什么也不想做。八小時的工作外,我的業余時間似乎變少。中午,我常要午睡,只剩晚上和周末的空余時間。雖然采訪不多,但有時也要在晚上和周末進行,這使我寧靜的時間越來越少。
我的記者工作是拿著相機拍照,有時在現場找來椅子拍文藝演出,注意抓拍舞臺上豐滿的視覺效果;有時,在一些活動中跑來跑去,搶拍人物鏡頭,這無法讓人慢慢瞄鏡頭,只能在大概看見人物輪廓時,急按快門,因為人物的表情、動作轉瞬即逝。我覺得自己是生活的觀照者和記錄者,看見生活的變遷和世相百態,這算不算人生經歷的另一種額外收獲,常讓我對生活有了新的看法和感悟。為了保證照片效果,我常從不同角度多拍,拍上百張也是家常便飯。這功夫沒白費,我常能拍到一些效果極好的照片,頗有些得意,而拍照也是自己自學的。在此之前,我從未買過相機,拍過照。這讓我頗有感悟,人都是在歷練與挑戰中成長的,要勇于面對未知的一切。在采訪現場,我還要想辦法同別人交流,拿資料,問問題,了解情況,回來后好寫稿件。這使我不得不外向,練就一身的從容和淡定,而我以前曾一直內向、靦腆。
三年的生活,就在這樣的模塊中輪轉著。但我覺得失去自我,我的靈魂似乎褪色了,不能思考,不能呼吸。我在應付著生活,缺乏足夠的寧靜,有些焦躁。而過去,我是一名教師,生活單純,心思單純,學校、家兩點一線,安安靜靜,有暑假、寒假,平日里有大把的空閑時間休息、寫作。我問自己,這是我想要的生活嗎?其實,和生活內容無關,和生活狀態有關。我不允許自己在這樣繼續下去。
在這期間,我幾乎放棄了文字,只是偶爾寫上兩、三篇。我回望過去,在長達一年的時間里,沒寫下任何一篇文字。在沒有文字的日子里,我又過得如何,是否更好?事實上,我更多的是一種無意識感的存在,忙忙碌碌,記不住多少時光里的影像,從生活的表象里如蜻蜓點水般輕浮地掠過,我的心靈與現實存在明顯的脫離。文字并非有多重要,也不是要通過它追逐什么。但文字是觀照內心的最好方式,當我放棄時,我的靈魂似乎凝固了,我遭到自我良心的自覺譴責。我似乎成了一個不負責任的拋棄者,這使我心靈難安。
但我的靈魂仍需要呼吸,需要種種的心靈色彩,需要在生活的洪流中慢慢學會堅強、獨立和努力。
那么,我應該怎么面對以后的生活呢?安頓好自己的生活,過著平凡而安樂的日子。重拾文字,讓自己的靈魂得到休息與審視,尋找更豐富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樂趣。在工作中尋找更多的價值感與意義,讓自己成為一塊重要基石。與這世界和解,與人為善,微笑著面對生活。重拾內心的柔和與想象力,激活質感的心靈,去擁抱這世界中美好的一切。要相信,大地包容著一切,不管好與壞。而人,也需要容納這世界的林林種種,這既是解脫自己,也是營造和諧,我們的靈魂也因此而博大、美麗。我們都在清醒地活著。
三
某個階段,我時常陷入回憶,無比懷念舊日時光。似乎過去有更多的美好與故事,更值得留戀,過去似乎比現在更好。人總愛在回憶中,習慣性地賦予過去某種不真實的幻覺和色彩。在記憶里,過去往往被高度美化,好的東西被永遠凝固在特定的時空里,成為永恒的標桿記憶,一點點細節都能讓人倍覺溫暖,而這不過是意識性的慣性錯覺。
曾經,時常懷念童年、少年時光的無憂無慮和快樂心情,覺得那時的日子美妙、神奇,什么都是好的。回憶起那些玩耍細節,一個小物件都能讓我興致盎然,玩味不已。還有一些影像,在一個夏夜,在一間狹小的平房里,風扇在無精打采地打轉著,我們幾個孩子擠在一起看電視、說故事,其樂融融,一個靜謐的夜晚就在這樣如水的時光里漫漶而過。回憶起來,有20世紀90年代貼在墻壁上風靡兩地的小虎隊的帥氣海報,有屋里略微昏暗的十幾瓦的白燈光、幾張矮矮的小板凳、一臺四方形的十幾寸的小電視機,有幾個孩子扎堆圍坐在一起的幼小稚氣身影,還有掛在墻上的老時鐘在無聊地晃動著鐘擺。這些零碎的記憶片段,時常在我腦海浮現,成為時光素描里充滿意境的藝術剪影,令人回味。
但這只是斷章取義式的片面描述。我們習慣性地把好的牢牢抓住,而對不好的一切產生天然的排斥與忘卻。過去未必就比現在好,假如真的可以永遠停留在過去,或許我們都會害怕逃離。那時簡陋、清苦的無奈環境,那時無處可去的無聊,那時狹窄無比的小世界,那時乏善可陳的經歷,怎能同現在優越的生活環境相比。手機、微信、汽車成為個人裝備,高科技的信息化時代,讓我們的生活便捷無比,也走得更遠,生活內容與方式也愈加多樣化與豐富。
我們感到現在不如從前,是因為我們心靈粗鄙,缺乏感性與色彩,缺少與這世界更多的心靈聯系,因而一切顯得平淡如常,沒有新奇和歡喜。而在我們簡樸的童年生活里,因為心境的天真無邪與未知,人還未被高度社會化,沒有什么欲望,因此對世界充滿熱情與新奇感,覺得什么都有意思,覺得童年都是快樂的。
現在,我們還缺少真正意義上的追求與價值觀。我們所有的付出與成功,似乎總要用物質的允諾和回報來呈現才算正確,我們都容易活得很累。我們得到物質,卻無法讓心靈滿足與快樂,這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我們很容易受外界大風潮影響,攀比之心,爭奪之心,自我之心,種種低級、負面的心靈能量通過我們的言行展現在現實生活里。而整個現實生活的樣子,就是我們心靈模樣的另一種影子投射,只是換了一種載體。通過觀察現實,就能看到種種人心。
沉湎過去絲毫沒有意義,更應該建構美好的現在。而美好從來不是從天而降,是靠自己一點一點去努力。現在不應不如從前,我們是走在越來越成熟與穩重的路上,就像不斷飛升的科學技術。現在不如從前,就是自我在一定程度上的放縱與逃避,是自身無法改變現狀的體現。
現在有什么呢?在謀得生存的安定后,更好地工作、休息、娛樂,更好地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好地與人相處,更好地共同營造一個足夠溫暖的世界。就像我此刻的生活。期待做好一名記者,編好一份報紙,從這如常的工作中,尋找更多工作上的自我成就感與自我價值認可,去發現平常工作中的閃光點,記錄凡人不尋常的生活姿態與想法,讓自己的工作時光毫不虛度,成為值得留在生命里的記憶,而不只是工作。去創造自己好的生活,在泛黃的燈光下看書,寫作,讓身心不斷趨向高雅、趣味,讓心靈充滿力量與陽光。去和他人融洽交流,期待能和更多的人擁有兄弟姐妹般的情誼,恰似家人,互幫互助,一起同甘共苦,共同走過一段段值得銘記終身的歲月。
而這樣的日常生活,卻足以讓我們微笑地面對這原地繞圈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