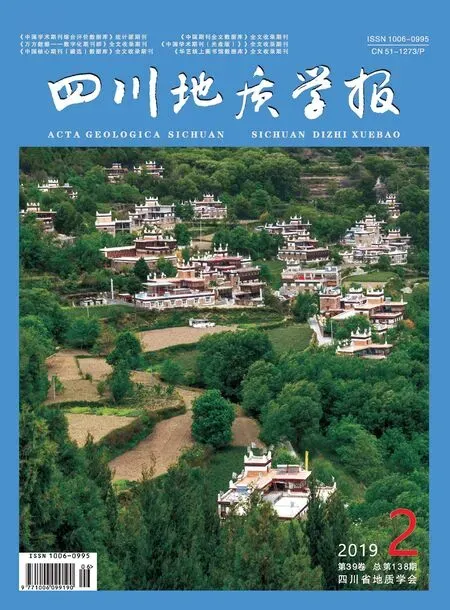四川恐龍化石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
彭光照,秦鋼,葉勇,朱桃秀,郝寶鞘,江山,唐薇,李雙江*
四川恐龍化石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
彭光照1,秦鋼2,葉勇1,朱桃秀2,郝寶鞘1,江山1,唐薇2,李雙江2*
(1. 自貢恐龍博物館,四川 自貢 643013;2. 四川省地質(zhì)學(xué)會,成都 610081)
四川是恐龍資源大省,自1915年首次科學(xué)發(fā)現(xiàn)恐龍化石以來,已有100多年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歷史,在恐龍動物群組合、系統(tǒng)演化、集群死亡原因與埋藏環(huán)境、生活習(xí)性與行為方式、骨組織學(xué)與古病理學(xué)等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研究成果。迄今為止,四川地區(qū)發(fā)現(xiàn)并鑒定出的恐龍骨骼化石有35屬48種,占中國恐龍骨骼化石種類的近1/5,恐龍足跡化石21屬20種,占中國恐龍足跡化石種類的1/3。其中,包括我國最早的恐龍足跡和我國最具典型意義的中侏羅世蜀龍動物群和晚侏羅世馬門溪龍動物群。我們期待未來四川恐龍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將在早期和晚期恐龍的發(fā)現(xiàn)、絕對年代測定、系統(tǒng)演化、區(qū)域性對比、微觀研究等方面有很大的突破。
恐龍;現(xiàn)狀;展望;四川
四川地域面積48×104km2,是中國第17大省,其中1/3為四川盆地內(nèi)的平原和丘陵地帶。盆地內(nèi)中生代陸相沉積地層發(fā)育,地層連續(xù),除恐龍蛋外,恐龍骨骼和恐龍足跡化石埋藏異常豐富,是中國恐龍研究最為理想的地區(qū)之一,具有得天獨(dú)厚的優(yōu)越條件,吸引了許多國內(nèi)外的古生物學(xué)家和地質(zhì)學(xué)家來四川盆地考察、發(fā)掘和合作研究,并取得舉世矚目的研究成果。
1 發(fā)現(xiàn)和研究歷史
據(jù)史料記載,1 600多年前,巴蜀先民就可能已接觸到了恐龍化石,只是那時人們根本不知道有恐龍的存在,而是把它們看成了神話傳說中的“龍”的骨頭。四川恐龍化石真正的科學(xué)發(fā)現(xiàn)和研究歷史只有100來年的時間。百年來,四川恐龍的科學(xué)發(fā)現(xiàn)和研究大致經(jīng)歷了四個時期:
1.1 揭幕時期(1915~1949年)
四川恐龍化石最早的科學(xué)發(fā)現(xiàn)可追溯到1915年。美國加州大學(xué)地質(zhì)學(xué)家勞德伯克(G. D. Louderback)受原中央地質(zhì)調(diào)查局之聘,在四川開展石油地質(zhì)調(diào)查工作時,于榮縣城東發(fā)現(xiàn)一段肉食龍的股骨、一枚牙齒以及一可能的坐骨碎塊和肋骨碎塊,化石被運(yùn)到美國加州大學(xué)博物館,存放了20年后,才經(jīng)美國加州大學(xué)古生物學(xué)家甘頗教授(C. L. Camp)研究,確認(rèn)為一種大型的巨齒龍類[1]。
1936年,楊鐘健教授邀約從歐洲和南非到中國來考察的甘頗教授,在四川大學(xué)周曉和教授陪同下來到榮縣,在榮縣城東西瓜山發(fā)現(xiàn)并采掘到一具較完整的大型蜥腳類恐龍化石,后經(jīng)楊鐘健(1939)研究命名為榮縣峨眉龍()[2]。這是四川盆地出土的第一條完整的恐龍化石,也是四川盆地最早命名的恐龍。至此,四川盆地恐龍研究的帷幕徐徐拉開。
在隨后的十多年里,不斷有零星恐龍化石發(fā)現(xiàn)。1939~1940年間,地質(zhì)學(xué)家岳希新教授在威遠(yuǎn)地區(qū)開展地質(zhì)調(diào)查過程中,在長嶺和鋪?zhàn)訛持g的新店子一帶采集到一批恐龍化石,后經(jīng)楊鐘健(1944)整理研究,將其中一類命名為岳氏三巴龍()。
1941年,楊鐘健、卞美年、米泰恒等在考察過程中,于四川廣元地區(qū)采集到一批脊椎動物化石。楊鐘健(1942)研究鑒定出恐龍4屬4種:甘氏四川龍()、角形劍閣龍()、破碎中國虛骨龍()以及似榮縣峨眉龍(cf.)。
1.2 奠基時期(1950~1970年)
新中國成立后,全國各地掀起建設(shè)的高潮,四川也不例外。這一時期恐龍化石的發(fā)現(xiàn)主要來自基本建設(shè)施工和基礎(chǔ)地質(zhì)調(diào)查,研究工作也主要由楊鐘健教授進(jìn)行,為四川恐龍化石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1952年,在宜賓縣城南馬鳴溪渡口修建公路過程中,于上侏羅統(tǒng)上沙溪廟組地層中發(fā)現(xiàn)了一具大型蜥腳類恐龍骨架,經(jīng)楊鐘健(1954)研究,命名為建設(shè)馬門溪龍()[3]。這就是馬門溪龍屬的模式種。
1957年,四川石油勘探局一野外隊(duì)在渠縣水口鎮(zhèn)(原平安鄉(xiāng))坪花村太平砦上侏羅統(tǒng)上沙溪廟組地層中發(fā)現(xiàn)一較完整的劍龍骨架,楊鐘健(1959)研究命名為關(guān)氏嘉陵龍()。這是我國第一條比較完整的劍龍化石。1978年,重慶市博物館和渠縣文化館又在該地采得一些化石材料,董枝明等(1983)作了補(bǔ)充記述。
1960年,楊鐘健描述了地質(zhì)調(diào)查隊(duì)送交的在宜賓縣觀音鎮(zhèn)改進(jìn)村上白堊統(tǒng)打兒凼組地層中發(fā)現(xiàn)的3個恐龍足跡化石,命名為宜賓揚(yáng)子足跡(),并發(fā)現(xiàn)在足印上還保存有清晰的皮膚印痕,這是我國發(fā)現(xiàn)的第一塊恐龍的皮膚印痕。
1967年至1971年間,四川省地質(zhì)局第二區(qū)域地質(zhì)調(diào)查隊(duì)在峨眉山市川主鄉(xiāng)幸福崖下白堊統(tǒng)夾關(guān)組地層中發(fā)現(xiàn)了幾個恐龍足跡,并記錄在冊。1983年,重慶自然博物館和北京自然博物館又在該足跡點(diǎn)的落石上發(fā)現(xiàn)30多個足印,后由甄朔南等(1994)研究,命名了5個足跡種,其中包括4個恐龍足跡種和1個鳥類足跡種:四川快盜龍足跡()、川主小龍足跡()、峨眉翹腳龍足跡()、幸福禽龍足跡()、[4]。2010年,西南石油大學(xué)陸廷清等在川主鄉(xiāng)的夾關(guān)組一垂直巖面上發(fā)現(xiàn)了一批恐龍足跡,并做了簡要的描述。2015年,邢立達(dá)、陸廷清、彭光照、葉勇等在川主這個地點(diǎn)又發(fā)現(xiàn)了一些足跡,包括甲龍類足跡。
1.3 發(fā)展時期(20世紀(jì)70年代~80年代)
這一時期以自貢伍家壩和大山鋪代表的重要化石點(diǎn)的發(fā)現(xiàn)和發(fā)掘,將四川恐龍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其中特別是大山鋪蜀龍動物群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及我國第一座專業(yè)性恐龍博物館—自貢恐龍博物館的建立成為了我國恐龍化石發(fā)現(xiàn)、發(fā)掘和研究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四川恐龍的研究主要由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董枝明和唐治路、重慶自然博物館周世武和張奕宏、成都理工大學(xué)(成都地質(zhì)學(xué)院)何信祿和蔡開基等第二代恐龍學(xué)家所開展。
1970~1971年間,成都地質(zhì)學(xué)院何信祿、姚代宗、林文球等在達(dá)州開江縣金雞鄉(xiāng)老山溝中侏羅統(tǒng)下沙溪廟組地層中采集到大量恐龍化石,何信祿(1984)記述了獸腳類兩個屬種和1個基干鳥臀類未定種:原始川東虛骨龍()、林氏開江龍()和鹽都龍屬未定種(sp.)[5]。該地點(diǎn)出土的蜥腳類材料由匡學(xué)文(1996)研究,并取名為“開江巴蜀龍()”,然至今未正式發(fā)表。
1972年,自貢市天然氣化工研究所在自貢鴻鶴壩金子凼中侏羅統(tǒng)下沙溪廟組地層中挖出一具小型的基干鳥臀類恐龍化石,何信祿(1979)研究命名為鴻鶴鹽都龍()。
同年,地質(zhì)部第七普查大隊(duì)的黃建國和展俊山在自貢大山鋪萬年燈中侏羅統(tǒng)下沙溪廟組地層中發(fā)現(xiàn)恐龍化石,拉開了大山鋪這個舉世聞名的恐龍化石群研究的序幕。1977年,董枝明率領(lǐng)的四川省“保護(hù)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化石訓(xùn)練班”在大山鋪采得一具較完整的蜥腳類恐龍骨架,這就是李氏蜀龍()的正型標(biāo)本。1979~1984年間,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重慶自然博物館、成都地質(zhì)學(xué)院、自貢市鹽業(yè)歷史博物館和自貢恐龍博物館的科研人員先后在大山鋪開展了長期的化石清理和發(fā)掘工作,獲得上百具恐龍及其它脊椎動物化石骨架,鑒定命名了蜥腳類、獸腳類、基干鳥臀類、劍龍類等12屬13種恐龍,出版了5部研究專著,2本研究專輯,40余篇研究論文,將四川盆地恐龍研究推向峰巔,成為中國恐龍研究的里程碑。
1973年,成都地質(zhì)學(xué)院博物館在資中縣羅泉鎮(zhèn)小河村下沙溪廟組下部紫紅色泥巖中采掘到一具不完整的蜥腳類恐龍骨架。1981年,李奎又在該化石點(diǎn)附近采到一些零星的化石標(biāo)本。這批標(biāo)本由何信祿、李奎、蔡開基(1988)研究,定名為羅泉峨眉龍()。
1974年,重慶市博物館和自貢市鹽業(yè)歷史博物館在自貢市伍家壩上侏羅統(tǒng)上沙溪廟組地層中發(fā)現(xiàn)了一個埋藏豐富的恐龍化石群,采得化石100余箱,各類恐龍骨架10多具。董枝明等(1983)系統(tǒng)整理和研究,共鑒定出恐龍4屬4種:甘氏四川龍()、釜溪峨眉龍(=釜溪自貢龍)、榮縣峨眉龍()和多棘沱江龍()。
1978年,董枝明和唐治路等在威遠(yuǎn)黃石板、護(hù)林、葫蘆口及資中鐵佛、羅泉井一帶珍珠沖組、自流井組地層中獲得一批零星的化石材料,經(jīng)董枝明等(1983)鑒定,有原蜥腳類和原始蜥腳類,并將資中羅泉井的原始蜥腳類材料命名為船城資中龍()。
1979年春,郭運(yùn)林等在自貢市水泥廠采石場下侏羅統(tǒng)自流井組大安寨段灰?guī)r中采集到一些破碎化石材料,董枝明(1984)鑒定為似巨型祿豐龍(cf.)。
同年,四川省煤田地質(zhì)局137地質(zhì)隊(duì)在宣漢縣東鄉(xiāng)鎮(zhèn)項(xiàng)山社區(qū)中侏羅統(tǒng)下沙溪廟組地層中發(fā)現(xiàn)一不完整的肉食性恐龍個體,后經(jīng)董枝明(1984)研究,命名為七里峽宣漢龍()。
1979~1980年間,成都地質(zhì)學(xué)院在廣元市河西區(qū)上侏羅統(tǒng)上沙溪廟組地層中采集了大量恐龍化石,其中獸腳類材料經(jīng)何信祿[5]鑒定,歸為甘氏四川龍,而蜥腳類材料由李奎等(1998)研究,命名為廣元馬門溪龍()。
1981年,地質(zhì)工作者鄧康齡在彭州磁峰鎮(zhèn)蟠龍村的上三疊統(tǒng)須家河組地層中發(fā)現(xiàn)2個足印化石,楊興隆、楊代環(huán)(1987)命名為磁峰彭縣足跡()。邢立達(dá)等(2013)還在正模標(biāo)本上發(fā)現(xiàn)了2塊皮膚印痕和2個似哺乳爬行動物的足印。
同年,重慶自然博物館在資中縣興隆街鎮(zhèn)五馬村曬壩和雞爪石新田溝組底部地層中發(fā)現(xiàn)200多個恐龍足跡化石,同時還在資中縣金李井鎮(zhèn)碾盤山村曾家院壩下沙溪廟組地層中發(fā)現(xiàn)幾條獸腳類恐龍行跡。楊興隆和楊代環(huán)(1987)對這批足跡化石進(jìn)行了研究,命名了7個屬種:五馬資中足跡()、小重慶足跡()、水南沱江足跡()、何氏重龍足跡()、雞爪石巨大足跡()、五皇船城足跡()、碾盤山金李井足跡(Jinlijingpus nianpanshanensis = Eubrontes nianpanshanensis)[6]。
1982年,中英聯(lián)合考察隊(duì)在旺蒼縣西河鄉(xiāng)(現(xiàn)嘉川鎮(zhèn)槐樹村)上侏羅統(tǒng)上沙溪廟組地層中獲得一些劍龍類和蜥腳類化石,但由于標(biāo)本保存較差,未見正式記述。
同年,北京自然博物館在岳池縣黃龍鄉(xiāng)袁家?guī)r上侏羅統(tǒng)蓬萊鎮(zhèn)組地層中獲得38個鳥臀類恐龍足印。甄朔南(1983)研究命名為岳池嘉陵足跡()。后來,重慶自然博物館又在該地點(diǎn)采集到30多個同樣的足印,并在黃龍鄉(xiāng)的深溝發(fā)現(xiàn)5個具有蹼痕的足印,楊興隆和楊代環(huán)[6]在補(bǔ)充描述岳池嘉陵足跡時,將深溝足印命名為深溝黃龍足跡()。
1983年,董枝明、周世武和張奕宏出版了《四川盆地侏羅紀(jì)恐龍化石》一書,第一次對四川盆地之前所發(fā)現(xiàn)的恐龍化石及其研究情況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總結(jié)[7]。
同年底,重慶市博物館在營山縣濟(jì)川鄉(xiāng)上侏羅統(tǒng)上沙溪廟組地層中采掘到一具不完整的劍龍骨架,朱松林(1994)研究定名為濟(jì)川營山龍()。
1985年4~5月,自貢恐龍博物館先后在沿灘區(qū)仲權(quán)鄉(xiāng)銀河村和大安區(qū)和平鄉(xiāng)田灣村上侏羅統(tǒng)上沙溪廟組地層中采掘到一具完整的劍龍和一具完整的肉食龍。歐陽輝(1992)將劍龍取名為四川巨棘龍(),但沒有對標(biāo)本進(jìn)行描述,最近郝寶鞘等(2018)對該標(biāo)本進(jìn)行了較詳細(xì)的描述,并分析了它的系統(tǒng)發(fā)育關(guān)系。肉食龍則由高玉輝(1992)研究命名為和平永川龍(),并出版了《四川自貢一完整的肉食龍——和平永川龍》研究專著。
同年8月,自貢恐龍博物館在威遠(yuǎn)縣連界鎮(zhèn)榮勝村朱家廟下侏羅統(tǒng)珍珠沖組地層中采集到6個獸腳類恐龍足跡,高玉輝(2007)命名為自貢威遠(yuǎn)足跡(),但邢立達(dá)等(2014)將威遠(yuǎn)足跡并入實(shí)雷龍足跡中。
1987年,重慶自然博物館在井研縣梅旺鄉(xiāng)和三江鎮(zhèn)上侏羅統(tǒng)上沙溪廟組地層中采掘到一些大型蜥腳類恐龍骨骼,經(jīng)張奕宏等(1998)研究,定名為井研馬門溪龍(),并將以前在榮縣度佳鄉(xiāng)巖灣村發(fā)現(xiàn)的材料也歸在該種中。
同年,成都地質(zhì)學(xué)院博物館和安岳縣文管所在安岳縣龍橋鄉(xiāng)水月村上侏羅統(tǒng)遂寧組頂部地層中采掘到比較完整的巨型蜥腳類,何信祿等(1996)取名為安岳馬門溪龍()。
1.4 繁榮時期(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
隨著自貢伍家壩和大山鋪恐龍化石群的發(fā)現(xiàn),恐龍博物館的建立和年輕一代的恐龍研究力量的成長,四川恐龍發(fā)現(xiàn)的產(chǎn)地和層位飛速擴(kuò)展,自貢恐龍博物館、成都理工大學(xué)博物館成為四川恐龍研究的主力軍,四川的恐龍研究也走向一個多元化的時代,恐龍化石的發(fā)現(xiàn)多點(diǎn)開花,發(fā)掘、修復(fù)和保護(hù)技術(shù)日趨成熟,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加多樣化,橫向的合作研究廣泛開展。
1989年初,自貢恐龍博物館在大安區(qū)新民鄉(xiāng)九井壩上沙溪廟組地層中采掘到一具完整的蜥腳類恐龍,皮孝忠等(1996)命名為楊氏馬門溪龍(),歐陽輝、葉勇(2002)出版了《第一具保存有完整頭骨的馬門溪龍——楊氏馬門溪龍》研究專著。
同年,成都理工大學(xué)博物館在四川天全縣城以北青衣江右岸的上三疊統(tǒng)須家河組地層中發(fā)現(xiàn)并采集到一些恐龍足跡化石,但一直沒有進(jìn)行鑒定和研究。2005年,四川省地調(diào)院又在該足跡化石點(diǎn)附近發(fā)現(xiàn)了2個足印化石,經(jīng)王全偉等(2005)初步研究,認(rèn)為可能屬于虛骨龍類足跡。
1991年,昭覺縣三岔河鄉(xiāng)三比羅嘎銅礦在采礦過程中,暴露出了約1 500m2的飛天山組含1 000多個恐龍足跡的層面。2006年,成都理工大學(xué)博物館李奎和劉建對這些足跡進(jìn)行了調(diào)查。遺憾的是,2006~2009年間,由于持續(xù)的采礦活動導(dǎo)致超過95%的足跡不復(fù)存在。2012~2013年間,邢立達(dá)等多次到該足跡點(diǎn)考察研究了巖層上殘留下來的100多個足跡,同時還在礦坑的西南側(cè)發(fā)現(xiàn)了若干恐龍足跡,包括中國最早鑒定的獸腳類游泳行跡和10余條獸腳類、蜥腳類、鳥腳類的行跡[8]。
1995年初,自貢恐龍博物館在自貢市榮縣復(fù)興鄉(xiāng)發(fā)現(xiàn)了一個埋藏量非常豐富的恐龍化石群,并于1995年和1999年兩次對該點(diǎn)進(jìn)行試探性發(fā)掘。但由于該化石點(diǎn)位置較偏遠(yuǎn)、交通不便,發(fā)掘和保護(hù)工作難度較大,沒有進(jìn)行徹底發(fā)掘和系統(tǒng)研究。

四川重要恐龍骨骼和足跡化石分布圖
同年8月,成都理工大學(xué)博物館在簡陽縣三星鎮(zhèn)蟠龍村蓬萊鎮(zhèn)組頂部獲得2個不完整的蜥腳類個體材料,王正新等(2003)鑒定為馬門溪龍未定種(sp.)。
同年底,自貢恐龍博物館在自貢市匯東新區(qū)園丁苑建設(shè)工地采掘到一具巨型的蜥腳類恐龍骨架,葉勇等(2001)研究鑒定為合川馬門溪龍()。
1997年,202地質(zhì)隊(duì)周鳳云等在珙縣石碑鄉(xiāng)紅沙村自流井組東岳廟段地層中發(fā)現(xiàn)一恐龍化石群。何信祿等(1998)、駱耀南等(1999)依據(jù)3個個體的蜥腳類材料,命名了石碑珙縣龍()。此后,重慶自然博物館在該化石點(diǎn)附近采掘到一具比較完整的原始蜥腳類恐龍骨架,歐陽輝(2005)取名為“周氏宜賓龍()”,但至今未正式發(fā)表。
1998年,浙江自然博物館在井研縣研經(jīng)鎮(zhèn)同前村上侏羅統(tǒng)上沙溪廟組中采得一具非常完整的蜥腳類恐龍骨架,唐烽、金幸生等(2001)研究命名為毛氏峨眉龍()。
2001年,自貢恐龍博物館與成都理工大學(xué)地球科學(xué)學(xué)院采用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在自貢大山鋪恐龍化石群遺址東側(cè)發(fā)現(xiàn)一具大型蜥腳類恐龍化石,江山等(2011)命名為焦氏峨眉龍()。
2002年底,自貢恐龍博物館在沿灘區(qū)永安鄉(xiāng)上沙溪廟組地層采掘到一具較完整的蜥腳類幼年個體化石,葉勇等(2005)研究命名為張氏大安龍()。
2005年,彭光照、葉勇、高玉輝等對自貢地區(qū)的恐龍及其他脊椎動物化石及研究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的歸納和總結(jié),出版了《自貢地區(qū)侏羅紀(jì)恐龍動物群》研究專著[9]。
2006年,樂山市國土資源局和自貢恐龍博物館在犍為縣孝姑鎮(zhèn)同益村上侏羅統(tǒng)上沙溪廟組地層中獲得一具較完整的肉食龍類骨架,李飛、彭光照、葉勇等(2009)研究命名為犍為樂山龍()。
2007年,成都理工大學(xué)博物館在會里縣通安鎮(zhèn)通保村下侏羅統(tǒng)益門組采掘到一具蜥腳類恐龍,李奎等(2010)研究定名為何氏通安龍()。
2008年,四川省地調(diào)院王全偉、梁斌、闞澤忠等對四川幾個重要的恐龍動物群進(jìn)行了生態(tài)環(huán)境和恐龍死亡與埋藏原因的調(diào)查和分析,出版了《四川盆地中生代恐龍動物群古環(huán)境重建》研究專著[10]。
2009年,自貢恐龍博物館在富順縣童寺鎮(zhèn)龍貫山上三疊統(tǒng)須家河組地層中發(fā)現(xiàn)19個足跡化石。邢立達(dá)、彭光照、葉勇等(2014)研究鑒定為始龍足跡(),造跡者可能是一種早期的兩足行走的初龍類。
2010年,古藺縣椒園鄉(xiāng)鐘山村下侏羅統(tǒng)自流井組地層中暴露出許多足跡化石,彭光照、葉勇和邢立達(dá)等先后赴現(xiàn)場調(diào)查,確定為蜥腳類恐龍足跡化石。邢立達(dá)等(2015)將其命名為蜀南劉建足跡()。
2011-2015年間,敘永縣委宣傳部新聞中心記者楊濤在大石鄉(xiāng)新陽村和龍井村發(fā)現(xiàn)三處下白堊統(tǒng)夾關(guān)組恐龍足跡點(diǎn),經(jīng)彭光照、葉勇、邢立達(dá)等多次現(xiàn)場調(diào)查,確定為早白堊世的獸腳類、蜥腳類和鳥腳類恐龍足跡。
表1 四川恐龍骨骼化石屬種統(tǒng)計(jì)


2014年,四川區(qū)調(diào)隊(duì)一野外隊(duì)在昭覺縣央摩租鄉(xiāng)和解放鄉(xiāng)爾結(jié)得村、喜德縣巴久鄉(xiāng)、樂武鄉(xiāng)母腳吾、博洛鄉(xiāng)吉爾博石、洛哈鎮(zhèn)足谷村以及洛哈鎮(zhèn)依子村等地發(fā)現(xiàn)了多處白堊系飛天山組和小壩組恐龍足跡點(diǎn),經(jīng)邢立達(dá)等陸續(xù)調(diào)查研究,確定主要類型有蜥腳類、獸腳類、鳥腳類。
2015年,中科院南京地質(zhì)古生物研究所王永棟等在宣漢七里鎮(zhèn)西公路邊中侏羅統(tǒng)新田溝組的落石上發(fā)現(xiàn)2個腳印,經(jīng)邢立達(dá)等(2017)研究,確認(rèn)為獸腳類的異樣龍足跡(isp.)。
2016年11月,邢立達(dá)、彭光照、葉勇等先后在重慶綦江郭扶鎮(zhèn)永勝村和四川馬邊縣荍壩鄉(xiāng)會步村下白堊統(tǒng)夾關(guān)組地層中發(fā)現(xiàn)兩處恐龍足跡化石點(diǎn),包括鳥腳類、蜥腳類和獸腳類足跡。
2017年8月,自貢恐龍博物館在富順縣永年鎮(zhèn)五里村一采石場自流井組馬鞍山段地層中獲得許多小型的獸腳類恐龍足跡。
2 研究現(xiàn)狀

表2 四川恐龍足跡化石屬種統(tǒng)計(jì)
四川恐龍化石資源非常豐富,遍布四川18個市州(圖1),吸引了中國科學(xué)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國地質(zhì)大學(xué)(北京)、四川省地礦局、成都理工大學(xué)博物館、重慶自然博物館、自貢恐龍博物館、北京自然博物館、浙江自然博物館、香港大學(xué)、美國科羅拉多大學(xué)、日本福井恐龍博物館、英國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德國弗倫斯堡大學(xué)等國內(nèi)、外眾多的科研院所、博物館的廣大專家學(xué)者參與調(diào)查和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包括上百篇的科研論文和十多本科研專著,鑒定和命名恐龍35屬47種(表1),恐龍足跡14屬19種(表2)及若干未定種,并且在生物多樣性、恐龍演化關(guān)系、地質(zhì)年代、古地理環(huán)境、死亡原因與埋藏特征、恐龍生活與行為方式以及骨組織學(xué)、古病理學(xué)等方面都有涉及。這些成果為四川恐龍化石的保護(hù)和開發(fā)利用的研究提供了堅(jiān)實(shí)的科學(xué)依據(jù)。
2.1 恐龍動物群及其組合
早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初,董枝明(1980)在總結(jié)中國的恐龍動物組合情況時,提出五個恐龍動物群[11],其中四川地區(qū)就有兩個代表性恐龍動物群:早-中侏羅世蜀龍動物群和晚侏羅世馬門溪龍動物群。這兩個動物群的劃分主要以蜥臀類恐龍的更替和演變而確定的。蜀龍動物群涵蓋了早侏羅世晚期自流井組馬鞍山段-中侏羅世下沙溪廟組所發(fā)現(xiàn)的脊椎動物類群,屬于原蜥腳類被原始蜥腳類恐龍取代,并向進(jìn)步蜥腳類恐龍演化的過渡時期。馬門溪龍動物群則主要包括晚侏羅世上沙溪廟組的脊椎動物組合,代表巨型的蜥腳類恐龍發(fā)展的鼎盛時期。
1983年,董枝明等在總結(jié)四川盆地侏羅紀(jì)恐龍化石時認(rèn)為,早侏羅世晚期自流井組的原始蜥腳類較中侏羅世下沙溪廟組中的蜀龍、酋龍、峨眉龍等要原始得多,加上1984年董枝明又研究了自貢涼水井自流井組上部大安寨段灰?guī)r中發(fā)現(xiàn)的原蜥腳類材料,認(rèn)為屬于祿豐蜥龍動物群的分子,因而將四川盆地早侏羅世珍珠沖組和自流井組的恐龍組合均劃歸祿豐蜥龍動物群。
然而,隨著新材料的不斷發(fā)現(xiàn)和研究,李奎等(1997)提出在祿豐蜥龍動物群和蜀龍動物群之間存在一個過渡性質(zhì)的動物群,取名為資中龍動物群[12],因而四川侏羅紀(jì)恐龍組合包括四個動物群:早侏羅世早期祿豐龍動物群、早侏羅世晚期資中龍動物群、中侏羅世蜀龍-峨眉龍動物群和晚侏羅世馬門溪龍動物群。祿豐龍動物群分布于珍珠沖組中,以原蜥腳類為主,沒有蜥腳類的成分;資中龍動物群分布于自流井組中,以原蜥腳類消亡成為孑遺分子,出現(xiàn)了具有原始性質(zhì)的蜥腳類恐龍妖龍類為特征;蜀龍-峨眉龍動物群分布于新田溝組和下沙溪廟組中,恐龍類群豐富,蜥腳類、獸腳類、基干鳥臀類和劍龍類屬種都很豐富,蜥腳類除原始的蜥腳類外,較進(jìn)步的大型蜥腳類恐龍已成為主要分子;馬門溪龍動物群分布在上沙溪廟組、遂寧組和蓬萊鎮(zhèn)組中,原始的蜥腳類恐龍已不存在,蜥腳類屬種單調(diào),以巨型的進(jìn)步馬門溪龍類為主要成員。
目前,蜀龍動物群(或蜀龍-峨眉龍動物群)和馬門溪龍動物群的組成分子已十分清楚,研究也比較透徹,而且分別都有比較豐富、保存完整的化石群為代表,如中侏羅世的自貢大山鋪恐龍化石群、榮縣復(fù)興青龍山恐龍化石群,晚侏羅世的自貢伍家壩恐龍化石群、安岳龍橋馬蹄寺恐龍化石群、廣元河西恐龍化石群、廣元旺蒼嘉川恐龍化石群等。至于資中龍動物群,由于化石材料比較少而且零星,組合面貌尚不十分清楚,代表性的屬種資中龍、珙縣龍等保存材料有限,研究程度不高,開展動物群對比研究比較困難,尚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2.2 恐龍各類群的系統(tǒng)發(fā)育關(guān)系
四川恐龍研究,長期以來多集中在化石描述、傳統(tǒng)分類鑒定和特征對比方面,隨著分支系統(tǒng)學(xué)(或系統(tǒng)發(fā)育系統(tǒng)學(xué))在古生物學(xué)領(lǐng)域的應(yīng)用,年輕一代的學(xué)者們也開始嘗試應(yīng)用新的分析方法借助計(jì)算機(jī)系統(tǒng)來研究分析各恐龍類別的系統(tǒng)位置和相互間的親緣關(guān)系。2011年,關(guān)谷透(Toru Sekiya)以阿納川街龍()為基礎(chǔ),采用PAUP 4.0系統(tǒng)軟件,附帶分析了四川幾種蜥腳類恐龍的系統(tǒng)位置。2013年,楊春燕以何氏通安龍為例,嘗試使用定量分析法對四川幾種長頸椎型蜥腳類恐龍的演化關(guān)系進(jìn)行分析研究。2018年,郝寶鞘等對四川巨棘龍進(jìn)行了再研究,應(yīng)用PAUP 4.0系統(tǒng)軟件作了分析,顯示巨棘龍并非之前Maidment等(2008)和Raven等(2017)所分析的比華陽龍還原始的類群,而是介于華陽龍和沱江龍之間的一個類群。
2.3 恐龍生活的地質(zhì)時代
四川盆地是一個沉積盆地,由于盆地內(nèi)部缺乏火成巖,找不到測年所需的鋯石,給絕對地質(zhì)年代的測定帶來巨大困難,含恐龍化石的沉積地層的地質(zhì)年代一直是困擾研究者的問題,盡管通過古生物化石的進(jìn)化水平分析研究和古生物組合面貌的對比,盆地內(nèi)中生代這套陸相沉積地層的相對地質(zhì)年代已大致確定,但由于沒有確切的絕對年代數(shù)據(jù)的支撐,爭論也就在所難免,地層年代界線的劃定意見不很統(tǒng)一,比如自流井組是早侏羅世晚期還是早侏羅世晚期-中侏羅世早期的沉積地層,上沙溪廟組屬中侏羅世還是晚侏羅世,甚或跨越中、晚侏羅世。中國地質(zhì)科學(xué)院的劉剛等(2017)嘗試性利用沉積地層中碎屑鋯石對川東北大巴山地區(qū)的遂寧組進(jìn)行年代測定,測定結(jié)果顯示遂寧組最年輕的U-Pb年齡為120Ma,進(jìn)入早白堊世晚期,相當(dāng)于阿普特期。這與古生物化石確定的相對年代相差甚大。最近,香港大學(xué)王俊和自貢恐龍博物館葉勇等(2018)也利用碎屑鋯石來測定自貢大山鋪下沙溪廟組蜀龍-峨眉龍動物群的絕對年代,結(jié)果是最年輕的U-Pb年齡為159Ma,進(jìn)入晚侏羅世牛津期,比原先認(rèn)為的中侏羅世巴柔期或巴通期要晚得多。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要進(jìn)一步論證和研究。
2.4 恐龍集群死亡原因和埋藏環(huán)境
四川地區(qū)的恐龍主要生活在侏羅紀(jì)中、晚期,屬于恐龍演化的繁盛期,還遠(yuǎn)未到6 600萬年前白堊紀(jì)末期非恐龍類衰亡絕滅的時期,所以四川的恐龍研究對解決恐龍絕滅的問題意義不大。然而,諸多的恐龍化石埋藏群對于研究恐龍生活方式、古環(huán)境對于恐龍興盛的影響、集群死亡原因和化石埋藏的古地理環(huán)境意義重大。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夏文杰等(1984、1988)專題研究了自貢大山鋪恐龍化石群的埋藏環(huán)境、和巖相古地理特征,并發(fā)現(xiàn)恐龍骨骼和植物化石中微量元素特別是砷(As)的含量異常超高,認(rèn)為這里的古環(huán)境為低能湖濱淺灘環(huán)境,恐龍群居生活在這一地帶,可能因砷等微量元素中毒而大量死亡,迅速原地埋藏在這低洼的湖濱地帶形成化石群。張景華等(1993)也分析發(fā)現(xiàn)自貢大山鋪恐龍骨骼化石中放射性元素鈾(U)的超高異常,但這是否意味著當(dāng)時這里存在一個嚴(yán)重的放射性污染事件發(fā)生,從而導(dǎo)致恐龍成批死亡,抑或鈾的超高異常是U元素長期在恐龍遺體內(nèi)積累的,他們沒有給出明確的結(jié)論。李奎等(1997、1998)根據(jù)恐龍骨骼化石和圍巖中微量元素的分析,探討了廣元河西恐龍化石群集群死亡的原因,認(rèn)為砷和鋇(Ba)的超高異常和鋅(Zn)的低異常引發(fā)恐龍中毒事件導(dǎo)致河西恐龍集群死亡。李奎等(1999)擴(kuò)大到自貢大山鋪的分析也顯示出同樣的結(jié)果。
2.5 恐龍的生活習(xí)性和行為方式
恐龍研究除了基本的屬種鑒定、分類、個體發(fā)育和系統(tǒng)發(fā)育分析外,還有可能涉及恐龍的行為和生活習(xí)性,如食性、行走方式、行走速度、如何防身自衛(wèi)、體溫調(diào)節(jié)等。基于自貢大山鋪發(fā)現(xiàn)的蜥腳類骨質(zhì)尾錘化石,董枝明等(1989)提出這種特殊的尾部構(gòu)造不僅能有效地平衡身體,而且是很好的防御武器,同時還印證了蜥腳類恐龍是營陸地生活的動物。
邢立達(dá)等(2009)采用有限元分析(FEA, Finite Element Analysis)研究了自貢匯東發(fā)現(xiàn)的合川馬門溪龍骨質(zhì)尾錘,得出尾錘的側(cè)向擺動比上下擺動更加有效,最佳的碰撞點(diǎn)在愈合的尾錘第二個脊椎的神經(jīng)棘上,最大載荷可達(dá)450牛頓,但合川馬門溪龍的尾錘可能不是主要用作防衛(wèi)武器,而是一個改善神經(jīng)傳導(dǎo)速度,提高環(huán)境感知能力的感覺器官[13]。
四川發(fā)現(xiàn)豐富的恐龍足跡為研究恐龍的居群方式、行走方式、行走速度提供了大量證據(jù)。邢立達(dá)等(2013)從昭覺三岔河鄉(xiāng)三比羅嘎足跡點(diǎn)發(fā)現(xiàn)的中國首例獸腳類恐龍游泳足跡為恐龍會游泳提供了實(shí)證。
2.6 恐龍骨組織學(xué)與古病理學(xué)
恐龍的微觀研究也是恐龍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葉勇等(2007)采用切片法研究了自貢大山鋪蜀龍和峨眉龍的長骨骨組織結(jié)構(gòu),發(fā)現(xiàn)具有快速的后生生長速率,它們的生長模式是非限定生長,但生長輪結(jié)構(gòu)不明顯[14]。邢立達(dá)等(2009)分析了自貢發(fā)現(xiàn)的和平永川龍肩胛骨骨折的病理現(xiàn)象,并認(rèn)為屬于外力的直接暴力所致骨折。最近,郝寶鞘等利用能譜CT對自貢發(fā)現(xiàn)的四川巨棘龍股骨的病變進(jìn)行斷層掃描和能譜曲線分析,首次發(fā)現(xiàn)恐龍骨腫瘤的病變[71]。
3 研究展望
3.1 早期和晚期恐龍化石的發(fā)現(xiàn)
四川地區(qū)恐龍化石資源,但恐龍骨骼化石主要集中產(chǎn)自在侏羅紀(jì)中-晚期地層中,恐龍足跡化石主要見于侏羅紀(jì)早期-白堊紀(jì)早期地層中,盡管晚三疊世和早侏羅世早期的恐龍足跡有所發(fā)現(xiàn),但恐龍骨骼化石卻仍是個空白。雖然早侏羅世晚期的自流井組有一些化石材料發(fā)現(xiàn),但仍顯稀少,動物群組合面貌不很清楚。上三疊統(tǒng)須家河組和下侏羅統(tǒng)珍珠沖組、自流井組在四川地區(qū)比較發(fā)育,出露也很好,發(fā)現(xiàn)更多更好的恐龍化石的希望是很大的,特別如若能在上三疊統(tǒng)須家河組中發(fā)現(xiàn)恐龍骨骼化石,那將對中國恐龍的研究都將是一個重大貢獻(xiàn)。另外,白堊紀(jì)早期的恐龍足跡發(fā)現(xiàn)很多,但恐龍骨骼化石至今未有正式報(bào)道,還有白堊紀(jì)晚期的灌口組和相當(dāng)?shù)男谓M、高坎壩組地層雖然分布不廣,但還是有所出露,除在喜德發(fā)現(xiàn)一些恐龍足跡外,未見恐龍骨骼化石。所以,未來向早期和晚期拓展是四川恐龍化石發(fā)現(xiàn)的重點(diǎn)。
3.2 絕對年代的測定
四川地區(qū)目前的地質(zhì)年齡主要依靠生物地層的結(jié)論,這僅僅是相對的,而且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爭議隨之而伴生。前述雖然有人開始嘗試采用沉積物中的鋯石來測定地層的絕對年齡,但其可靠程度有待證實(shí)。未來工作應(yīng)將生物地層學(xué)與同位素年代學(xué)、磁性地層學(xué)、旋回地層學(xué)、化學(xué)地層學(xué)、定量地層學(xué)等結(jié)合起來,使地質(zhì)年齡的精度更高、更準(zhǔn)確,有利于恐龍系統(tǒng)演化的研究。
3.3 系統(tǒng)演化的研究
傳統(tǒng)的恐龍研究主要依據(jù)化石材料進(jìn)行分類、鑒定和描述,當(dāng)然這也是恐龍研究的基礎(chǔ)。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的分類有很多人為因素在里面,得出的結(jié)論問題較大,爭議不少。近年來普遍將分支系統(tǒng)(也稱系統(tǒng)發(fā)育系統(tǒng))分析應(yīng)用于恐龍研究中,并借助于計(jì)算機(jī)來分析,減少人為的干擾,得出的結(jié)論更接近于自然。在這方面,四川有非常好的化石材料,可以做更多的系統(tǒng)演化方面的研究工作。
3.4 區(qū)域性對比研究
世界上由于海侵的關(guān)系,早侏羅世晚期-中侏羅世的恐龍動物群發(fā)現(xiàn)不多,仍然是恐龍系統(tǒng)演化和對比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隨著工作的深入,在英國、法國、德國、美國、阿根廷、摩洛哥、馬達(dá)加斯加、澳大利亞等地陸續(xù)有這段時期的恐龍發(fā)現(xiàn),在我國的云南祿豐、元謀、新疆五彩灣、寧夏靈武、內(nèi)蒙寧城、重慶云陽等也不斷有這段時期的恐龍發(fā)現(xiàn)。但在跨區(qū)域?qū)Ρ妊芯糠矫孢€存在不足,未來工作將在系統(tǒng)分析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開展四川地區(qū)之外同時代恐龍的研究工作,并在更大的區(qū)域和時空范圍內(nèi)進(jìn)行橫向和縱向的對比研究。
3.5 微觀研究
現(xiàn)代科技的發(fā)展使我們能夠在恐龍微觀研究方面有所突破,特別是CT、電子顯微鏡、掃描電子顯微鏡、光譜儀、質(zhì)譜儀、能譜儀、3D掃描與打印等技術(shù)手段,能幫助我們觀察到恐龍骨骼的微觀結(jié)構(gòu)、礦物成分和化學(xué)組成,這對于我們研究恐龍的骨組織學(xué)、古病理學(xué)提供了重要技術(shù)支撐。這方面我們剛剛起步,還有大量的工作可為。
[1] Camp C. L.. Dinosaur remains from the Province of Szechuan, China. Univ. Calif. Publ. Bull. Dept. Geol. Sci., 1935, 23 (14): 467-469.
[2] Young C. C.. On a new Sauropoda, with notes on other fragmentary reptiles from Szechuan. Bull. Geol. Soc. China, 1939, 19 (3): 279-315.
[3] 楊鐘健. 四川宜賓的一種新蜥腳類[J]. 古生物學(xué)報(bào),1954, 2 (4): 355-369.
[4] 甄朔南, 李建軍, 韓兆寬, 等. 中國恐龍足跡研究[M]. 四川科技出版社, 1996, 1-110.
[5] 何信祿. 四川脊椎動物化石[M]. 四川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 1984, 1-168.
[6] 楊興隆, 楊代環(huán). 四川盆地恐龍足印化石[M]. 四川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 1987, 1-30.
[7] 董枝明, 周世武, 張奕宏. 四川盆地侏羅紀(jì)恐龍化石[J]. 中國古生物志,新丙種, 1983, 162 (23): 1-145.
[8] 邢立達(dá), 馬丁·洛克利, 張建平. 中國西南早白堊世恐龍及其他四足類足跡[M]. 寧波出版社, 2016, 1-410.
[9] 彭光照, 葉勇, 高玉輝, 舒純康, 江山. 自貢地區(qū)侏羅紀(jì)恐龍動物群[M].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1-236.
[10] 王全偉, 梁斌, 闞澤忠, 李奎, 朱兵, 紀(jì)相田. 四川盆地中生代恐龍動物群古環(huán)境重建[M]. 地質(zhì)出版社, 2008, 1~189.
[11] 董枝明. 中國的恐龍動物群及其層位[M]. 地層學(xué)雜志, 1980, 4 (4): 256-263。
[12] 李奎, 謝衛(wèi), 張玉光. 四川侏羅紀(jì)恐龍化石[J]. 大自然探索, 1997, 16 (59): 66-70.
[13] Xing L. D., Ye Y., Shu C. K., Peng G. Z. et You H. L. Structure, orientation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the tail club of. Acta Geologica Sinica, 2009, 83 (6): 1031-1040.
[14] 葉勇, 彭光照, 江山. 四川自貢大山鋪中侏羅世蜀龍和峨眉龍長骨骨組織結(jié)構(gòu)的初步研究[J]. 古生物學(xué)報(bào), 2007, 46 (1): 135-144.
De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Dinosaur Fossils in Sichuan
PENG Guang-zhao1QIN Gang2YE Yong1ZHU Tao-xiu2HAO Bao-qiao1JIANG Shan1TANG Wei2LI Shuang-jiang2
(1-Zigong Dinosaur Museum, Zigong, Sichuan 643013; 2-Geological Society of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610081)
Sichuan Province is rich in resources of dinosaur fossils. It's been over 100 years since the first discovery of the dinosaur fossils in 1915. The research into dinosaur faunal assemblages, systematic evolution, causes of mass death and buried environments, life habit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bone histology and paleopathology etc. has achieved world famous results. Up to now, there are 35 genera, 48 species of dinosaur bones and 21 genera, 20 species of dinosaur footpr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which count for respectively one-fifth of all dinosaur bone species and one-third of all dinosaur footprint species in China. They include the earliest dinosaur tracks, and the most typical Middle Jurassic-Fauna and Late Jurassic-Fauna. We look forward to great breakthroughs in discoveries of early or late dinosaurs, absolute dating, systematic evolutions, regional correlation and microscopic researches etc. in the future.
Sichuan; dinosaurs; history; present situation; prospect
2018-09-01
彭光照(1963-),男,四川隆昌人,研究館員,主要從事古生物學(xué)與地層學(xué)相關(guān)研究
李雙江(1986-),女,四川廣元人,工程師,主要從事地質(zhì)礦產(chǎn)勘查、水工環(huán)地質(zhì)相關(guān)工作
[P52]
A
1006-0995(2019)02-0215-09
10.3969/j.issn.1006-0995.2019.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