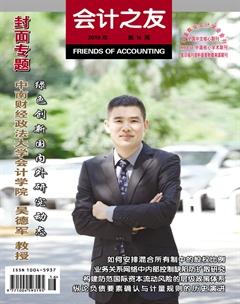如何安排混合所有制中的股權比例
于成永 劉旭 丁明明
【摘 要】 混合所有制是國企改革的重要方向,如何安排第一、前五或前十大股東股權比例是個理論與實踐都有待解決的問題。在現有文獻中,有關股權集中與企業績效變化關系的理論觀點紛呈,證據矛盾。在區分“一股獨生”“大股東共生”生態基礎上,分析了“股東數量遞增效應”與“持股非均衡效應”,提出混合所有制股權比例安排假設后,以中國銀行業為例,文章運用元分析技術,依據40篇樣本文獻,提取了148個方程信息,經實證檢驗后發現:一是第一大股東股權越集中,企業績效越差;二是前五或前十大股東股權越集中,企業績效越好;三是前十大股東股權集中能夠減弱第一大股東利益侵害;四是前十大股東股權集中效應高于前五大股東股權集中作用;五是前五大股東股權內部不均衡效應相對顯著。文章政策啟示在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應重視降低第一大股東持股集中帶來的利益侵害,也應著力培育多個大股東,特別是前十大股東力量;同時,應注意大股東之間股權比例分布適度均衡。
【關鍵詞】 混合所有制; 股權集中; 企業績效; 銀行業; 元分析
【中圖分類號】 F27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9)16-0143-10
國企改革歷經放權(自主經營)、兩權分離(所有權、經營權分離,政企分開)、現代企業制度和股份制,目前已經進入混合所有制和分類改革攻堅階段[1]。從微觀角度看,國企混合所有制一般是指企業產權性質除國有成分外,還包括非國有成分。混合所有制經濟經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于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得到進一步強調。與制度背景形成互動,根據中國知網檢索可以發現,學術界對混合所有制關注可以追溯到1998年,自2014年開始逐步成為研究熱點。一些文獻表明,“混改”對國有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具有促進作用[2,3]。在區分混合所有制企業、國企、民企以及外企基礎上研究發現,混合所有制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最強[3]。國企在進行混改中,引入非國有資本具有正面影響;不過,企業控制權的改革對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提升企業競爭力的作用更大[4]。一些國外文獻發現,完全國有或完全私有績效低于混合所有制企業;可見,混合所有制是國有或私有的有效替代[5-8]。
既然混改有利于提升企業創新能力和績效,那么,在國企進行混改時,不同大股東在持股比例上差異是否重要?一些研究表明,第一大股東與第二大股東既可能存在合謀,也可能存在制衡關系;甚至在特定條件下,中小股東也能夠獲得公司控制權[9-10]。從股權集中與企業績效變化關系上看,以新興市場國家為樣本的研究中,雖然單篇文獻之間經驗證據混合,但是元分析得到的整合證據是兩者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11];與此相反,在以亞洲國家為樣本的研究中,元分析得到的整合證據是兩者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12]。單獨以研究中國企業為對象的元分析文獻尚未見報道。更為重要的是,包括元分析方法在內的現有文獻沒能有效地回答以下問題:在混合所有制下,第一大股東、前幾大股東持股比例與企業績效變化關系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如果存在顯著差異,那么前幾大股東持股內部結構是否重要?
在理論分析基礎上,本文運用元分析方法,以研究中國銀行業股權集中與企業績效變化關系的文獻為樣本,檢驗了第一大、前五大以及前十大股東股權比例與企業績效關系假設。之所以選擇研究中國銀行業的文獻為樣本,是由于金融業特殊性。在中國,銀行業是國有資本集中或相對集中的行業,歷經多年改革,如股份制、引進戰略投資者以及上市,整體上已經處于混合所有制階段;進一步改革方向是調整不同所有制投資者比例以獲取股東治理效應[13-15]。
本文的價值在于:一是有助于解決現有文獻在股權比例與企業績效關系上理論紛爭和證據混合,修正股權比例與企業績效關系理論,發現了一股獨大的“獨生”生態是利益侵害成立的條件,而多個大股東“共生”生態是利益協同的基礎;二是研究了“共生”生態中大股東數量遞增效應與非均衡效應,運用元分析技術提供了相應經驗證據;三是一股獨大、多股共生生態以及數量遞增效應和非均衡效應在邏輯上具有遞進性,在利益協同上具有遞增性,這無疑為混改中股權比例安排提供了參考。
一、理論分析與假設
國企進行混改的結果,必然形成多個性質不同的大股東。大股東之間關系本質上在于多方博弈,其內部結構非常復雜[9,16]。現有文獻中有關股權集中對企業績效影響的理論觀點主要有三種:無關論、協同論與侵害論。無關論認為,股權結構是由股東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內生決定的,內嵌于潛在的和顯在的企業特征中;因此,股權結構與企業業績之間沒有顯著性關系[11]。相比較,有關股權比例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正向關系的利益協同論以及股權比例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負向變化關系的利益侵害論的觀點更為針鋒相對。
在本文看來,利益協同或利益侵害的基礎在于大股東生態類型。大股東之間存在兩種生態環境:一是一股獨大的“獨生”生態,其他股東制衡力量有限;二是多個大股東“共生”生態,是指不同性質的大股東之間所形成的密切互利關系,一類股東為另一類股東提供有利于企業持續發展方面的資源,同時也獲得對方的支持。此外,在大股東共生生態中,存在著大股東數量越多,越能獲得利益協同的“數量遞增效應”以及存在著少數相對持股高的大股東,這些大股東在決策和監督高管上更為積極的“非均衡效應”。
(一)獨生生態與利益侵害
利益侵害論強調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呈現負相關關系。本文認為,一股獨大的“獨生”生態傾向于利益侵害。這一論斷有以下依據:
一是一股獨大生態下,沒有能夠發揮制衡作用的其他大股東,或者其他大股東無力抗衡第一大股東行為。事實上,當第一大股東擁有遠高于其他股東的持股量時,其控制權地位便無人撼動[11]。理論上,大小股東之間代理問題表現在集中的股權可能增加大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風險,一股獨大可能便于大股東獲取私人利益而犧牲少數股東利益或產生潛在的低效活動。
二是在一股獨大情境中,其一,第一大股東在管理層任命和績效激勵上話語權更大,更易于與管理層形成合謀,或者大股東傾向于鞏固自己地位,派遣家庭成員或代表擔任管理層而非招聘更高素質的外部人,這不利于內部治理完善;其二,一股獨大的企業實際控制人權利不易旁落,這可能阻礙外部治理機制,如高管市場和控制權競爭市場或者并購市場上接管機制發揮作用,從而不利于公司治理改善。
三是一股獨大會造成投資風險過于集中在單一股東身上,企業融資約束程度高,這易導致融資成本過高。根據資本成本假說,一股獨大會增加公司籌資和管理風險。由于在一股獨大條件下更有可能發生大股東侵占,由此導致外部融資困難,遭遇融資約束。因此,一股獨大的公司更多地依賴于大股東的財富或企業內部產生的現金流為新項目提供資金,或者接受高資本成本籌資。一股獨大也降低了大股東的投資多元化,投資風險相對集中。
此外,在國有股權為第一大股東時,由于所有者虛置以及管理者激勵機制扭曲等問題存在,企業資源配置和使用極有可能是低效率的。
基于這些理由,可以提出假設1。
H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企業績效呈現負向變化關系,即一股獨大會造成利益侵害。
(二)共生生態與利益協同
本文認為,存在數個不同性質的大股東的“共生”生態更有可能形成利益協同,表現為股權集中正向影響企業績效關系。這是因為:
一是性質上迥異的股東之間易形成有效的制衡結構。股東在股權性質上相同時,實現目標時面臨的約束條件相近,擁有共同的利益。相反,不同性質的股東代表的利益主體不同,可能更傾向于互相監督與制衡,這有利于績效提升。在經驗證據上,一些學者利用案例研究發現,民營性質的第二大股東與國有性質的第一大股東博弈,形成利益制衡,有利于公司治理結構改善和企業績效提升[9]。
二是在有效的制衡和監督結構下,不同性質的大股東在管理層選聘和考核上具有激勵性和有效性。研究表明,不同性質大股東能夠有效地制衡并減少內部人侵占,顯著改進股權激勵契約,抑制高管防御行為[17]。在理論上,混合股權能夠緩解傳統上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代理問題,從而提高企業績效。混合股權集中不僅是相對于股權分散,大股東能夠分擔監督成本,有足夠的動力和權利約束管理層,減少其瀆職和不作為;而且不同性質的大股東之間能夠形成相互監督與制衡,不易發生攫取控制權私利或者隧道挖掘的“合謀”行為,降低代理成本。
三是在現階段公司發展所需要的資源要素并非完全通過市場競爭來獲取,不同性質的股權可以為公司帶來相應的資源。例如當非國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后,非國有股東能夠作為國有股東的制衡者,減少國有股東的非效率行為,并為企業提供不同的資源要素,進而促進公司績效的改善[17]。反之從國企角度看,國企進行混改引入非國有股東,能夠提升影響與控制力,優化資源配置[16]。國企進行混改能夠為非國有股東進入國企特定業務領域創造機會,有利于資本市場公平與公開[18-19]。
此外,不同于一股獨生生態會造成企業融資約束,研究發現,通過不同性質股東之間的利益博弈能夠實現企業資本成本最低[20]。
根據上述,本文提出假設2和假設3。
H2: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混合股權集中與企業績效呈現正向變化關系,即混合股權集中能夠形成利益協同。
在此基礎上,可以推論,實施混合所有制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降低,其他性質的股東持股比例增加,在一股獨大具有利益侵害后果這一假設下,混合股權能夠顯著降低第一大股東侵害行為的負面影響,可以認為:
H3: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混合股權集中能夠減弱第一大股東利益侵害。
由于不同性質的大股東個數越多越難形成共謀,越易對一股獨大行為進行有效制衡,因此可預計,隨著不同性質的大股東個數增加,越有利于降低一股獨大的負面影響。據此,可以提出假設4。
H4:在其他條件不變下,隨著大股東個數增加,混合股權集中的績效效應隨之增加。
從邏輯上看,越平均的持股比重,越易形成相互掣肘,越難以有效地進行重大決策和對管理層進行激勵,從而造成決策延誤,管理層代理成本上升。因此,在不同性質的大股東持股結構中,股東內部持股比例不均衡效應預計較好。據此,可以提出假設5。
H5: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混合股權內部分布不均衡對企業績效具有正向影響。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與數據
為相對全面反映國內研究銀行業現狀,并構建樣本文獻,本文利用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維普資訊數據庫、萬方數據庫、Google學術搜索、百度學術搜索等,通過對篇名、主題、摘要和關鍵詞檢索涉及“股權集中度”“第一大股東持股”“股權結構”“所有權”“銀行績效”等詞匯的文獻。
考慮到民營銀行獲批始于2014年,學術期刊發表滯后,為了避免混入全民營銀行數據,本文樣本文獻檢索截至2014年12月31日。同時,利用萬得數據庫,對本文樣本文獻中數據對應年份的前十大股東性質進行分析,也驗證了銀行業整體上已處于混合所有制階段的判斷。
在此基礎上,通過以下標準進行手工篩選:(1)僅選取公開發表在學術期刊上論文;(2)僅保留研究銀行業的實證文獻;(3)刪除缺少元分析所需基本數據的文獻;(4)鑒于現有支持股權集中與企業績效存在非線性關系文獻篇數較少,無法提供足夠數據進行元分析且非線性關系非本文關注點,因此,刪除股權與企業績效關系呈現曲線關系的文獻。經過上述篩選,最終得到40篇樣本文獻,具體見附表1。
從附表1中可看出,以中國銀行業為樣本的實證研究文獻結論迥異。支持負向關系的有11篇,如祝繼高等(2012)和譚興民等(2010)基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支持正向關系為9篇,如何婧(2014)、趙尚梅等(2012)基于前十大股東持股比與企業績效的研究以及楊德勇(2007)等基于前五大、前十大股東持股比與企業績效關系研究;不顯著12篇,如傅勇等(2011)基于前十大股東持股比與企業績效關系研究以及高正平(2010)等基于前五大股東赫芬德爾指數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等。可以看出,無論股權集中度用什么指標測量,均存在負向、正向、不顯著等多種類型證據。這些混合證據類似于國外發現[11]。
根據樣本文獻中股權比均值,本文進一步分析了其統計特征(表1)。以樣本文獻觀察值為權重,第一大股東持股比均值為0.22,最低0.020,最高為0.742;前五大股東持股比的均值為0.544,最低0.307,最高0.673;以赫芬德爾指數計算的前五大股東持股比均值為0.391,最低0.020,最高0.742;前十大股東持股比均值0.581,最低為0.082,最高為0.706。
通過股權集中度與企業績效關系效應值漏斗圖(見圖1)分析,本文分析涉及的效應值基本落在-10與10之間,而其標準誤絕大部分低于0.3,沒有效應值的標準誤高于0.4。這與Pursey et al.、Kun Wang與Greg Shailer(2015)數據分析分布類似[11]。
(二)變量設計
1.被解釋變量
樣本文獻中股權集中度與企業績效關系的偏相關系數與其標準誤的商,即t統計量為本文被解釋變量,按照元分析一般習慣,稱之為效應值。表2顯示,效應值簡單平均數為-0.097,極大值為9.562,極小值為-22.966。
2.解釋變量
考慮股權集中度測量差異,本文分別以樣本文獻的股權集中與企業績效關系方程中是否采用第一股東比重(CR1_indep)、前五股東比重(CR5_indep)、前十股東比重(CR10_indep)以及前五股東持股比平方和(HI5_indep)為解釋變量;其中,與CR5_indep相比較,HI5_indep由于是選用前五大股東持股比平方和,在同樣水平的CR5_indep下,前五大股東持股越不均衡,HI5_indep越大,因而HI5_indep體現了前五大股東持股不均衡情形。如表2所示,在這些指標中,第一大股東、前五大股東或前十大股東比重選用程度高,分別占48%、23.6%以及19.6%,而前五大股東持股平方和指標選用相對較低,為8.8%。
3.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包括樣本文獻的股權集中與企業績效關系方程中企業績效測量、樣本數據特征、估計方法、估計精度以及出版物地位等,具體統計特征見表2所示。可以看出,在企業績效測量指標選用上,總資產利潤率(ROAdep)最多,占32.4%;排在第二位的是凈資產收益率(ROEdep),占28.4%。在樣本數據來源上,上市公司數據(Listed)大致占45.9%。從樣本數據時間區間中值(Middletime)看,具有13年長度(2000—2012年);大致有58.8%的方程含有董事會特征變量Boardvar,64.2%的方程含有企業規模變量(Sizeofbank)。
(三)模型設計
本文中股權集中度與企業績效關系效應值來自樣本文獻股權集中與企業績效關系方程中股權集中變量的系數ti,j統計量,它也等于股權集中與企業績效之間偏相關系數pcci,j與其標準誤se(pcci,j)的商。ti,j表示來自第j個來源文獻的第i個效應值。
借鑒現有研究,構建隨機效應均值模型,即Hedges-Vevea模型來檢驗利益侵害與利益協同假設:
此處,誤差項被分解成兩部分:一是文獻水平上隨機項(study-level random effects),即ζj;二是估計水平上干擾項(estimate-level disturbances),即εi,j。
如前述,在樣本文獻中,研究設計上差異具體表現在企業績效測量、股權集中度測量、估計方法、數據特征等多個方面。借鑒Petra Valickova等研究,本文引入以下混合多水平元回歸模型(Mixed-level metaregression)來檢驗股東數量遞增效應與非均衡效應[21,22]:
此處,Xi,j=(x1,i,j,…,xp,i,j)是p個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的向量,這些變量指表2中企業績效測量、股權集中度測量、估計方法、數據特征等方面變量。β=(β1,…,βp)是模型2回歸方程系數向量。1/se(pcci,j)是偏相關系數的標準誤的倒數,表示估計精度。
運用混合多水平元回歸分析方法對模型2進行估計,以規避樣本文獻內和樣本文獻之間異質性導致的偏差以及可能的內生性等問題。此外,運用聚合標準誤Robust線性回歸和一般到特殊回歸(General to Special)技術進行了相應假設的穩健檢驗[22]。
三、實證分析
(一)利益侵害與利益協同假設檢驗
運用模型1,采用REML檢驗方法,得到不同測量指標下股權集中度與企業績效關系效應值,如表3所示。數據表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CR1_indep)效應值為-0.867,在10%水平顯著,這支持了H1,即一股獨大均有利益侵害效應;前五大股東持股比(CR5_indep)對應的效應值為-0.411,不具統計顯著性;前五大股東持股比平方和(HI5_indep)對應的效應值為2.124,在5%水平上顯著,前十大股東持股比(CR10_indep)效應值1.170,在1%水平上顯著,這支持了H2,即混合股權具有利益協同效應。顯然,此處股權集中與企業績效關系方向的證據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與企業績效負向關聯的證據支持Kun Wang與Greg Shailer(2015)的股權集中與企業績效負向關系的發現[11];而前五或前十大股東持股比與企業績效正向關系證據和Pursey et al.[12]發現的股權集中與企業績效正向關系的證據一致。
(二)數量遞增與非均衡效應假設檢驗
采用模型2,用REML方法估計混合效應方程,得到表4數據。在方程1中,前五大股東持股比(CR5_indep)系數為0.172,t值為1.60,接近10%邊際顯著性,同時,在一般到特殊方程中,即方程2中,前五大股東持股比(CR5_indep)系數為0.217,t值為2.21,達到了5%顯著性水平,這說明前五大股東持股比效應值顯著高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與企業績效關系,這支持了H3。
從表4方程1看,前十大股東持股比(CR10_indep)系數為0.360,t值為3.43,達到了1%水平上顯著;從表4方程2看,在一般到特殊方程中系數為0.42,t值為4.64,也達到了1%水平上顯著。這些證據表明,前十大股東持股比效應值顯著高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效應值,這也支持了H3。
利用估計后檢驗,在方程1中,對β1(CR5_indep)<β2(CR10_indep)關系檢驗發現,F值為1.88,接近10%水平上顯著;在一般到特殊方程中,即方程2中,對β1(CR5_indep)<β2(CR10_indep)關系檢驗發現,卡方值為2.66,在10%水平上顯著。這些證據支持了H4,即前十大股東股權集中減弱第一大股東利益侵害程度高于前五大股東股權集中作用。
進一步檢驗股東持股均衡集中效應,表4表明,利用估計后檢驗,在方程1中,對β1(CR5_indep)<β3(HI5_indep)關系檢驗發現,F值為6.17,在1%水平上顯著;在一般到特殊方程中即方程2,對β1(CR5_indep)<β3(HI5_indep)關系檢驗發現,卡方值為7.07,在1%水平上顯著。這些證據支持了H5,即前五大股東股權內部分布不均衡減弱第一大股東利益侵害程度相對顯著。
(三)穩健性檢驗
一是對模型2采用線性回歸聚合標準誤Robust檢驗方法得到表5證據。表5與表4主要差異在于對β1(CR5_indep)<β2(CR10_indep)關系檢驗發現,F值為1.05,沒有顯著性,僅在一般到特殊技術中,即方程4中發現F值為2.82,在5%水平上顯著。
二是為了防止樣本文獻本身質量影響,進一步剔除了非CSSCI期刊樣本文獻,運用混合效應模型進行了檢驗,發現上述主要結論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如表6所示,其中,方程5為CSSCI樣本文獻檢驗結果,方程6為CSSCI樣本文獻且對連續變量進行5%縮尾后檢驗結果。
三是在CSSCI樣本文獻基礎上,運用聚合標準誤線性回歸Robust檢驗(附表2)發現,方程7為CSSCI樣本文獻檢驗結果,方程8為CSSCI樣本文獻且對連續變量數值進行5%縮尾后檢驗結果。可以發現,方程也提供了支持本文主要假設的證據。
四是采用鎖定解釋變量逐步回歸方法,分別對全樣本、CSSCI來源文獻樣本進行了穩健回歸檢驗,發現結果與前文沒有明顯差異。
四、結論與啟示
(一)基本結論
通過上文研究,可以認為,在理論上,存在一股獨大“獨生”生態、混合股權的“共生”生態以及共生態中股東數量遞增效應、股東持股非均衡效應。實證檢驗發現:(1)“一股獨大”生態中存在利益侵害;(2)“大股東共生”生態中存在利益協同;(3)大股東個數越多,減少利益侵害程度越顯著;(4)大股東非均衡共生時減少利益侵害程度越顯著。
作為結論可拓展解釋的是,本文提出了利益侵害與利益協同存在于不同的股東生態環境,且這一論點能夠得到元證據支持,這不但直接解決了現有文獻存在利益協同與利益侵害理論觀點針鋒相對、經驗證據混合現象,而且也檢驗了混合所有制中大股東持股比例安排假設。
(二)研究啟示
本文證據具有遞進關系,即“一股獨大”存在利益侵害,應鼓勵“大股東共生”;特別是,既要鼓勵大股東數量增長,也應避免大股東之間股權均衡化,以防相互掣肘,導致決策效率下降。
據此,在微觀企業層面上,本文價值在于對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權比例安排提供以下參考:一是降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以避免一股獨大帶來的利益侵害;二是增加前五大,特別是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以提升利益協同程度;三是在大股東持股比例分布中,避免平均化,以提升決策效率。
【參考文獻】
[1] 于成永.制度質量與企業并購悖論關系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2-4.
[2] 趙放,劉雅君.混合所有制改革對國有企業創新效率影響的政策效果分析——基于雙重差分法的實證研究[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6):67-73.
[3] 吳延兵.不同所有制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考察[J].產業經濟研究,2014(2):53-64.
[4] 武常岐,張林.國企改革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及企業績效[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5):149-156.
[5] BUTLER F C,et al.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acquired Top management team turnover on firm performance post-acquisition:a meta-analysis[J].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2012,(1):47-60.
[6] KATO,KAZUHIKO.Optimal degree of privat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J].Journal of Economics,2012(2):165-180.
[7] MONTEDURO,FABIO.Public Private versus public ownership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italian local utilities[J].Journal of Management & Governance,2012(1):29-49.
[8] TATAHI,MOTASAM.Enterprise performance,privatization and the role of ownership in finland[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ehavioral Studies,2013(3):122-135.
[9] 郝云宏,汪茜.混合所有制企業股權制衡機制研究——基于“鄂武商控制權之爭”的案例解析[J].中國工業經濟,2015 (3):48-60.
[10] 鄭國堅,蔡貴龍,盧昕.“深康佳”中小股東維權:“庶民的勝利”抑或“百日維新”?[J].管理世界,2016 (12):145-158.
[11] WANG K,SHAILER G.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markets:a meta-analysis[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15,29(2):199-229.
[12] Heugens,et al.Meta-analyzing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sia:towards a more fine-grained understanding[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9,
26(3):481-512.
[13] 劉兵勇,我國商業銀行產權、股權與混合所有制改革[J].江西社會科學,2016(6):52-60.
[14] 王曙光,楊敏,徐余江.制度勢能的實現機制及績效:金融業混合所有制構建與戰略投資者引入[J].社會科學戰線,2017(1):33-42.
[15] 張樂,韓立巖.混合所有制對中國上市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影響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16(7):50-61.
[16] 馬連福,王麗麗,張琦.混合所有制的優序選擇:市場的邏輯[J].中國工業經濟,2015(7):5-20.
[17] 楊志強,石水平,石本仁,等.混合所有制、股權激勵與融資決策中的防御行為——基于動態權衡理論的證據[J].財經研究,2016(8):108-120.
[18] 鄭志剛.國企公司治理與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邏輯和路徑[J].證券市場導報,2015(6):4-12.
[19] 李東升,杜恒波,唐文龍.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利益機制重構[J].經濟學家,2015(9):33-39.
[20] 汪平,鄒穎,蘭京.異質股東的資本成本差異研究——兼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財務基礎[J].中國工業經濟,2015(9):129-144.
[21] VALICKOVA P,HAVRANEK T,HORVATH R.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a meta-
analysis.[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15,29(3):506-526.
[22] 于成永.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方向與結構差異——源自全球銀行與股市的元分析證據[J].南開經濟研究,2016(1):3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