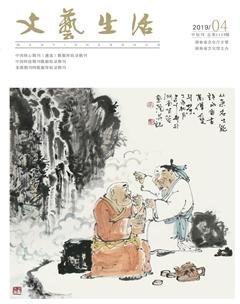論元好問《論詩絕句》對潘岳的評價
胡劍
摘要:元好問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其文學思想集中體現在《論詩絕句》三十首之中。元遺山通過對漢魏至宋代著名的作家或文學流派的評論,闡明了自己的文學理論主張,其思想在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重要的影響。其第六首本著詩歌應抒發真情實感的原則,對西晉文人潘岳的的作品提出了“心畫心聲總失真”的批評。但是聯系其他名家對潘岳的評價,并結合潘岳生活的背景及其詩文創作來考察,潘岳所抒發的隱逸之情是與其內在敏感多情的氣質相符,不能簡單地因其政治上的污點否定其文學創作的價值。
關鍵詞:元好問;《論詩絕句》;真與誠;潘岳;文品與人品
中圖分類號:120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9)11-0001-01
一、前言
《論詩絕句》是在元好問文學理論思想的集中體現。這組七言絕句繼承了杜甫“以詩論詩”的傳統,在整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縱觀這三十首絕句,作者在情感抒發上提倡真情實感之作,在藝術風格上推崇風云壯闊之作,在詩歌創作上偏愛自然天成之作,在詩歌流派上批評江西詩派的“閉門覓句”的創作。元好問在《論詩絕句》第六首評論潘安仁的代表作品《閑居賦》時云:“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仍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元好問認為潘岳在《閑居賦》中抒發的閑居隱逸之情和他饞侍賈謐、望塵而拜的實際行為相背離,是文品與人品的背離。那么,潘岳在《閑居賦》中抒發的情感是否虛假?是否能夠因為“拜路塵”之事而否定《閑居賦》?事實似乎并不盡然。
二、遺山對真與誠的強調
我國傳統詩學理論中主張“詩言志”“詩緣情”,詩歌之于文人,是表達內心情感的重要載體,詩人情動,才有了將內心情感付諸文字的實踐行為。故而元好問主張作詩需要真情,反對虛假偽飾之作。《論詩絕句》三十首中對此多次申訴強調。第四首在評價陶淵明詩歌之時云:“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遺山在贊美陶淵明詩歌自然質樸、不假雕琢的風格之時,也對陶詩中的真樸淳厚之情感給予了極大的肯定,并認為陶詩乃萬古常新、具有永恒魅力的佳作。第五首評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詩歌時云:“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阮步兵的詩歌同樣得到了遺山的認可,阮籍雖然行為佯狂任誕、且多驚世駭俗之舉,但是他心中的矛盾痛苦、糾結無奈之情卻在詩文之中得到了真實地反映。遺山認為阮詩的縱橫之氣如長江大河洶涌奔騰,而這正是胸中不平之氣的真實流露。同陶詩相比,阮詩雖頗顯“遙深”,但始終是詩人內心情感真實的流露。遺山對阮詩的肯定正是對詩言真情的肯定。除此之外,《論詩絕句》中十二首、十五首、十九首也都不同程度了體現了遺山對真情實感的強調。
三、安仁的心畫與心聲
心畫心聲之說由揚雄提出,他在《法言·問神》中云:“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楊雄認為言語是心聲,文字是心畫,透過言語文字,可以窺探出人的內心、判斷出品質道德的高低。
潘岳為西晉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流傳下來了眾多文質兼美的詩文佳作,與太康之英陸機并稱為“潘陸”。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潘岳美名遠揚,一方面與他風姿神韻有關,但更多是自身卓絕的文學才能。蕭統、劉勰、鐘嶸對安仁的詩賦文都推崇極高。如蕭統在《昭明文選》賦類中收入安仁辭賦八篇,為歷代賦家之最;劉勰《文心雕龍》中對潘岳也多次贊美,高度推崇他的誄文……對于潘岳在文學上杰出成就我們是無法否認的。
遺山所言安仁拜路塵,并不是街談巷議之語,而是在正史之中明確有記載的。《晉書·潘岳傳》載:“岳性輕躁,趨勢利……岳為其首。”潘岳熱衷仕途,對政治有著極大的熱情,不顧尊嚴地阿諛奉承,不辨是非地陷害他人。其卑劣人格與優秀詩文成為文學中迷霧,人們對此頗多爭議。
就《閑居賦》而言,潘岳主要抒發了對閑居隱逸生活的向往之情。“仰眾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舊,潘岳在多次的宦海沉浮之后,向往隱居的閑樂生活,此主旨也正和賦的題目“閑居”二字相契合。此賦作于安仁政治和情感雙重失意之時,免官、喪妻都發生在此前后,內心愁苦悲痛之情充溢,故而心生歸隱之思,從此角度上講,《閑居賦》并非偽情之作,是詩人內心情感之自然流露。而且“遺山所說的真詩觀簡言之,就是詩文為詩人當時當地真情的抒發”,那么遺山又為何認為《閑居賦》乃失真之作呢?因為在第二年,潘岳便再次投入到政治的熱潮中去,讒事賈謐,望塵而拜,構陷太子,關于潘岳的人品的穢行多發生在這段時間。潘岳此時的所作所為很難使人們相信《閑居賦》中所抒發的千古高情。
四、人品與文品的辨析
文如其人是我國古代一個古老的命題,文學作品常常要和作者的品德聯系起來。孟子要求理解作品要做到“知人論世”,即同作家的品性和時代背景結合起來。后來不少的理論家對文如其人的命題也多有論述。但總體上看來:在文品與人品的關系上,我國古代的文學理論家多數是傾向于贊同“文如其人”的。然而縱觀整個文學史,我們可以發現,事實上存在很多的“文非其人”的現象。初唐時期著名的詩人宋之問,其與沈儉期被后人合稱為“沈宋”,二者對律詩的發展具有開創性的貢獻。但其人品卻飽受詬病,因詩殺親、賣友求榮、逢迎諂媚,其所作所為,為當時文人所不齒。像此類薄于操守卻又有佳作的文人歷史上還頗為常見,潘岳僅為其中之一。人品與文品不相一致,如此便可認為作者在詩文中都是在說假話嗎?對此,陳琳先生就曾提出過置疑,他認為:魏晉知識分子生活在儒道交織的思想中,一邊熱心功名,一邊歌詠隱逸,張華如此,二十四友中也不乏少數,歸根結底,只是一種時代風尚而已。縱觀潘岳《閑居賦》中的隱逸思想,并不是對功名之心的虛偽巧飾,而是受其時代風尚和個人命運的影響。
那么,該如何來理解“文如其人”這個命題呢?蔣寅先生曾對此有過詳細的探討辨析。其認為“我們可以在一定限度內來談論這一命題,即文如其人是如人的氣質,而非如人的品德”,此也正如曹丕所云“文以氣為主”。若從此種觀點出發,潘岳作品之中流露出來的悲苦之痛、隱逸之情不正和他深情敏感的性格氣質相一致嗎?如此,便能理解蕭統、劉勰、鐘嶸等人為何對潘岳的詩文評價如此之高,他們都是從純粹的文學的角度來評價作家作品的,而元遺山則是以道德為出發點的,故而得出了人品與文品的背離。
元好問強調詩歌創作要抒發真情實感,是十分有道理的。詩歌作為情感抒發的媒介,固不可虛假偽飾。但是詩歌的真與誠應歸結于詩人的氣質,更何況人的性格是復雜多樣且易于變化,文學的風格也是多變的,不可輕易判斷。道德上的污點可以是鄙棄人品的原因,但是若因人廢言就難免偏頗。
元好問論詩,重在評論著名的詩人和詩人所屬于的詩歌流派,他能夠旗幟鮮明地亮出自己的詩歌主張,不人云亦云,雖自云“撼樹蜉蝣自覺狂,書生技瘁愛論量”,自謙如蚍蜉撼樹一樣不自量力,只是書生之議論而已,但是作者對潘岳、陸機、劉禹錫、孟郊、秦觀、黃庭堅、等詩中名家大膽提出批評,觀點新穎,論據充足,引人深思,且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總之,元好問的文論思想足以在整部文學批評史上獨樹一幟,值得再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