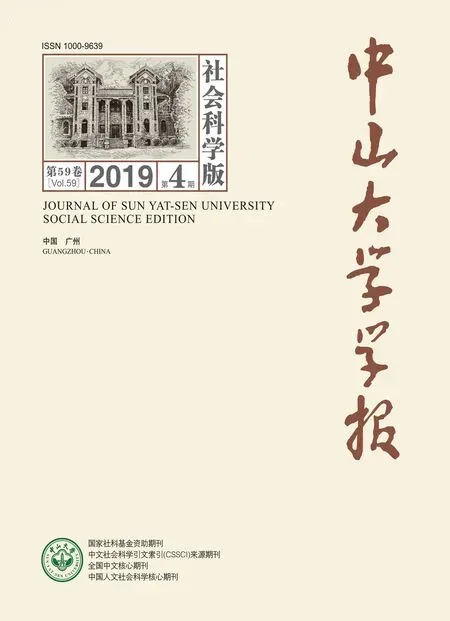明代漕運衛所中的藩王護衛軍*
張 程 娟
明初護衛指揮使司是藩王直接掌握的軍事力量,洪武五年(1372)規定藩王設三支護衛①《明太祖實錄》卷71,“洪武五年春正月己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313頁。。作為護衛藩王的軍隊,卻在明代長期被納入到漕運體系中,成為漕運衛所運軍的重要組成部分,此情狀尚未引起學界重視。《漕運通志》等文獻所記載的127個漕運衛所中,其一名曰“兗州護衛”,位于山東總下②楊宏、謝純:《漕運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魯府招》等文獻對兗州護衛運糧等亦有詳細記載③《魯府招》,《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30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據明抄本影印。按:嘉靖初年魯端王與其叔祖館陶王朱當淴不和,分別向朝廷上書攻擊對方,揭露對方的種種不法行為,皇帝令刑部左侍郎楊志學等三位欽差前去審理,《魯府招》即為審理記錄,大致成書于嘉靖十六年。目前學界對此文獻利用不多,相關研究唯有吳艷紅的《明代宗藩司法管理中的分別議處——從〈魯府招〉說起》,《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2期。,提示我們有必要將漕運衛所與藩王護衛軍結合在一起進行考察。兗州護衛是配給魯王府的護衛軍,卻出現在漕運衛所中,而且魯藩護衛并非孤例,遍檢《漕運通志》所載漕運衛所成立之情況,發現徐州左衛、東昌衛、任城衛、豹韜左衛和龍虎左衛等的設立均與藩王護衛軍有所關聯,它們分布在徐州到南京的運河沿線,涉及的王府有楚王府、蜀王府與魯王府,此現象顯然值得關注。
藩王護衛軍與承擔漕運任務的漕運衛所關系密切,楚藩和蜀藩護衛軍在宣德年間實現了長距離的徹底改調,而魯藩護衛軍的調動則經歷了復雜的過程。以漕運衛所中的藩王護衛為切入點,有助于推進對于削藩政策的具體實施與漕運衛所的特質等問題的理解。
明代削藩的政策與方式多樣,相關研究成果豐碩,多認為裁撤護衛軍是削藩政策的一種重要形式。永樂時期,朱棣便已開始削弱藩王權勢,曾提倡藩王交出護衛軍,宣宗繼承此政策,裁撤藩王護衛軍④顧誠:《明代的宗室》,《明清史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2頁;張顯清:《明代宗藩由盛到衰的歷史演變》,《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2期;趙毅:《明代宗室政策初探》,《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馬長泉、張春梅:《明成祖削藩策略簡論》,《新鄉師專學報》1994年第1期;蘇德榮:《明代分封制度的演變》,《鄭州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趙中男:《明宣宗的削藩活動及其社會意義》,《社會科學輯刊》1998年第2期;楊永康、賈億寶:《明初藩王護衛牧羊制度的起源與演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5年第2期;鄭曉文:《明代河南藩王護衛的設置和裁撤》,《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10期;宋永志:《明代宗藩制度的調適與演變:以藩王移國為例》,《歷史教學問題》2018年第4期。。但是對于削藩政策的具體情境、藩王護衛軍的去向及如何將藩王護衛軍安置于王朝國家疆土管理體系等問題,學界鮮有觸及。我們認為將被裁撤的藩王護衛軍納入都司衛所體系,是比較直接的辦法,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又因時地人情不同而有所差異。朝廷在裁撤護衛軍的過程中,結合國家當時所面臨的重要問題,將軍隊安置與國家制度結合在一起考量,既可以達到削藩目的,又可以緩解國家所面臨的諸如漕糧運輸等問題。在全國藩王護衛軍裁撤改調過程中,楚藩、魯藩和蜀藩護衛軍的裁撤所呈現出的復雜過程尤為典型,其護衛軍的裁撤均與漕運改革有關,漕運重臣將削藩政策與漕運改革聯系在一起,既能達到削藩目的,又可以補充運軍,將護衛軍納入到漕運衛所體系,使得護衛軍得以安置。此外,明代中后期,很多府州城面臨著衛所城操不足的問題,將同府所在藩王護衛軍改立新的衛所,亦是削藩政策和護衛軍安置過程中的具體操作方式。
同時,考察明代漕運衛所中的藩王護衛軍,是理解漕運衛所的重要面向。明代漕運衛所是運軍的基本組織,前輩學者多將運軍的組織層級概括為運軍—衛所—運總。相關研究集中在運軍與運總組織變化方面[注]星斌夫:《明代漕運の研究》,日本學術振興會刊,第四章《明代漕運の軍運組織とその運営》,第179—235頁;唐文基:《明代的漕軍與漕船》,《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4期;林仕梁:《明代漕軍制初探》,《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5期;鮑彥邦:《明代漕軍的編制、任務及其簽補制度》,《暨南大學學報》1992年第9期;陳峰:《明代的運軍》,《中州學刊》1997年第1期;王偉:《論明清時期的漕運兵丁》,聊城大學2007年碩士論文;王偉:《明代漕軍制的形成與演變》,《聊城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徐斌:《明清軍役負擔與衛軍家族的成立——以鄂東地區為中心》,《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于志嘉:《明代江西衛所屯田與漕運的關系》,收入《衛所、軍戶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00—235頁。,但對漕運衛所這一層級則關注較少,很多問題尚未解決,比如漕運衛所的來源、設立之初的情境與原因等。關注藩王護衛軍調動背后的具體原因、調動過程、統轄方式以及藩王護衛軍在不同的時期如何納入漕運體系,有助于進一步分析漕運衛所最初設立的原因、漕運衛所與藩王護衛軍的關系和漕運衛所的特質性。本文便以楚藩、蜀藩和魯藩為中心,考察藩王護衛軍裁撤的具體運作過程以及與漕運衛所的內在聯系。
一、宣宗削藩與漕運衛所設立:楚藩和蜀藩護衛軍的調動
藩王護衛參與漕運可以從楚藩護衛的調動前后展開。洪武三年(1370)楚王楨受封,洪武十四年(1381)之國于武昌府,設有武昌三護衛,即武昌左護衛、武昌右護衛及武昌中護衛,守護藩王城。明初護衛軍是藩王掌握的軍事力量。按洪武五年的規定,藩王設三護衛,衛設五所,所設千戶二人、百戶十人[注]《明太祖實錄》卷71,“洪武五年春正月己酉”,第1313頁。。其官屬設置為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一人、指揮僉事四人等。“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注]張廷玉等撰:《明史》卷116《列傳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557頁。這是藩王護衛設置的一般情況。明初分封諸王時,護衛軍士人數尚少,僅供侍從護衛而已。大約到了洪武末年,諸王府的三護衛規模日增,統率的軍隊越來越多,掌握了相當大的軍事統率權和指揮權[注]張德信:《明代諸王分封制度述論》,《歷史研究》1985年第5期。。
靖難之役后,永樂帝逐步推行削藩政策,其中或明或暗地削減護衛軍是重要舉措之一[注]參見顧誠:《明代的宗室》,《明清史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集》,第1—12頁;馬長泉、張春梅:《明成祖削藩策略簡論》,《新鄉師專學報》1994年第1期。。但永樂帝對楚府的態度比較緩和,沒有大規模地征調和削弱楚府護衛軍。直至宣德五年(1430)十一月,宣宗決定“改武昌中護衛為武昌護衛,調左護衛于東昌,改為東昌衛,右護衛于徐州,改為徐州左衛”[注]《明宣宗實錄》卷72,“宣德五年十一月戊戌”,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684頁。按:正統《彭城志》卷2《軍功》記載:“徐州左衛,在城之西隅,宣德五年,調楚府護衛官軍于徐州,由是立衛所,領左、右、中、前、后凡五所云。”見《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325冊,第20頁。嘉靖《山東通志》卷11《兵防》記載:“東昌衛,在府治南,原系湖廣武昌護衛,宣德六年,調東昌府,改名東昌衛。”《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51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718頁。。至此,楚藩只剩一支護衛軍,即武昌中護衛,后稱武昌護衛。宣德年間為何對楚藩護衛軍進行調動,并隨之改建徐州左衛與東昌衛,值得探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昌右護衛調入徐州之前,當地軍事建置已頗具規模。自明吳元年(1367)徐州設立州治,同時建立徐州衛,起初領五所,永樂五年(1407)戰事頻繁,又調靈山、安東二衛軍到徐州衛,由是增設二所,徐州衛共領七所。在明初整個王朝國家衛所駐防體系中,徐州衛看來也是備受重視的。同樣,洪武初東昌府已經有平山衛和臨清守御千戶所,軍事駐防嚴密[注]嘉靖《山東通志》卷11《兵防》,《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51冊,第718頁。。對于軍事規模已經很大的徐州和東昌府來說,加強兩地的軍事防御,可能不是調動楚藩護衛軍的主要考量。《明宣宗實錄》記載了楚藩護衛軍調動的具體過程,起于宣德五年漕運總兵官陳瑄令其子上密疏,曰:
平江伯陳瑄遣其子儀赍密奏言:湖廣東南大藩,襟帶湖江,控引蠻越,實交廣黔蜀之會,人民蕃庶,商賈往來,舟車四集。楚府自洪武初立國,有三護衛官軍,及儀衛司旗校,俱無調遣。四五十年之間,生齒繁育,糧餉充積,造船以千計,買馬以萬數,兵強國富,他藩莫及,而衛所之官多結為姻親,枝連蔓引,小人乘時,或有異圖,實難制馭。伏乞皇上勿為疑慮,斷自圣衷,于今無事之時,托以京師糧儲不充,命重臣與湖廣三司,選其護衛精銳官軍,給糧與船,令運至北京,因而留使操備,則剪其羽翼,絕其邪謀,王可以永保國土,而朝廷恩義兩全矣。上不納,顧謂侍臣曰:從來楚國無過,祖考待之皆厚,朕尤加意禮之,瑄何其過慮也,調兵運糧一時權宜,運畢則遣歸,拘留操備,上失宗親之心,下失軍士之心,鄙哉,瑄也。[注]《明宣宗實錄》卷64,“宣德五年三月丙辰”,第1511—1512頁。
從密奏內容看,陳瑄欲建議宣宗削弱楚國這個“湖廣東南大藩”,認為其若圖謀不軌,將會對皇權造成威脅,但楚府并未顯出不忠行為,陳瑄提議“托以京師糧儲不充”為由,選楚府護衛軍赴京師運糧,趁機留下操備,剪其羽翼。實錄的書寫為顯示皇帝的仁義,行文中宣宗對陳瑄持批評態度,認為陳瑄卑鄙多慮,而且調兵運糧本是一時之計,運完之后理應遣歸,若是在京拘留,將“上失宗親之心,下失軍士之心”,其要求沒有被批準。但事態的發展與此記載并不相契。同年十一月,楚王孟烷派遣楚府儀賓魏寧和長史楊振上奏,主動將三護衛中的兩支歸于朝廷。宣宗“猶疑”之際,兵部尚書張本勸說宣宗,楚王自愿交納護衛軍是“欲示簡靜,以杜讒邪,乃其深計遠慮”[注]⑤ 《明宣宗實錄》卷72,“宣德五年十一月壬子”,第1683—1684,1684頁。。張本的勸說使得皇帝既能夠保全“仁義”,又能夠達到削藩的目的。最后的結果是宣宗“順承雅意”,調左護衛于東昌,改為東昌衛,調右護衛于徐州,改為徐州左衛⑤。將楚府兩支護衛徹底地調走,而非暫調運糧,楚府僅留一支,楚藩軍事力量被大大地削弱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宣宗削藩的意圖。宣德年間,在朱元璋冊封的26個藩王中,只剩下8個藩府還保留有護衛軍,宣宗最終完成削藩之舉[注]趙中男:《明宣宗的削藩活動及其社會意義》,《社會科學輯刊》1998年第2期。另,張顯清的《明代宗藩由盛到衰的歷史演變》、趙毅的《明代宗室政策初探》、蘇德榮的《明代分封制度的演變》,在論述明初削藩政策時,也認為永樂、宣德采取削減護衛軍的方式。。可見,楚府護衛軍的調動正處于朝廷“削藩”的背景下。
雖然實錄記載的整個過程中,陳瑄被貶低為“鄙哉”,但他所動議的內容卻最終得以實行,這也足以讓我們反思他在提議削弱楚藩背后的考量,實際上與當時朝廷所面臨的運軍缺乏的局面相關。
宣德年間,陳瑄所統率的運軍常被工部等衙門用來修理南京殿宇或為南京運載諸物[注]《明宣宗實錄》卷22,“宣德元年冬十月辛酉”,第591頁。,陳瑄請求禁止運軍別差,得到皇帝允許[注]《明宣宗實錄》卷44,“宣德二年二月己未”,第669—670頁。。宣德五年三月,運軍不足問題更為嚴重,南京和直隸衛所運糧官軍,共兩萬余人,連年被派下西洋、征交趾或調到北京,運軍不足,“須增儧運”。為了補足歲用,陳瑄提議采取清軍的辦法,在南京、湖廣、江西、浙江和直隸衛所附近府縣迷失旗軍和見在操守軍中,選擇精壯的軍人補運軍的數量,但是清軍效果往往有限[注]《明宣宗實錄》卷64,“宣德五年三月己巳”,第1524—1525頁。。在削藩的背景下,運軍缺乏的局面可能是陳瑄提議調楚藩護衛軍運糧的考量。
改調護衛的結果補充了運河沿線的運軍數量。調到徐州和東昌的楚藩護衛軍主要充當運軍,徐州左衛和東昌衛成為新設立漕運衛所,徐州左衛屬江北總,東昌衛屬山東總,均由漕運總兵陳瑄統轄,并在《漕運通志》等文獻中記載有運軍、運船及運糧固定額數[注]楊宏、謝純:《漕運通志》,第86、90頁。。正德五年(1510),漕運總督邵寶所記“會議狀”稱,“(徐州)本衛左等五所運糧旗軍,原系湖廣武昌右護衛”[注]邵寶:《會議狀》,《容春堂集》續集卷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5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97頁。,也說明護衛軍調到徐州多承擔運糧任務。

表1 嘉靖年間徐左二衛軍役情況表 單位:人
資料來源:嘉靖《徐州志》卷8《兵防》。
據表1可知,直到嘉靖年間,徐州左衛的運軍仍占旗軍的大部分,對比京操軍和城操軍的比重,一定程度上亦可說明加強守御并非主要目的。同時,嘉靖《山東通志》記載了東昌府衛所軍役情況,洪武五年,東昌已設平山衛五所。宣德六年(1431),調武昌左護衛到東昌府,改名東昌衛[注]嘉靖《山東通志》卷11《兵防》,《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51冊,第718頁。。東昌府衛所軍役情況見下表:

表2 明初山東東昌衛軍役情況表 單位:人
資料來源:嘉靖《山東通志》卷11《兵防》。
據表2可知,調往東昌衛的楚藩護衛軍大多數也是充當運軍職役,守城軍比重較小,加強守御并非主要意圖。到了正統六年(1441),東昌衛又有一次調動。據康熙《濮州志》記載:“本湖廣武昌左護衛軍,宣德五年調東昌一衛五所,正統六年擇其最弱者移置濮州。”[注]康熙《濮州志》卷2《兵防》。方志編纂者將濮州所的來歷上溯到了武昌左護衛,濮州所與護衛軍亦有關聯。濮州所位于運河沿線,配有漕船25只,運軍250名[注]康熙《濮州志》卷2《兵防》。。正統六年設濮州所后,運糧軍占了旗軍數額的五分之二,至嘉靖年間,士兵多逃亡,留存者也多充當運軍。
宣德年間除了調楚藩護衛軍到運河沿線,蜀藩護衛軍也被裁撤和調動。據《明宣宗實錄》稱:
蜀王友堉奏,成都三護衛,請以中、右二護衛歸朝廷,留左護衛官軍供役。上嘉其能省約,從之。友焴又奏缺官請調補,及留南人為匠,皆從之。上命都督王彧、兵部侍郎王驥持書諭王,所歸二衛皆令赴南京,所過給糧與舟,仍命彧等途中善撫綏。[注]《明宣宗實錄》卷80,“宣德六年六月癸巳”,第1858頁。
同楚王面臨的削藩局面相同,宣德六年,蜀王友堉上奏將成都中護衛和右護衛歸于朝廷,只留下成都左護衛。宣宗派都督王彧和兵部侍郎王驥向蜀王下達諭旨,將兩支護衛軍調到南京,給予糧與舟,運輸漕糧。其中,成都中護衛改為豹韜左衛,成都右護衛改為龍虎左衛[注]《明宣宗實錄》卷83,“宣德六年九月壬戌”,“改成都右中二護衛官軍之調南京者,為龍虎左,豹韜左二衛”,第1917—1918頁。。豹韜左衛和龍虎左衛也為《漕運通志》所載漕運衛所,屬南京總。豹韜左衛有運軍2032名,漕船192只,龍虎左衛有運軍1439名,漕船142只,主要兌運湖廣、江西和浙江等地漕糧[注]楊宏,謝純:《漕運通志》,第78、80頁。。據《通漕類編》記載,宣德七年(1432),開始確立兌運法[注]《通漕類編》卷2,《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443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112頁。。與支運法相比,兌運法需要更多的運軍來運輸漕糧。宣德七年總兵官陳瑄繼續撥軍運糧,他上疏言運軍負擔沉重,大量逃亡,需要增加運軍,提議從豹韜左衛和各都司衛所的軍余中,增調16萬人充當運軍,進一步支持兌運法的運作[注]《明宣宗實錄》卷95,“宣德七年九月丙辰”,第2162頁。“行在戶部奏,比者平江伯陳瑄言,總督官軍一十三萬,歲運淮安、臨清等倉糧五百萬余石赴北京,人運糧四十石,春初河淺,舟行甚艱,夏秋有水又多,漂流損失,而軍士亦有疾病逃亡者,糧多不足,請增兵。今議于南京豹韜左等衛,及各都司直隸衛所軍余內,增撥通一十六萬人,從之。”。盡管無從知曉這次豹韜左衛所進一步增加的運軍數量,但可以看出調到南京的蜀藩護衛軍,主要承擔起漕運的職能。
徐州左衛、東昌衛、豹韜左衛和龍虎左衛均處于運河沿線,它們所在的徐州、東昌和南京亦是明代漕糧關鍵轉輸節點,在漕運體系中處于重要的地位。宣德四年(1429),面對運軍缺乏的問題,將楚藩護衛和蜀藩護衛調到徐州、東昌和南京,充當運軍,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運軍不足的問題,為之后施行“兌運法”提供了條件。這種結果與漕運總兵陳瑄的考量相吻合,同時,也合理“安置”了所裁撤的藩王護衛軍,給宣宗削藩政策的推行提供了正當的理由與操作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的兵部尚書張本,也在宣德五年幫助陳瑄補充運軍,將從浙江松門衛清出的軍士,“宜悉送平江伯陳瑄處,發邳州衛帶管運糧,以警其余,上從之”[注]《明宣宗實錄》卷74,“宣德五年閏十二月丁酉”,第1720頁。。再次透露出調楚藩和蜀藩護衛軍運糧之動議背后的復雜與微妙。
調楚藩護衛軍所建立的徐州左衛與東昌衛,納入了漕運衛所體系,明初屬于“江北直隸總”,運軍由漕運總兵官陳瑄統轄。在正德年間,清軍御史補充徐州左衛運軍時,到護衛軍的原籍勾補,不再到王府征調[注]邵寶:《容春堂集》續集卷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58冊,第497頁。。此外,即使所調護衛軍擔任徐州左衛和東昌衛的其他職役,如屯田及守城等,也不再受到王府制約,歸都司衛所管理。倪岳《青谿漫稿》中有一則劉宗岱將軍的傳記,記載了軍戶家族的承襲過程。宗岱祖父為武昌右護衛后所正千戶,宣德年間隨著衛所調動,改為徐州左衛正千戶,正統年間宗岱繼其父之后世襲該位,仍隸屬徐州左衛[注]倪岳:《青谿漫稿》卷2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第337頁。。又,《毛襄懋文集》中所記賈尚德傳:“賈懷,字尚德,咸陽人也,其先護衛楚藩,后調徐州左衛,今為左衛人。”[注]毛伯溫:《毛襄懋文集》卷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3冊,濟南:齊魯書社出版社,第321頁。可見,原屬于楚藩的護衛官軍調到徐州左衛之后,其本人及后代只隸屬于徐州左衛,調走的兩支護衛軍不再聽從楚王差遣。又,由武昌護衛軍所構成的東昌衛有配給的屯田[注]康熙《濮州志》卷2《兵防》。,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楚藩護衛軍調到東昌后脫離楚藩統轄,重新開始營生。蜀藩護衛軍的調動也是徹底的,蜀藩兩支護衛軍調走后,藩府將其屯田收歸為藩產,不再與調走護衛有關[注]譚綸:《懇乞圣明講求大經大法以足國用以圖安攘以建永安長治疏》,《譚襄敏公奏議》卷7,《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21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1052頁。。由此推知,宣德年間,楚藩和蜀藩護衛軍的調離比較徹底,調走的護衛軍在新設立的衛所中無論是充當運軍還是屯田軍、守城軍等,不再與王府發生聯系。
二、魯藩護衛軍與漕運:嘉靖十八年之前的改調與借調
上文所言,楚藩和蜀藩護衛軍在削藩背景下徹底調離。魯府左護衛早在永樂五年就被調走建立漕運衛所,相比之下,魯王府兩支護衛軍改調與借調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如果說永樂帝對楚府態度緩和,魯府則是永樂削藩對象之一,這應從魯府的設置情況說起[注]參見顧誠:《明代的宗室》,《明清史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集》,第1—12頁。馬長泉、張春梅:《明成祖削藩策略簡論》,《新鄉師專學報》1994年第1期。顧誠認為,朱棣從根本上改變了朝廷與諸藩的軍事力量上的對比。。洪武三年,朱元璋第十子朱檀被封為魯王,洪武十八年(1385)之國兗州府,在府治正中建立王城[注]康熙《兗州府志》卷4《建置》,“宮殿城垣,備極宏敞”。,并將兗州護衛軍賜給魯王,位于府治東。明代兗州有魯、德、衡、涇諸多王府宗室,卻單獨為魯藩設立了護衛軍。關于魯府護衛最初設立的情況,方志等文獻語焉不詳,記載較為詳細的是大致成書于嘉靖十六年(1537)的《魯府招》,曰:“洪武十八年,分封魯王兗州府之國,設有兗州護衛、兗州左護衛,各原額旗軍六千五百五十八名,儀衛司六,典仗所原額校尉六百二十名,每名月支糧一石。”[注]《魯府招》,《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30冊,第35頁。據《魯府招》記載:“永樂五年,將兗州左護衛官軍改調濟寧左衛,屯田子粒隨收該州廣豐倉,聽候支用。”魯藩兩支護衛軍可謂規模龐大。永樂五年,兗州左護衛先被調走,成立濟寧左衛[注]《魯府招》,《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30冊,第36,36頁。,《臨清州志》記載了濟寧左衛調到臨清衛前的旗軍數量,可以反映濟寧左衛的一些情況,如下表:

表3 濟寧左衛五所運軍比重情況表[注]康熙《臨清州志》卷3《兵防》。按:筆者所見方志等文獻中僅康熙《臨清州志》有關于“濟寧左衛”軍額記載。《中國方志集成》,《善本方志輯》第一編第27冊,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664頁。 單位:人
資料來源:康熙《臨清州志》卷3《兵防》。
表3反映出濟寧左衛設有運軍,運軍占旗軍總數的大部分,濟寧左衛應屬漕運衛所范疇[注]按:嘉靖《漕運通志》不見濟寧左衛的記載,因為景泰元年其全部被調到臨清衛,成為臨清衛的一部分。,且濟寧左衛有屬其管理的一段河道[注]弘治《漕河圖志》曰:“嘉祥縣,在漕河之西二十五里,該管河岸,北自汶上縣界之界首起,南至巨野縣界大長溝止,長一十八里,原系濟寧左衛管。”王瓊:《漕河圖志》卷1,姚漢源、譚徐明點校:《中國水利古籍叢刊》,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90年,第38頁。。可見,兗州左護衛一支全部調到濟寧左衛,護衛軍參與到了漕運體系中,不再受魯王的約束。正統年間土木堡之變,臨清為兩京往來交會咽喉之地,需要加強守御,景泰元年(1450)便將濟寧左衛調到臨清衛[注]王直:《修城記》,嘉靖《山東通志》卷12,第772—773頁。“正統十四年秋,虜寇侵犯邊,鄙京師戒嚴,畿甸以及山東河南諸郡俱有城池,以貯重兵保障人民,拱衛國家,獨臨清為兩京往來交會咽喉之地……同理其事陳公名豫……乃請于朝建臨清衛,調濟寧左衛五所,并原守御臨清千戶所官軍俱隸于此,而制守御之器。”,據《魯府招》記載:景泰一年(1450)將濟寧左衛官軍改調臨清衛,屯田子粒該衛委管屯指揮征收,仍在前倉上納[注]《魯府招》,《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30冊,第36,36頁。。原濟寧左衛的屯田子粒由臨清衛管屯指揮征收,在臨清廣盈倉上納,同時濟寧左衛運軍也調到臨清衛,具體情況見下表:
據表4分析,所調濟寧左衛的運軍占臨清衛運軍總數的81.1%,可以推測,鎮守臨清平江侯陳豫以正統己巳之變為契機,調濟寧左衛于臨清衛,補充臨清衛的運軍數量也是重要考量。盡管兗州左護衛調到濟寧左衛又被調到臨清衛,但兗州左護衛的兩次調動也比較徹底。

表4 所調濟寧左衛運軍占臨清衛運軍總數比重情況表[注]康熙《臨清州志》卷3《兵防》,第664頁。按:嘉靖《山東通志》和萬歷《東昌府志》所載臨清衛的旗軍額不同,但運軍數量均為2665人,一定程度可以看到景泰元年所調運軍所占比重。 單位:人
資料來源:康熙《臨清州志》卷3《兵防》。
原魯藩兩支護衛軍僅留兗州護衛一支,此支護衛軍的調撥則比較復雜,從永樂年間開始到正統年間,主要以“借調”的形式參與漕運。明實錄記載了兗州護衛最早被調運糧的情況:
山東都司舊調兗州護衛旗軍一千三百人運糧,宣德元年,魯府奏留修理王府,本司以登、萊、寧海、膠州四衛所旗軍撥補,緣俱近海路遠來遲,況其軍士不諳水運,往往誤事。[注]《明宣宗實錄》卷64,“宣德五年三月辛丑”,第1525頁。
魯藩護衛軍設立之初,受到藩王的控制,永樂年間,山東都司調1300名兗州護衛旗軍運輸漕糧,約為兗州護衛原額的五分之一,宣德元年,魯府奏留護衛軍“修理王府”,表明永樂年間參與漕運的兗州護衛軍只是被山東都司“借調”,魯王仍然具有管理護衛的權力,而宣德五年,陳瑄又提議將宣德元年(1426)魯王奏留的護衛軍用來運糧。多次調遣兗州護衛軍充當運軍,不免觸動藩王的利益,宣德八年(1433)魯王妃薨,王府也以修造工程等為緣由,奏留護衛軍在王府供役差使[注]《明宣宗實錄》卷108,“宣德九年春正月己卯”,第2426頁。“魯王肇煇奏,今造墳及享堂,請免護衛軍士運糧、屯田者,以助役,從之。”。但正統十三年(1448)春,朝廷又重提調魯府護衛軍,用以運輸漕糧。據實錄記載:
先是魯王肇煇妃薨,奏留護衛運糧軍造墳,朝廷允其請命,于濟寧等衛所撥軍補運。至是墳已久完,各衛屢訴差役繁重,且平山、東昌衛,達官數多,乞量存軍守備,仍以護衛軍儧運,從之。[注]《明英宗實錄》卷162,“正統十三年春正月戊子”,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3151頁。
正統十三年,離魯府奏留運糧護衛軍的時間已有15年,魯王妃的墳墓早已修好,朝廷認為不應該再將護衛軍留在魯府,加之濟寧等補運的衛所差役繁重,土木堡之變后,平山衛和東昌衛安插的達官數量較多,更需要軍隊來駐防,權衡之后,重新將奏留魯府的兗州護衛軍儧運漕糧。同年夏,朝廷再次下令強調此事[注]《明英宗實錄》卷165,“正統十三年夏四月丙辰”,第3194頁。“命魯府護衛原撥運糧旗軍,并工修造王府房屋城垣,候明年仍舊儧運糧儲,其屯田軍余,仍舊屯種辦納子粒。”。
由此,從永樂年間最初的調兗州護衛軍運輸漕糧,到宣德元年魯府奏留這批運糧軍修建王府,一直到正統十四年(1449),這樣的反復“爭奪”(奏留與撥運)上演了三次。之后,魯府兗州護衛軍不斷地被調作他用。同濟寧左衛一樣,正統十四年,兵部借“己巳之變”之名,調魯府兗州護衛軍500名到臨清衛,聽從平江伯陳豫提督統領[注]《明英宗實錄》卷189,“廢景泰元年二月丙子”,第3864頁。“(兵部)奏近有自虜中還者,言也先聽從喜寧奸計,欲往臨清搶掠,宜敕魯府兗州護衛調官軍五百赴臨清,聽平江伯陳豫等提督摻練,俱從之。”。兗州護衛軍在參與運輸漕糧與魯府奏留之間不斷反復,一定程度上表明這個時期護衛運軍還受到魯王的控制,但控制力在減弱。直到嘉靖初年,兗州護衛運軍的數額固定化,成為山東總下漕運衛所之一。據嘉靖《漕運通志》記載:兗州護衛有額定運軍600名,淺船60只,每年需要造船6只,額運漕糧約18 421石[注]楊宏、謝純:《漕運通志》,第90頁。“兗州護衛,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旗軍六百名,淺船六十只,每年該造六只,運糧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一石二斗。”,設“治漕艎廠”即衛廠,運軍和衛廠都總隸于督漕御史管轄[注]嘉靖《山東通志》卷13《漕河》,第813頁。。與此同時,這600名運軍仍然屬于魯府兗州“實在護衛旗軍”中。據《魯府招》記載:
查得兗州護衛旗軍,實在二千六百六十四名,除漕運及臨清操備一千一百名外,其余一千五百六十四名,并余丁八千六百十五名,俱在本府私令辦納錢物。[注]《魯府招》,《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30冊,第52頁。又《魯府招》記載:“比兗州護衛官軍除逃亡事故外,實在二千六百六十四名,內除運糧六百名,臨清操備兩班五百名,其余俱在本府辦納銀錢役。”第36頁。
材料顯示,參與漕運的600名護衛軍和調到臨清操備的500名護衛軍,包括在2664名兗州護衛旗軍中,仍屬于魯王府。所不同的是,這1100名護衛軍不需向魯王府交納錢物和服役。但魯王府仍然覬覦于有運糧和操備任務的護衛軍軍余,據《魯府招》記載:
(嘉靖九年)王準信將前守城實操余丁,并供給生員及丁及漕運、操備貼丁,一概拘收,入府占用,及辦納銀錢,多寡不等。[注]《魯府招》,《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30冊,第59頁。
秦信是嘉靖初年魯府典膳使,也是《魯府招》所記審理案件中的“招首”,即主要罪犯。本來兗州護衛運軍無需在魯府服役納錢,但在秦信的“撥置”下,守城軍余、漕運和操備貼丁全部被納入王府,辦納銀錢。可見,嘉靖初年魯王依然可以占用兗州護衛運軍軍余。
綜上,從永樂年間到嘉靖初年,魯府兗州左護衛這一支經歷了徹底的改調,即調設濟寧左衛,再調到臨清衛成為其一部分,所調護衛軍主要承擔運軍的職能,隸屬于山東總,受漕運總兵官統轄;而魯府兗州護衛這一支,永樂年間開始以藩王護衛軍的身份“借調”運糧,在朝廷“調撥”與魯王“奏留”間,藩王護衛運糧軍受到魯王和漕運總兵的雙重節制,遲至嘉靖初年,兗州護衛才有固定的運軍額數,成為漕運衛所,規定運軍無需再向王府納錢糧,實際上卻常被王府占用。
直到嘉靖十八年(1539),朝廷將兗州護衛改設任城衛,任城衛只屬山東都司,兗州護衛在制度規定層面脫離了魯府統轄,原來兗州護衛的運軍也只由山東總把總統轄,但實際上仍與魯府牽連不斷。
三、分改衛所:明代中后期魯藩護衛軍的安置與轉變趨勢
上文提到,魯府兗州護衛的調動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從永樂年間“借調”運糧,到嘉靖年間成為有額定運軍的漕運衛所。嘉靖十八年,是兗州護衛的最后一次調撥。據萬歷《兗州府志》記載,“任城衛,在府治東南,洪武中為魯府署護衛,嘉靖十八年奉例分改任城衛,守府城池”[注]《兗州府志》卷32《武衛部·兵防》,《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55冊,上海:上海書店,第544頁。,嘉靖十八年,兗州護衛分改任城衛,位于兗州府治東南,屬同城調動,除留下2000軍余在魯府,其余軍丁“收充衛所正軍”,全部改建任城衛,直接隸屬于山東都司統轄[注]楊博:《覆山東撫按官霍冀等請敕魯王退還護衛軍疏》,《楊襄毅公本兵疏議》卷20,《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7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萬歷十四年影印本,第588頁。“議得山東魯府護衛軍余原奉欽,依止留二千,其余軍丁改建任城衛,徑隸屬都司統轄”。。這實際上是削掉兗州護衛軍,來建立一個新的衛所,為什么要調兗州護衛在同一個府城建立新衛所?兗州護衛這一漕運衛所中的運軍如何處理?建立之后與魯王府的關系如何?值得追問。
“任城衛,守府城池”[注]《兗州府志》卷32,第544頁。,透露出任城衛的建立可能與守護兗州府城池相關。藩王護衛軍在明初設立之時,是藩王掌握的軍事力量,與都司、州縣互不參與對方的事務,無守護兗州府城池的職責。但當兗州府城缺少衛所守城軍時,朝廷便開始考慮調用藩王護衛軍。正德四年(1509),在山東巡按御史孫恭的推動下,護衛軍守城之事,得到了皇帝批準:
兗州護衛官軍及舍余余丁,除額設侍衛之外,數多空閑,乞編修立隊伍,防守城池。兵部覆議,宜令恭查選精壯,責令該衛官操練,都司管操官提督,分守、分巡官稽考……詔是之,仍行天下有護衛所在,俱從御史閱視。[注]《明武宗實錄》卷55,“正德四年閏九月庚申”,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1246—1247頁。
清軍御史孫恭提議將兗州護衛官軍和舍余余丁,編立成隊伍,用來防守兗州府城池。兵部決定由孫恭選出精壯的護衛軍,令兗州護衛軍官領導操練,都司管操官提督,分守、分廵官員負責稽考,“俱從御史閱視”。值得注意的是,兵部復議后得到了皇帝的準許,并將在兗州府實行的該政策推行到“天下有護衛所在”。實際上,此方案確在其他藩府推行。正德十一年(1516),時任欽差湖廣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督御史秦金在湖廣推行該法,令楚藩武昌護衛軍守城。其奏曰:
照得湖廣省城設有武昌衛、武昌左衛,官軍操練保障。其武昌護衛專屬楚府護守王國,平時既無統攝之司,遇警又無協濟之力,酌量事體,甚非所宜 ……合無將武昌護衛官舍軍余,照舊查選一千員名,與武、左二衛官軍舍余,相兼操守,具聽考選城操都指揮號令約束,隨時訓練,遇警并力防剿。[注]秦金:《安楚錄》卷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46冊,濟南:齊魯出版社,1996年,第418頁。
宣德年間,楚藩調走兩支護衛軍后,留武昌護衛一支軍隊“專一防護王國”。正德七年(1512),湖廣遭流賊劫掠,調武昌護衛旗軍1000多名,防守城池,但只是暫時性的調撥,等賊亂平息,又還歸楚藩。正德十一年,督御史秦金試圖將護衛軍守城設為定例,并推廣到“凡有護衛并儀衛司去處”。具體辦法是從武昌護衛官舍軍余中選出一千名護衛軍,與湖廣都司下的武昌衛和武昌左衛官軍舍余一同操練守城,聽從都指揮管束,守護武昌府城,由按察司每月委官稽查②秦金:《安楚錄》卷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46冊,濟南:齊魯出版社,1996年,第418頁。。湖廣都御史秦金奏疏的方案與正德四年山東巡撫孫恭的改革精神如出一轍,反映出了明代中后期,全國藩王護衛軍的裁撤與安置趨勢,即將同府城內本專屬于藩王府的護衛軍用于守護府城池,和都司衛所守城軍一樣,聽從都指揮調遣,推動了護衛軍納入都司衛所體系的進程。
正德年間,編立護衛軍為都司統轄的守城軍是推動藩王護衛軍轉變的一次重要改革,都司、御史等逐漸介入到藩王護衛軍的管理中。從結果上看,正德四年山東御史孫恭的改革使得兗州護衛軍有了守護兗州府城池的職能,設額軍3390名,占兗州護衛軍總額的68.3%[注]嘉靖《山東通志》卷11《兵防》,第714頁。“兗州護衛,運糧軍六百人,城守軍余,三千三百九十人,屯田軍余,三百七十人。”,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兗州護衛軍納入到都司統轄體系,但是就魯藩的情況來看,孫恭改革并不徹底。兗州護衛中編立的守城軍,仍被魯王府和承奉司私自占用,嘉靖初兗州府依然面臨無衛所軍守城的困境[注]《魯府招》,《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30冊,第52頁。據《魯府招》記載:“查得兗州護衛旗軍……及各府并承奉司私自占用,委無一人守城實操,以致兗州府操守又虛,萬一賊寇生發,缺人防護城池,剿捕盜賊,貽患地方。”。兗州護衛守城軍仍然由魯王管控,這可能是山東巡撫孫恭前項改革不徹底的癥結所在。《魯府招》成書于嘉靖十六年,恰好處于兗州護衛改建任城衛的前夕,《魯府招》記載了魯府典膳使秦信的招供,透露出一些背景信息:
(秦信)撥置啟說,護衛人俱是爺爺的,豈可與他有司家守城把門,都該拘來辦錢供應……其守城實操至今廢缺,并無一人防守,以致兗城內軍民人等及府縣官員,明知城守久虛,不敢聲言,恐被信與夏宗堯等撥置兇橫,羅織辱打,至今結舌。[注]《魯府招》,《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30冊,第58—59,52頁。
嘉靖年間魯王聽從秦信撥置之言,認為兗州護衛軍是屬于魯王的,“豈可與他有司家守城把門”,于是將之前設立的運軍及貼丁和守城實操軍等拘入王府占用,辦納銀錢。這樣就導致兗州府城內沒有護衛軍防守,而城內百姓及府縣官員害怕被王府官吏秦信等人施暴,不敢聲言守城之事。為了解決此問題,針對兗州府城操軍的組織與歸屬,審理魯府案件的刑部侍郎、山東巡撫等官員,提出了進一步改革建議,據《魯府招》記載:
合無遵照祖訓內事理,將兗州護衛五所旗軍,共摘撥七百二十名,并前項金鼓手旗軍一百一十二名,共八百三十二名,坐委正副千戶各一員,百戶十員管領,專在本府宿衛……先年清軍御史孫恭奉到勘合及魯莊王批行,令旨盡數查出,編成隊伍,俱行兗州府衛掌印官督率操守,又恐頑猾之徒私投王府撥置生事,合無改隸山東都司管轄,庶事體穩便,一以保安宗室,一以屏蔽地方,兼免后患。⑥《魯府招》,《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30冊,第58—59,52頁。
為避免“頑猾之徒”投充王府等弊端,嘉靖十六年,刑部侍郎李清學等進一步提議將720名兗州護衛軍重新編立為守城實操軍,按照衛所規制,設立千戶、百戶等軍官,改由山東都司管轄,認為這樣既可以保安王府宗室,又能守護兗州地方。這項建議是對正德四年清軍御史孫恭改革的進一步的推進,在編審兗州護衛軍為守城軍的基礎上,試圖使其完全改由山東都司管轄。嘉靖十八年,這項提議便以在兗州府城內設立新的衛所——任城衛的形式實現。正如《山東觀風備覽》所記載“護衛原系全設,嘉靖十八年奉例止撥以上官員、旗軍在魯王位下守衛直宿,余俱改隸任城衛”[注]萬歷《山東觀風備覽》卷1《藩府》,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第54頁。。
為了使兗州護衛城操軍脫離魯府統轄,嘉靖十八年,朝廷將兗州護衛大部分旗軍調到城東南建立任城衛,任城衛直屬于山東都司,兗州護衛守城軍也就直屬于山東都司管轄。萬歷《兗州府志》記載了任城衛軍役情況,列表如下:

表5 萬歷初任城衛旗軍職役情況表[注]《兗州府志》卷32《武衛部·兵防》,第544、555—556頁。 單位:人
資料來源:萬歷元年(1537)《兗州府志》卷32《武衛部》。
對比發現,從兗州護衛運軍到任城衛運軍,數量一直是600名[注]嘉靖《山東通志》卷11《兵防》,第714頁。“兗州護衛,運糧軍六百人,城守軍余,三千三百九十人,屯田軍余,三百七十人。”按:嘉靖《山東通志》成書于嘉靖十二年,尚未有“任城衛”的相關記載。,可以推知,兗州護衛分改到任城衛后,運軍數量沒有變,原來兗州護衛的運軍全部改到了任城衛。此外,嘉靖七年(1528)《漕運通志》山東總下記有“兗州護衛”這一漕運衛所,但嘉靖十八年后編纂的相關文獻,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漕船志》[注]席書編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3,《淮安文獻叢刻》,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第54頁。、萬歷十年(1582)《萬歷會計錄》[注]《萬歷會計錄》卷35,《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第1096頁。、萬歷《通漕類編》[注]《通漕類編》卷2,《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443冊,第126頁。等關于漕運衛所的記載,在山東總下不再有“兗州護衛”,而是增加了“任城衛”,且運軍仍為600名,《漕船志》等文獻不記“兗州護衛”,不代表兗州護衛運糧旗軍退出漕運衛所體系,而是隨之一同改到任城衛,以任城衛所運軍的身份參與到漕運體系。在制度規定層面,任城衛本直屬于都司衛所體系,不再受到魯王府的控制,但不同于楚藩和蜀藩護衛軍的遠距離調動,兗州護衛和任城衛均位于兗州府城池內,兗州護衛在府治東,任城衛在府治東南,二者空間位置上非常靠近[注]萬歷《兗州府志》,《府境州縣圖考》,濟南:齊魯出版社,1984年。。這樣的空間格局,使得任城衛與魯藩依然糾葛不斷。據時任兵部尚書楊博奏疏記載:
議得山東魯府護衛軍余,原奉欽依止留二千,其余軍丁改建任城衛,徑隸屬都司統轄。邇來宗室生齒日繁,占役軍從過多,以致衛名徒存,軍伍久廢。欲要賜敕魯王嚴諭,各宗將役占、投充軍從,盡行退回,守巡該道將該衛見在軍丁及退回軍從,查明造冊,撥補運糧、操守,敢有不行首正及撥置奏擾者,俱行拏問,干礙輔導等官,一并參治。[注]楊博:《覆山東撫按官霍冀等請敕魯王退還護衛軍疏》,《楊襄毅公本兵疏議》卷20,《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77冊,第588頁。
朝廷調兗州護衛改立任城衛,本是希望兗州護衛守城軍余等能徹底脫離王府的管理體制,守護有司城池,可是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左右,距改任城衛已有十七年,魯藩宗室生齒日繁,留下的2000護衛軍已經不能滿足王府的需求,王府宗室仍然占役任城衛軍并接納投充王府的軍余,導致“(任城衛)衛名徒存,軍伍久廢”。相較于兗州護衛,任城衛在制度規定層面已脫離了魯王府控制,隸屬于山東都司,但實際上,遲至嘉靖四十五年,改調到任城衛的護衛軍(包括運軍)一直未擺脫魯王府的役占。這也是魯藩護衛與楚藩、蜀藩護衛調動后所建漕運衛所的不同之處。為解決此問題,時任兵部尚書的楊博提議,令魯王將王府各宗室役占、投充軍從退回任城衛,分守、分廵官將退回的軍從和任城衛見任軍丁,登記在冊,撥補運糧、操守,并重新按照宗室品級撥給其固定隨從人員,允許出錢代役,削弱了藩府對護衛軍的控制[注]楊博:《覆山東撫按官霍冀等請敕魯王退還護衛軍疏》,《楊襄毅公本兵疏議》卷20,《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77冊,第588頁。。值得注意的是,任城衛的運軍可能被王府役占,也可能為了逃避漕運差役,主動投充王府,王府與任城衛同城,這種長期的聯系,使得任城衛運軍生計選擇多樣化。
明代中后期,兗州府城面臨缺乏城操軍的局面,正德四年在山東御史孫恭的推動下,山東都司、巡撫等官員介入對兗州護衛軍及軍余的管理,將其編立為守城護衛軍,但此改革并不徹底,城操軍仍屬于兗州護衛軍官的管轄,受魯藩牽制。為保證府城有足夠多的守城護衛軍,使其脫離魯王府的統轄,嘉靖十八年朝廷調兗州護衛在同城建立任城衛。在制度規定層面,任城衛完全隸屬于山東都司,隨著任城衛的設立,原來兗州護衛運糧軍也調到任城,以任城衛運軍的身份承擔運糧任務,受漕運總督的統轄。但是與徹底改調的楚府護衛不同,兗州護衛與任城衛同處一城,運軍或受魯王府占用或私自投充王府,嘉靖四十五年山東巡撫等仍在請命朝廷令魯王退還護衛運糧軍。
結 語
本文旨在探究明代藩王護衛軍與漕運衛所的關系,以護衛軍為切入點考察削藩政策的具體實施過程,探究在明代都司衛所體制下存在的藩王、漕運總兵等多重軍隊統轄關系與國家軍隊調撥與安置方式。明代漕運衛所并非全部是洪武朱元璋建立的都司衛所,藩王護衛軍也是漕運衛所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被納入到漕運體系中。考察漕運衛所中的藩王護衛軍,是理解漕運衛所體系的復雜性與特質性的重要切入點。楚藩和蜀藩護衛軍在明宣宗削藩背景下,被徹底地調往徐州、東昌和南京,在運河沿線建立徐州左衛、東昌衛、豹韜左衛和龍虎左衛,所調護衛軍大部分充當運軍,補充了運河沿線衛所的運軍數量,與楚藩和蜀藩不再有牽連,受漕運總兵統轄。
但相比之下,魯王府兩支護衛軍調撥與借調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早在永樂五年兗州左護衛被調到濟寧左衛,景泰元年改調臨清衛,這個過程也是比較徹底的。兗州護衛的調動則比較復雜,其調立原因、統轄方式、參與漕運的方式和調后與王府的關系等,反映出與一般漕運衛所的不同。就所調兗州護衛軍的統轄方式而言,并非由漕運總兵單一統轄,一直與魯王府存在著聯系。永樂到正統年間,兗州護衛軍是以藩王護衛軍的身份被“借調”運糧;后兗州護衛逐漸有固定的運軍額數,遲至嘉靖七年成為山東總下的漕運衛所,呈現出了受漕運總兵與魯王雙重統轄的狀態,兗州護衛運糧軍仍屬護衛“見在旗軍”;一直到嘉靖十八年,兗州護衛分改任城衛,運軍隨之改調任城衛,以任城衛運軍身份參與漕運,兗州護衛雖然在制度層面屬山東都司管轄,運軍實際上或受魯府役占,或投充王府。一方面,將藩王護衛軍改調漕運衛所和同城分立衛所是明王朝裁撤藩王護衛軍后的兩種安置方式,亦是削藩政策的具體實施過程。另一方面,從長時段看,楚藩、蜀藩和魯藩護衛軍的變遷又呈現出共同的趨勢,即護衛軍最終均某種程度上納入都司衛所統轄下。如果說宣德年間將削藩政策及所裁護衛軍安置問題與國家面臨漕運軍隊缺乏的局面相結合,護衛軍被納入漕運衛所體系;至明代中后期,當府州縣面臨城操軍不足的問題,將護衛軍同城分立衛所亦為此政策題中之意。總之,魯藩護衛軍在調為漕運衛所運軍過程中,與楚藩和蜀藩護衛軍,呈現出了不同的模式與統轄關系,既體現了漕運衛所與藩王護衛的復雜關系及漕運衛所的特質,又反映了明代皇帝對藩王的態度與政治策略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