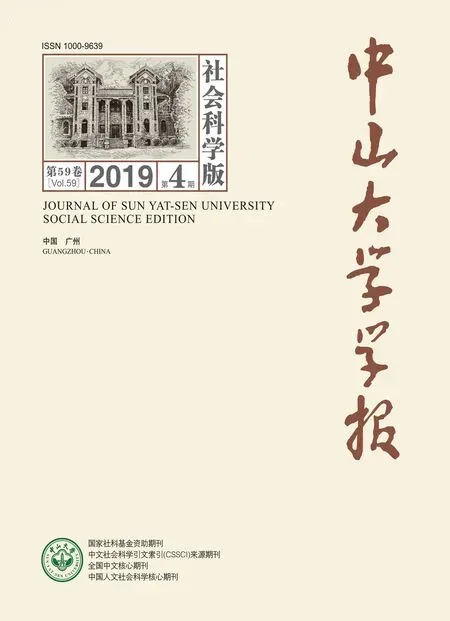把握“脫虛向實”力度*
——房地產與實體經濟的風險傳染機制研究
楊海生, 楊禎奕
一、引 言
從2012年開始我國經濟結束近20年10%的高速增長,轉而進入增速換檔期,進入 “新常態”。如何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保持經濟結構的合理發展,實現“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保障實體經濟的增長是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重要問題。
從1998年7月的“房改”將住房分配制度轉變為市場化制度至今約20年,房地產在我國經濟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房地產投資占總投資的比例從1998年的7%左右提升到2016年的17.8%,房地產貸款占金融機構總貸款比例到2017年末達到35%,房地產企業利潤率2017年達到12%左右,是工業企業的一倍。如今,房地產已經逐漸區別于建筑行業,不單單具有實體經濟的特征,其資本化的定價方式與投資品的特征也已經使之成為虛擬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蘇治等,2017;黃群慧,2017;王千,2006;彭俞超等,2018)[注]由于房地產也具有較長的產業鏈條,且居民對房地產的投資也是有著貨幣乘數效應的,放大的貨幣量流入到各行各業中,房地產是否為虛擬經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因此,我們在第二部分文獻綜述處加入對房地產虛擬性的討論。。2008年房產泡沫的破裂、金融危機的爆發也充分證實了房地產的虛擬性。2015年11月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補”中的“去杠桿”,“降成本”,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于房地產部門的杠桿和由此拉高的資金成本。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穩中求進,‘脫虛向實’,將資金從房地產或者金融部門有效地引導到實體經濟部門”。可見,房地產的虛擬性已經被學界和政策制定者所肯定,且其虛擬性正是其風險的主要來源。深入分析房地產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對當前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然而,要實現“脫虛向實”,簡單地將資金從房地產抽離到實體經濟部門就可以實現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嗎?重拳打壓房地產市場、造成房地產行業劇烈的波動就能夠讓資金轉移到實體經濟部門嗎?反之,實體經濟的增速下降、風險加大是否會使資金更多地轉移到房地產部門呢?基于以上問題,本文構建雙元VAR的GARCH-in-Mean模型,首次將增長速度和風險強度同時納入分析框架,并探究了其中的金融傳導機制,且從短期沖擊到長期動態溢出效應的角度分析并揭示了房地產波動的風險驅動力及其與政策周期的聯結,得出在“脫虛向實”中不應冒進,應著力先從供給側提高實體經濟水平的結論。
本文的主要貢獻有三方面:第一,以往的文獻忽略了風險對增長直接的影響。本文將風險因素直接引入到均值方程中,同時分析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增長和風險因素對彼此增長的直接影響。第二,本文把房地產、金融信貸部門和實體經濟三者同時納入一個框架,考慮了金融部門的風險傳導作用。第三,本文從短期沖擊和長期動態均衡角度發現房地產既是實體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也是風險的來源點,而且其風險溢出效應與房地產調控的政策周期之間具有同周期。
文章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關于房地產的虛擬性、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發展的關系、影響機制和溢出效應的研究文獻綜述;第三部分是變量選取和模型設定;第四部分為實證結果及分析;最后是結論以及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一)房地產的虛擬性
首先,根據虛擬經濟的定義,蘇治等(2017)和黃群慧(2017)等認為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最大的區別在于其主要由心理預期支撐的、資本化的定價方式。這種定價方式決定了虛擬經濟是單純地依靠資本利得,不必經過實體經濟的物質轉換。相比于依照成本定價的實體經濟,房地產業兼具了依照心理支撐的定價系統和成本支撐的定價系統兩種特性。王千(2006)則從房地產的不動產效應、投資品屬性、融資方式、證券化以及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因素的聯系減弱等多個方面闡述了房地產的虛擬性。黃群慧(2017)認為,房地產呈現的主要是金融衍生品的特征,且其涉及到實體經濟的部分已經包含在建筑業中,因此房地產業和金融業合并組成了區別于其他實體經濟行業的虛擬經濟。孟憲春等(2018)也指出在我國主要依賴間接融資的背景下,房地產作為抵押品和投資品的屬性使其價格逐漸脫離成本化的定價,成為一種虛擬資產。
誠然,房地產投資確實有一部分與建筑業相聯系,是具有實體經濟特征的。但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我國經濟“三大失衡”中指出:“房地產本來屬于實體經濟,但用加杠桿的辦法進行房地產投機就不同了”。由于實體經濟面臨結構性的失衡,利潤率較低,而經濟增長、財政收入、銀行利潤越來越依賴于“房地產繁榮”,大量的資金通過加杠桿的方式進入房地產市場,投機動機高漲,使資金“脫實向虛”。 由于我國房地產開發企業的杠桿率較高(2017年末上市房地產公司杠桿率為79.08%[注]根據wind數據庫計算。),高企的房地產投資杠桿使得房地產具有了投機的性質,也就出現了虛擬資產的特征。另外,2016 年我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共施工75.90億平方米,竣工10.61億平方米,但商品房銷售僅為15.73億平方米,占 20.7%[注]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我國的二級市場房價高企,但住房空置率很高(2017年我國城鎮地區住房空置率為21.4%[注]數據來源: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CHFS)發布的《2017中國城鎮住房空置分析》。),說明很大一部分的房地產開發已經變成了一種單純的資本品投資或炒作活動而非滿足生產生活的需要。這都反映了房地產投資的投機性和虛擬性。
再者,從定量上,蘇治等(2017)將房地產作為衡量虛擬經濟的四個主要指標之一。他們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發現,中國虛擬經濟規模主要由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決定。還發現房地產業對虛擬經濟沖擊的脈沖響應幅度最大,并呈現明顯的持續性和周期性,他們認為這種現象可以“從側面體現出房地產的虛擬性,以及虛擬經濟自我循環膨脹的特征”。 因此也佐證了房地產具有較強的虛擬經濟的特征這一觀點。
綜上所述,我們根據學界的定義和分析以及政策制定者的界定,并結合中國實際數據,從定性和定量角度論證了房地產的虛擬性。我們認為它是虛擬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房地產與實體經濟發展的關系
目前,對于房地產與實體經濟的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方向。研究實體經濟發展對房地產影響的文獻基本都得出相似的結論,即實體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更多文獻關注的則是房地產對實體經濟增長的影響,但這些文獻卻得到了相悖的結論。其中一方認為,房地產占用了過多的資源,不僅綁架了實體經濟,還阻礙了實體經濟的發展。Miao & Wang(2014)基于兩部門內生增長模型,發現資產泡沫具有明顯的再分配效應。實體經濟部門向有泡沫的部門轉移投資,同時金融部門也會給予房地產部門更多信貸支持,進一步擠出實體經濟投資。房地產業的過度投資加大了房地產泡沫,而房地產泡沫又進一步地刺激了房地產投資,這種惡性循環顯著地抑制了實體經濟投資。而另一方則認為房地產作為經濟中重要的一環,它的投資對拉動實體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如,唐志軍等(2010)發現當房地產投資額增長率上升1%,GDP 增長率上升0.181%。更進一步地,Farhi & Tirole(2012)認為房地產作為一種抵押品,能使得企業獲得更多外部融資,從而使投資“擠入”實體經濟部門。當企業擁有的房屋價格上漲時,其投資會顯著增加,總體經濟也會增長。
同樣,房地產的風險與經濟風險也有很強的關系。比如Green(1997)區分了住宅投資和非住宅投資波動對 GDP 的影響,發現前者的波動風險放大了國民經濟的波動風險而后者則更多地是受到國民經濟波動風險的影響。我們也承認房地產與實體經濟之間具有較強的內生關系,且這種關系既存在于短期也存在于長期,因此需要把兩者納入同一框架下進行研究。但是現有文獻忽略了兩部門間一方的發展中就直接包含了另一方的風險因素,即一旦一個部門有較大的波動或者結構性的調整,另一個部門的發展方向就會直接受到影響,而非只是單純的波動變化,因而低估了相互之間的風險傳染力度,低估了相關政策實施時產生的沖擊。我們認為房地產不僅在增長率上與實體經濟的增長率具有相關性,它們各自的風險也會影響另一方的增長率。
其次,我們還探究了房地產與實體經濟間增長率和風險的金融傳導機制。以往文獻從模型和實證角度都闡述了銀行信貸對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的影響(趙勝民等,2011)。但基本都是分開研究房地產與金融或實體經濟與金融的關系,沒有把三者同時納入一個框架并分析其中的風險傳染機制。另外,我們還認為它們兩者對金融部門增長或者風險的影響很可能是不同的,而正是這種不同導致了它們的地位是不同的。
最后,現有文獻大多都集中在VAR方差分解的框架下研究短期的脈沖影響(如唐志軍等,2010),或者研究長期的均衡關系,卻沒有考慮到長期的均衡關系也可能根據經濟周期、政策周期等不同而發生結構性的變化。本文利用廣義脈沖響應函數、方差脈沖響應函數和基于Diebold和Yilmaz(2009)的動態溢出效應分析,為我們的VAR框架下的 GARCH-in-Mean模型加上了時間維度的分析,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在房地產市場化改革20年來,它與實體經濟之間在增長和風險、短期和長期方面到底存在怎樣的關系,以及政策周期對兩者關系的影響。
三、變量選取及模型設定
(一)變量選取
本文選用房地產投資來衡量房地產業的發展。我們選用房地產投資作為衡量房地產業發展情況的指標是因為投資是當前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投資不當也是造成許多其他問題的根源(李揚和張曉晶,2015)。而其中,房地產投資是中國投資及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但也是誘發相關行業投資“過度”與產能“過剩”的深刻原因。參照以上邏輯,我們認為房地產過度開發投資是驅動房地產業投機性及虛擬性等相關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可以選用它來作為反映房地產的虛擬性特征及引致房地產行業其他問題的基礎指標(張曉晶和孫濤,2006)。房地產投資的驅動作用也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得到證實(結果備索)。
具體地,我們選用月度的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額(累計值)計算得出的月度房地產開發新增投資額[注]根據統計核算規則,統計局只公布2—12月的累計投資額,因此將2月的累計投資額進行平均作為1月和2月的新增投資。。現有文獻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額都普遍被使用作為分析房地產業發展情況的主要指標(梁云芳等,2006)。盡管其有一定的提前計劃性,但文章中使用的新增額已去掉了部分提前計劃的維持性投資,且該指標是根據當月的實際情況調整的實際完成額,包含當期決策因素。另外,本文關注的是房地產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后文模型中控制的滯后項在一定程度上已考慮了“預期及計劃”的影響[注]我們仍然選用了當期土地成交價款和土地購置費用兩個指標做了穩健性檢驗,發現結果及所得結論與原結果基本一致(結果備索)。但是由于土地交易仍受到政府和政策的頗多約束,且土地的招標、拍賣、掛牌和協議方式出讓等過程更加依賴于長期以來的計劃、競拍、協商等,具有很強的計劃性和預期性,也無法反映當期的決策情況。因此,我們仍然選用房地產開發投資作為衡量每月房地產業發展情況的指標。此外,根據審稿人的建議,我們對該指標中的預期因素進行扣除,發現結果仍是一致且穩健的,結果備索 。。參照張曉晶和孫濤(2006)和張勇(2015),從房地產需求端考慮,用以1998年1月為基期的居住類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平減,得到實際值。我們認為,相比于受到限價政策影響的房價而言,居住類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更能反映實際的房市繁榮情況和房地產消費需求情況。而相比于生產者價格指數,房地產投資中受到心理預期及其他投資品價格影響的部分更能被消費價格指數反映。Liu et al. (1997)也指出房地產投資是一種對抗通脹的保值性投資,它可能更依賴于消費的價格而非生產者價格[注]為排除由于價格指數選用所致的結果差異的可能性,我們也從供給端考慮,用以1998年1月為基期的月度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對新增房地產開發投資進行平減,得到的模型估計結果以及結論與原文一致。限于篇幅原因,結果備索。。1998—1999年的房地產投資數據來源于東方財富Choice數據庫[注]數據來源:http://data.eastmoney.com/cjsj/hyzs_EMI00120219.html。,2000—2017年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
參考何青等(2018)和黃群慧(2017),我們選用月度的實際工業增加值作為衡量實體經濟增長的指標。這里,我們不研究工業投資額是因為本文更關注實體經濟的發展情況,而不是投入量,投入量可能出現很多失效的部分;另外,工業部門的投資和房地產的投資具有很強的共線性,難以辨別出相互影響。參考張勇(2015),我們推算出2007年以后的月度工業增加值,并用以1998年1月為基期的PPI進行平減,得到實際值。樣本期為1998年1月至2017年12月,旨在分析“房改”后20年房地產業的投資與中國實體經濟的增長及風險間的關系。
我們對以上數據進行了X12季節調整,并以兩部門對數差分的增長率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放入模型中估計。表1中為描述性統計。我們進一步對兩序列做了平穩性、自相關性和異方差性檢驗,發現它們為平穩的、有自相關和異方差性[注]由于篇幅原因,結果備索。。

表1 描述統計
注:方括號內的數值是p值,下同;顯著性水平分別為***p<0.001,**p<0.05,*p<0.1,下同。
(二)模型設定
根據數據具有的自相關和異方差特征,以及波動性在本文研究中的重要性,我們采用Engle et al.(1987)的GARCH-in-Mean模型來分析房地產投資和實體經濟增長的均值和方差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具體設定如下:
均值方程:
(1)

(2)

基準模型考察的重點有兩個:第一,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即系數矩陣Γj,j=1,…,p的顯著性與符號;第二,房地產與實體經濟波動對均值水平的影響,即Ψ的顯著性與符號。我們對模型設定的有效性進行了檢驗,發現該模型是有效的,限于篇幅原因,結果從略。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基準模型結果
我們對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增長率的GARCH-in-Mean模型進行了QML估計,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結論1:房地產投資增長推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但實體經濟增長對房地產投資的作用并不明顯。

表2 房地產和實體經濟GARCH-in-Mean 模型的實證結果


方差方程結果:矩陣元素CAB110.015***0.180***0.394***[0.000][0.000][0.000]120-0.154***0.080***[0.000][0.003]210.000***-1.062***-0.297***[0.155][0.001][0.000]220.000***1.865***-0.321***[1.000][0.000][0.000]
注:方括號內為P值;***、**和*分別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顯著。
從上述兩點發現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不管是房地產業還是實體經濟,風險對自身和對方的增長都具有非常顯著的影響。其中,房地產既是實體經濟風險加大時的投資替代品,又是實體經濟衰退的風險來源,它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增長有著確實與顯著的擠出效應以及風險約束效應。與此相反,我國實體經濟的增長背后也蘊含了高波動,具有一定的脆弱性,而且其對房地產業波動很敏感。此外,上述發現還表明,我國房地產風險的影響力度要明顯強于實體經濟風險的影響力度,這也呼應了上文的結論1。總結以上分析,我們得出:
結論2:房地產投資風險對實體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而實體經濟風險加大會提高房地產投資。
(二)金融傳導機制
由前文得到的不對稱的風險傳染機制,我們猜想其出現的原因在于資金更偏好房地產。在實體經濟不穩定時,資金會轉向于投資房地產等固定資產;而房地產風險加劇時,由于房地產通常是實體部門的企業最重要的信貸抵押品,由此導致的信貸資金風險加大會遏制實體經濟的發展,而且被房地產風險擠出的資金也不會向利潤率低的實體經濟部門轉移。
為了驗證這一猜想,我們選取月度銀行貸款余額來衡量金融部門的信貸情況。本來應該用每月銀行貸款增量作為信貸的衡量,但是由于銀行貸款增量存在很多負值,即銀行信貸規模會下降,無法進行X12的季節調整,因此我們采用銀行貸款余額作為衡量金融發展的指標。由于最后我們使用的也是一個增長率指標,銀行貸款余額的增長率變化趨勢與銀行貸款增量的增長率變化趨勢差異不大。數據來源于中經網宏觀數據庫,參照張勇(2015)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進行平減得到以1998年1月為基期的每月實際銀行貸款余額。參照前文我們對銀行信貸量進行了季節調整并計算每月增長率,然后做了單位根檢驗、自相關檢驗和異方差檢驗,發現其為具有顯著自相關和異方差的平穩過程。
根據Frankel & Romer(1999),雙元簡約模型(reduced-form)是最直觀且穩定的結構,更多變量的引入不僅無助于對結構穩定性的改進,反而可能因分化吸收原有變量的解釋力而導致對這兩個變量相關性的低估。因此,為了研究金融部門在影響房地產和實體經濟關系中所起的作用,我們分別分析了“房地產——金融部門——實體經濟”這一傳導機制的每個環節上的一對變量來構建雙元VAR的簡約模型,并沿用之前的GARCH-in-Mean模型(楊海生等,2014)。鑒于篇幅限制,房地產與金融、實體經濟與金融的具體回歸結果從略。表3匯總了上一部分我們得到的一般性結論和這一部分得到的金融傳導機制的估計結果,其中加粗的為在10%顯著性水平以上顯著的影響渠道。我們主要有三個重要的發現:
第一,在一般性結論中,我們發現房地產投資的增長對實體經濟的增長具有顯著作用,但是這一作用渠道并不通過金融渠道來傳導,而實體經濟則會通過促進金融業的發展然后帶動房地產部門的增長。這說明房地產更多的是資金的最終流向,而非能增加實體經濟信貸的部門。
式中,GWP的單位為t·hm-2;T為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I為CH4或N2O在百年尺度下的全球增溫潛勢,分別為CO2的25倍和265倍(IPCC,2013)。
第二,在一般性結論中,房地產風險增加會抑制實體經濟增長,其金融傳導機制主要為房地產短期風險的增加會加大金融部門的風險,而加大的金融風險則顯著地抑制了實體經濟的增長,說明房地產是通過影響金融行業的風險進而抑制了實體經濟的增長。房地產投資的波動增大說明了房地產市場的不確定或者相關政策的不確定,根據房地產作為一種重要的信貸抵押品的性質,它的風險加大導致了實體企業的抵押品價值波動上升,金融部門的信貸不確定性加大。根據胡奕明等(2017),金融風險的加大會使銀行收縮信貸,從而對實體經濟產生負向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于實體經濟的利潤率比房地產投資的利潤率低,資金轉移進入實體經濟的量也不會很大。這一發現說明盡管長期來看,房地產投資增長會促進實體經濟增長,但是它的風險卻會通過擴大金融部門的風險,迫使銀行收縮信貸,抑制實體經濟的發展。這也說明,在經濟結構轉型和“脫虛向實”的過程中,要把握好力度速度,一味地減少房地產投資會加大其波動,而這種波動也會抑制實體經濟的發展。
第三,在一般性結論中,實體經濟風險對房地產增長的影響為正效應,這其中的金融傳導渠道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方面,實體經濟的風險促進了金融的增長,說明在實體經濟衰退的背景下,企業會加杠桿以應對危機,信貸規模會擴大,導致金融業增長。這符合優序融資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當公司風險上升時,公司內部收益不足以滿足其投資或避險需求,會優先采用成本較低的債務融資方式,因而使危機時信貸擴張。相應地,潛力和胡援成(2015)也發現,在經濟景氣時,公司盈利高、增長機會多,會更偏向選擇股權融資;經濟下行時,公司盈利降低會更多地選擇債權融資。由于房地產的利潤率總體比實體經濟的利潤率高,在實體經濟風險加劇的背景下,房地產會從實體經濟中擠出一部分的信貸資金。該結果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指出的房地產搶占實體經濟資源的問題,他指出:“房地產高收益進一步誘使資金脫實向虛,導致經濟增長、財政收入、銀行利潤越來越依賴于 ‘房地產繁榮’,并推高實體經濟成本,使回報率不高的實體經濟雪上加霜”。該結果也印證了之前文獻中金融部門對房地產部門的依賴性以及房地產發展會搶占實體經濟信貸資源的結論(蘇治等,2017;張曉晶和孫濤,2006)。另一方面,實體經濟長期風險加大也會加大金融的風險,而金融的風險加大會促進房地產業的增長,說明在金融狀況不好的情況下,資金仍然會選擇投入房地產部門,這時房地產作為一種保值品的特征就體現出來了。這與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大力發展“鐵(路)、公(路)、基(建)”的政策邏輯基本相似。這也說明我國實體經濟處于獲取金融資源的劣勢地位,其中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實體企業產能過剩、效率較低、附加值不高等導致的其利潤率遠低于房地產部門。而當前經濟發展的趨勢已經不是“金融服務實體”而是“資本先行”(李揚,2017),想要引導資金進入實體經濟,首先要做的不是打壓虛擬經濟,而是提高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和投資效率,降低金融部門的風險,然后才能將資金從房地產部門引流到實體經濟。

表3 一般性結論及金融傳導渠道:匯總結果
注:方括號內為P值;***、**和*分別表示在 1% 、5% 和 10% 的水平上顯著。
綜上,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結論3:房地產投資風險加大會增加金融風險進而抑制實體經濟的增長,而實體經濟風險會刺激金融增長并加大金融風險進而擠出資金進入房地產。
為了更清晰地展示一般性結論和金融傳導機制,我們繪制了以下影響機制圖(圖1)。

圖1 增長率及風險傳導機制圖
(三)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前文我們討論了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增長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但是得到的都是靜態的長期均衡效應,估計系數本身往往很難將兩部門受到沖擊后的持續動態反應過程真實地呈現出來。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上述的GARCH-in-Mean模型做進一步的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1.短期沖擊——廣義脈沖響應函數
借鑒Koop et al. (1996) 提出的多元非線性系統方法,我們計算了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增長率沖擊的廣義脈沖響應函數。
我們考察了房地產投資增長率的短期沖擊以及實體經濟增長率沖擊對彼此增長的影響[注]限于篇幅的限制,以及本文主要研究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對彼此的影響,因而省略了它們的沖擊對自身的影響。。從圖2中我們可以看到,相較來說,實體經濟增長率對房地產投資增長率正向沖擊的反應比較小。先在1—3個月有一個較小的上升,而后迅速消失。而房地產投資增長率對實體經濟增長沖擊的反應比較滯后,在第4—5個月時才出現明顯的上升,而在第6—7月回調50%左右,直至第9個月之后消失。說明實體經濟增長的沖擊能夠正向地促進房地產的增長,但是具有3個月左右的滯后性。總的來說,增長率上是實體經濟沖擊對房地產投資的驅動作用比較明顯。

圖2 房地產投資增長率和實體經濟增長率對彼此增長率沖擊的反應
2.短期沖擊——方差脈沖響應函數
根據劉金全(2004),經濟變量之間的影響可能發生在水平值之間,也可能發生在波動成分之間。波動成分是宏觀經濟變量相對于長期趨勢的偏離,通過對它的沖擊分析,可以探究房地產和實體經濟之間的活性,以及兩者周期的動態關聯。因此,根據Hafner & Herwartz(2006)的估計方法,我們計算了房地產投資增長率的波動成分和實體經濟增長率的波動成分對各自及互相的波動沖擊的脈沖響應函數,以反映當沖擊出現時房地產投資和實體經濟的方差協方差結構隨時間演變的路徑。
從圖3中我們可以看到,房地產投資波動沖擊對實體經濟增長率的波動成分在第2個月有明顯的放大作用,并在第3個月之后迅速消失。相較而言,實體經濟波動沖擊對房地產投資增長率的波動成分的影響微乎其微,這說明房地產投資的波動有更強的溢出能力,能夠迅速地放大實體經濟波動,但是實體經濟的波動沖擊對房地產波動的影響較小。綜上,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結論4:短期來看,實體經濟的增長沖擊對房地產投資增長的影響更大,而房地產投資的波動沖擊對實體經濟的波動影響更大。

圖3 房地產投資增長率的波動成分和實體經濟增長率的波動成分對彼此波動沖擊的反應
3.長期動態溢出效應
我們前面的檢驗和估計結果均表明,房地產與實體經濟之間有著顯著的相互影響,但是這種長期均衡效應只是一個均值,雙方的相互溢出效應在時間上、在不同的經濟周期里大小是否不變呢?以及相互之間溢出效用的變動是受到什么的影響呢?而且,之前的結論告訴我們兩部門的增長率和波動之間都有顯著的相關性,但到底哪一種更主要呢?
我們借鑒Diebold & Yilmaz(2009)的溢出指數(Spillover Index)來研究房地產與實體經濟之間溢出效應的長期動態變化過程。為保證滾動窗口回歸具有足夠的估計樣本,我們選用3個月(即1季度)的預測窗口和24個月(即2年)的回歸窗口,表4展示了結果。我們測算得到,房地產投資增長率和實體經濟增長率之間的溢出指數約為3.8%,表明房地產投資增長率和實體經濟增長率的總變動中大約有3.8%的部分是來自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而房地產投資波動和實體經濟波動的總波動中有10.9%是來自二者相互之間的作用。這說明房地產和實體經濟之間風險的傳染性更強[注]溢出指數的取值位于0和100%之間,如果溢出指數接近100%,表明兩個變量高度相關;如果溢出指數接近0,則表明兩個變量基本不相關。。

表4 房地產投資與實體經濟增長率與波動溢出效應的結構分解
圖4和圖5分別描繪了房地產投資和實體經濟增長率和波動之間溢出效應的動態路徑,從中我們發現:第一,房地產投資增長率對實體經濟增長率的溢出效應強于實體經濟增長率對房地產投資增長的溢出效應,進一步說明房地產投資的驅動作用。第二,房地產投資增長率對實體經濟增長率的溢出效應與房地產相關改革及貨幣政策調整的時間周期比較吻合,比如“98年房改”后政府首次嚴格介入并嚴格調控房地產市場,頒布包括“國八條”、“國六條”等(2004—2005年);金融危機及其后對房地產的嚴格收緊,包括“國四條”和“國十五條”等(2008—2009年);2012年為金融危機后首次大力度降息降準,房價出現新一輪的快速上漲(2012—2013年);頻繁降息降準及人民幣大幅貶值(2016—2017年)。第三,兩部門波動率之間的溢出效應水平基本持平,除了2004—2006年(房地產收緊“政策年”),2007—2008年(金融危機前經濟高漲時期)與2012—2013年(金融危機后首次降準、降息、放松房地產管束)。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得到以下結論:
結論5:長期來看,房地產投資風險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更大,且這種影響與房地產相關政策改革周期相吻合。

圖4 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增長率的溢出效應動態路徑

圖5 房地產和實體經濟波動率的溢出效應動態路徑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在VAR框架下建立GARCH-in-Mean模型,將方差從引入均值方程,研究了1998—2017年房地產市場化改革后的20年間,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增長率和風險的長期均衡關系,以及其中的金融傳導機制。我們發現:第一,房地產投資增長能提高實體經濟的增長率,實體經濟發展也促進了房地產投資的加速;第二,房地產投資的風險升高抑制了實體經濟的增長,而實體經濟的風險增加則促進了房地產投資增長;第三,房地產投資風險加大會增大金融風險進而抑制實體經濟的增長,而實體經濟風險會刺激金融增長和加大金融風險進而擠出資金進入房地產。進一步地,為了研究兩部門之間動態的關系,我們分別利用廣義脈沖函數、方差脈沖響應函數和動態溢出指數分析了房地產投資與實體經濟增長短期沖擊響應和長期動態關系,發現:短期來看,實體經濟的增長沖擊對房地產投資增長影響更大,而房地產投資風險對實體經濟的風險影響更大;長期來看,房地產投資風險對實體經濟風險的影響占主要地位,且這種影響與房地產相關政策的周期更吻合。
基于以上結論,我們得到的啟示和政策建議為:第一,作為國民經濟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房地產和實體經濟之間總體上具有相互促進的關系。但是想要減緩房地產行業的增長、加快實體經濟的發展進程,采取嚴格打壓房地產投資或者房價的政策不僅會加大房地產風險,還會加大金融風險。資金會加大杠桿地投入到房地產部門,反而抑制了實體經濟的增長。要把握好“脫虛向實”的速度和力度。第二,要引導資金“脫虛向實”,首先要去產能并促進有效創新,提高實體部門的產出效率和利潤率,實現結構優化升級,而不是通過一味地打壓其他行業來保護現有的實體經濟結構。第三,在去產能的過程中,也要控制好速度,因為這個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實體經濟風險的加大,從而引致資金逃向房地產或者金融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