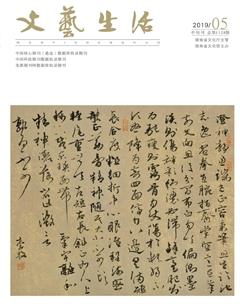談談當代藝術對中國文化“血脈”的繼承問題
李楠
摘要:本文在回顧中國當代藝術發生發展的幾十年的綜勢基礎上,重點探討文化“血脈”繼承問題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反思的啟發性。同時結合全球化趨勢下文化身份認同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指出中國當代藝術的精神性本質應歸結到本民族的文化“血脈”中,并對此觀點所涉及到的當代藝術家個案進行批評性分析,以期引起學術界對此問題的重視。
關鍵詞:中國當代藝術;“血脈”;繼承;文化個性
中圖分類號:J1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9)14-0167-02
一、回顧與反思
在中國當代藝術從萌芽到發生再到發展的全景式過程中,始終都存在一個文化“血脈_上的繼承問題。這個問題在當下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反思中愈顯其重要性,并有較大的探究空間。我們先著眼于85年美術思潮的發生過程。從筆者上一代的這些藝術青年的尋求追問當中似可以看出一種教訓。在那個時代的年青畫家接納了那個時代“前衛”理論的沖擊和自由思潮的滌蕩,對西方的各種“主義”瘋狂“摹拜”,對某個流派或巨匠的作品進行拷貝已顯出“全盤西化”的趨勢,這一現象帶來的后果是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一個國家形成的藝術風格只有建立在自己的民族特點之上才算是真正的風格,才能產生真正的主義,自己的主義,否則只能是別國的拙劣的翻版。其中的教訓與啟發是:只有深深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當中,才能產生真正的“中國版本”的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如果活生生的切斷了自身的文化“血脈”,不但產生不了世界有影響的藝術,而且無異于自毀文化根基。如果不斷地重復這種所謂藝術的“新潮”運動,可以說對中國藝術文化的發展是可悲的。
中國當代藝術想要產生一種真正新的面貌,就要把當代藝術的觀注重點由注重觀念轉移到關注人的內在心靈問題上。觀念本身并不是藝術,創造一種所謂“中國當代藝術形象”的符號也不是真正的當代藝術。當代藝術應真正的關注于這個社會,這個歷史時期人的心靈中最需要的情感和一種人性中永恒不變的東西;一種追求真善美的信念,而這種信念在當今所表現出來的中國當代藝術作品中似乎越來越孱弱。近幾十年來在世界范圍內藝術觀念進行著一場“選妃”運動。這種“選妃”的方式造成了中國文化符號的一種變異,而所謂“中國當代藝術形象”正是這種變異過后的一種產物。政治波普、文革圖像,玩世寫實主義在西方“后殖民”文化的國際化趨勢下,直接影響并刺激了中國當代藝術的創作思潮,并且由于符合西方人眼中和意念中的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形象,能頻頻亮相于國際性大展。在國外傳媒,國外畫廊及國內批評家,大眾傳媒的作用下逐步取得了社會性的影響,取得了當代藝術范疇的話語權。
這種現象之后產生了很值得思考的問題:一大批中國當代藝術家殫精竭慮地揣摩西方人的心理,迎合西方人的文化口味塑造并展示所謂的“當代中國藝術”的形象。從而產生了一大批只具圖式化意義的作品。它的影響力大都集中在海外,展出,發表,收藏的活動也都在國外,而且它的文化動機除了部分藝術家本身的需要外,大部分出自西方對中國的文化期待,與本土的心靈歸屬感和社會文化沒有多大聯系,這是西方系統催生出的“中國文化形象”。這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中國當代藝術的癥結所在:當代中國藝術品格并沒有真正形成。因為它缺乏藝術精神中最重要的一些東西,即自己本土民族的藝術風格和文化個性。沒有這些,藝術精神也就無從顯現和表達。沒有藝術精神,藝術的品格的形成也就無從談起。但同時我們應看到一點,在中國當代藝術中真正具有民族審美價值和本土文化價值的作品是存在的,而正是這些作品可以被歷史所證明是反映了真實的處于這一時期中國人的內在心靈問題的。這樣的作品體現出的文化價值是值得承認和肯定的。那些真正具有中國藝術精神和氣質品格的當代藝術品能引起廣大民眾心靈的共鳴,是能得到人們充分理解與好評的。這些說明我們今人要真正發展的繼承中國傳統文化“血脈”的精髓,就必須把眼光放到新的時代藝術背景中去,要給當代藝術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使之具有真實的文化價值。
上述論述說明,我們既不能永遠地停留在西方藝術的世界中,忘記了自身的文化“血統”,不斷地對西方藝壇崇洋跟風,做謅媚的奴才,也不能固步自封地停留在中國古老的傳統中不能自拔,作古人的走狗。總之,這兩條路都難以真正通向中國本土的當代之路。
二、對文化“血脈”的理解與創造性繼承
我們通過近年來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反思,可以看到當代藝術的出路何在呢?對于當代藝術的理念構成和理解,認為它關注的問題反映相關的社會語境,主要創作與社會語境相符的作品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這一點己使藝術與社會的發展問題過密過深地產生了一種“畸形”的關系。藝術的運用和體現完全用在暴露揭示在社會各方面的互相依存關系上,在這一過程中,當代藝術用反諷、荒誕、自娛、質疑等種種可能的手段,打造形成出了一片當代藝術話語權的新陣地。有很多人認為當代藝術就應該是這樣的藝術,這樣的藝術是符合時代對“藝術”的要求的,也是藝術家所理應表現出的方式。但如果一味地如此發展下去,藝術的真諦和它所飲食的人性精神與追求美的本質可能將消融,藝術也就不再是藝術,藝術會不存在了。因為這種對社會發展問題進行深入揭示和解決的工作應留給政治家、哲學家、社會學家去做。藝術家應該做他本份的事,而藝術家的本份就是使人的內心深處得到平靜快樂,用一種文化精神的內涵使人們和他的作品產生共鳴。這些的基礎恰恰源于本土本民族的文化“血脈'之中,對傳統文化“血脈”發展地繼承是這一切的動力。這種繼承會提供給藝術家一種本真的沖動和心境的自由,擁有這些他才能夠感受到美并創造出美。當代藝術家必須要對當今生活的世界性問題有一個比較深刻的了解,對同時代人的生存狀態和心靈需求有著異乎常人的敏銳,對于前代的藝術現象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要超越東西方任何一個主義和大師的模式,同時要發展、繼承和不斷的更新自身的文化“血脈”。只有這樣做,才能找到中國本民族當代藝術的真正出路。其本質就是要構建“中國版本”的當代藝術。真正“中國版本”的當代藝術作品是注重本國傳統文化精神和審美價值的,對本土本民族藝術特點和美學傾向有著深入的表現和挖掘。在現今一個時期,當代藝術所呈現出的紛繁多樣的狀態,可以說使中國當代藝術的創作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讓中國的藝術家們產生了對藝術不同的理念和表現藝術的方式,而不論如何去理解和去表現,我們認為有幾個基本的東西必須去確認,藝術家的作品是否提出了中國當代文化中最有價值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是否從中國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提煉出來的,最重要的是藝術家的作品是否智慧地傳達出中國文化特有的內涵。這種內涵傳達出中國藝術精神所特有美感與快樂。我們認為對當代藝術進行評價和研究的時候,不應根據從自己好惡出發也不應該用空洞的觀念、現象來代替藝術,藝術是一種源于內心最深處的美好沖動。它的發生與結束實際上是無所規定的,出來的作品掩飾不住自己本真的狀態,甚至連藝術家自己也吃驚。藝術不能用概念或企業化操作來創造,它是人性中美好一面的流露,必須有美學上的意義。中國的當代藝術理應回歸到關注人的內在心靈和精神的本質層面上來。我們要在立足于當代文化環境同時,在關注現今人們的心靈思想行為的同時,要有意識地去深入探求本民族文化內在的“基因”,去有建設性地保持本民族的文化“血脈”,有意識去繼承這種文化“血脈”。只有使自己的藝術真正產生于自身的民族和國家的藝術精髓之中,才能真正表達出自己的藝術精神。
在整個中國文明史的顯現中,在文學藝術形態(其中包括詩、書、畫、印、文、舞、樂、建筑、雕塑、園林等)的文化“血脈”之外,在古代的儒、釋、道三教中,大至文化體系,思想體系中,同樣體現了一種“血脈”,流露出神妙絕美的光芒,閃現著思想智慧的火花,而且這些都與藝術的精神“內核”密切相關。由此可見,中國的文化“血脈”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地發展,變化的。所以才能源遠流長,成為一個極宏大、瑰麗的藝術寶庫,提供大量的藝術財富,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堅強后盾,是吸收藝術營養和啟發創作靈感的家園。
對于中國思想文化體系中體現的文化“血脈”問題,許多近,現代先哲前輩如王國維、錢穆、宗白華、徐復觀、錢鐘書、李澤厚等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發掘,概括,歸納和闡述。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和側重點已給后學們指出了思路,使我們可以站在有一定高度的體認平臺上,但這項工程遠沒有做徹底,甚至可以說是永無止境的。因為只要中國的文化精神、體系存在,就存在對文化“血脈”問題的深入研究的必要,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學人和藝術家去繼往開來。
對于我們后學來說,生存于中國的文化環境中,這種文化“血脈”和我們的天性相連,是與生俱來存在于我們的血液之中的。要在后天通過系統刻苦的發掘練習來達到一種具有中國文化精神“內核”的藝術狀態。創造出真正“中國版本”的有價值的藝術作品,首先要對中國的傳統文化“血脈”進行發展的繼承,之后要在時代中進行創新,使之傳承久遠、發揚光大。
在當代,已有不少藝術家(國內與國外的)都致力于文化“血脈”的傳承與發揚,且己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徐冰、黃永玉、尚揚、周春芽、洪凌、井士劍、賈滌非、邱志杰、洪磊、吳為山、孔國橋、張謐詮、劉大明、任傳文等。而且這種趨勢己不僅局限于架上繪畫,也在影像、裝置、雕塑等多個不同領域拓寬和發展。由此看出,在相當一部分的當代藝術家的眼中,文化“血脈”繼承已是一個共識。也通過他們的作品,中國當代藝術在世界藝壇贏得了一席之地。但不得不承認,對文化“血脈”繼承問題的重要性還遠不是所有當代藝術家的共識,我們還需不斷努力,任重而道遠。
三、結論
使文化“血脈”傳承發揚,則中國當代藝術才能興盛發達。當代藝術家都應重視和關注這個問題,只有把我們中國的當代藝術之根牢固地深深地植入本土深厚而肥沃的文化土壤里,才能促使它在其中茁壯地成長、壯大,開出具有中國獨特文化性格的奇葩,從而傲艷于世界藝術群芳之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