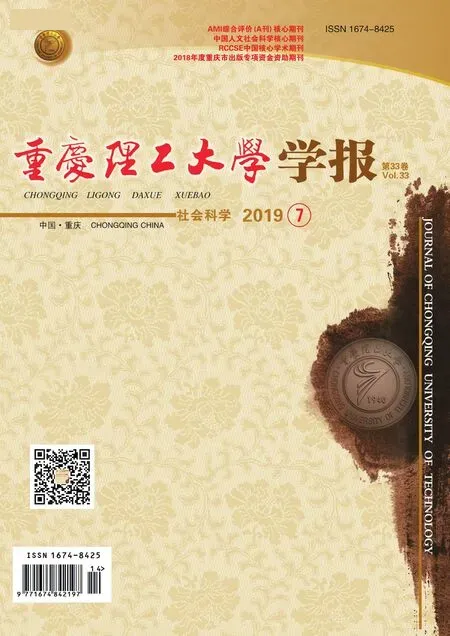國際移民和人才的流動分布及競爭態勢
周靈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 北京 100010)
自人類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以來,遷移可以說是人口在區域間配置的一大方式。尤其是在現代社會,人們基本上能夠從滿足自身偏好出發,為改善經濟狀況或發展空間而自由地進行遷移。當然,不同時期、不同社會經濟條件下的遷移是有差異的。一般而言,在一個停滯、傳統的經濟體中,遷移的經濟作用十分微小,但在經濟和人口都不斷增長的經濟體中,其作用卻非常重要[1]。這種作用既體現在個人身上,也表現在社會層面。譬如,移民往往能帶來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滿足生存及發展的需要,有助于減少貧困、提升人力資本、促進社會公平、推動城市化,這些作用得到了廣泛的證據支持[2-3]。
本文利用聯合國、OECD、世界經濟論壇等機構數據,在描述國際移民流動和分布態勢的基礎上,分析國際人才競爭的基本格局,并結合中國實際,歸納人才流動特征、探討新時期的國際人才戰略。本文所稱的國際移民是指人口的跨境遷徙,也即根據《聯合國關于國際移民統計的建議》,將常住國發生改變的人定義為國際移民國際移民可分為短期移民(常住國發生變化在3個月到1年之間)和長期移民(常住國改變至少1年)。但由于各國標準不盡一致,使得長短期的區分缺乏完備數據。。
一、國際移民的流動和分布態勢
(一)國際移民的總體演變和構成狀況
隨著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推進,全球范圍內的移民和人才流動成為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現象。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數據顯示,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移民總量在快速增長,移民數量從1970年的8 446萬人增加到了2017年的2.57億人,移民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也由1970年的2.3%上升到2017年的3.4%(圖1)。
按發展水平劃分,國際移民主要分布在高收入經濟體,其絕對量由1990年的7 523萬人增加到了2017年的1.64億人,增加了一倍多,居住在高收入經濟體的國際移民占到了世界移民總量的63.8%,也就是說,近2/3的國際移民分布在高收入經濟體。相形之下,2017年居住在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國際移民為8 143萬人,而居住在低收入經濟體的國際移民只有1 091萬人(圖2)。

圖1 國際移民數量及占人口比重[注]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November 2017[4];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2017),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The 2017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database,POP/DB/MIG/Stock/ Rev.2017).

圖2 國際移民存量累積分布圖(按發展水平)①
國際移民存量的區域分布表明(圖3),2017年亞洲擁有7 958萬移民,歐洲擁有7 789萬移民,北美洲的國際移民存量為5 766萬人,亞洲、歐洲和北美洲的國際移民存量排在世界前三位,再往后是非洲、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和大洋洲。大洋洲的國際移民存量最少,2017年只有841萬人。從趨勢看,1990年以來亞洲、歐洲、北美洲、非洲的國際移民存量在穩步增長,其中,亞洲、歐洲、北美洲的國際移民存量各增加了3 000萬人,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大洋洲因移民的數量級較小,增長趨勢不是很明顯。
同每個地區的人口數量相比,2017年國際移民比例最高的是大洋洲、北美洲和歐洲,其國際移民人口分別占對應地區總人口數的20.7%、16.0%和10.5%,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的國際移民比例則相對較小,2017年其比重僅分別為1.8%、2.0%和1.5%。按發展水平劃分,國際移民占對應地區人口比重最高的是高收入經濟體,2017年其占比高達14.1%,比1990年增加了6.4個百分點(1990年該比例為7.7%)。顯然,近30年來高收入經濟體的國際移民人口比重在逐步增加。相形之下,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的國際移民人口比重長期徘徊在1.6%左右,中等偏下收入經濟體和低收入經濟體的國際移民人口比重卻呈現下滑趨勢(圖4)。具體而言,中等偏下收入經濟體的國際移民人口比重由1990年的1.8%下降到了2017年的1.0%,低收入經濟體的國際移民人口比重則由1990年的2.6%下降到了2017年的1.6%。

圖3 國際移民存量分布(按區域劃分)[注]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2017),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The 2017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database,POP/DB/MIG/ Stock/Rev.2017).
從主要的移民來源國和目的國來看,2017年世界十大移民來源國從高到低依次是印度、墨西哥、俄羅斯、中國、孟加拉國、敘利亞、巴基斯坦、烏克蘭、菲律賓和英國,十大移民目的國從高到低則依次是美國、沙特阿拉伯、德國、俄羅斯、英國、阿聯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西班牙(圖5)。自1970年起,美國一直是國際移民主要目的國,居住在美國的外國出生人數從1970年的1 100多萬人上升至2017年的4 977萬人,翻了兩番。德國從2005年起便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移民目的國,2015年有1 200多萬名國際移民住在該國。2017年沙特阿拉伯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移民目的國,該年居住在沙特阿拉伯的國際移民達到1 218萬人。俄羅斯作為主要的移民目的國,勞務移民是其突出特色[注]1991年蘇聯解體后,在2005年之前的大約15年里,俄羅斯是世界第二大國際移民目的國。勞務移民是俄羅斯的主要移民形式[5]。,勞務移民已成為俄羅斯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和公共住宅服務業等行業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圖5 2017年世界十大移民來源國與目的國①
中國和印度作為人口大國,是主要的移民來源國。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的數據顯示,2017年有996萬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國際移民生活在世界各地,中國是世界第四大移民來源國。2017年有1 658萬名印度移民生活在世界各地,印度是世界第一大移民來源國。憑借地緣優勢,每年有大量墨西哥移民前往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墨西哥是世界第二大移民來源國(2017年有1 296萬名墨西哥移民生活在世界各地)。俄羅斯既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國,也是重要的移民來源國,2017年有1 063萬名俄羅斯移民生活在世界各地。主要移民來源國中比較特殊的是敘利亞,其國際移民大都是戰亂和沖突所致,也即難民和尋求庇護者是敘利亞移民的主體。
就常規移民而言,工作是人們進行國際移民的主要原因,而且外來務工人員占了全球國際移民的絕大多數。國際移民組織發布的《世界移民報告2018》顯示,外來務工人員約占全球國際移民總人數的 2/3,且75%的外來務工人員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23%生活在中等收入經濟體,去往低收入經濟體的外來務工人員僅占總量的2%[4],圖6展示了勞務移民在不同發展水平經濟體的分布情況。在職業構成上,大多數勞務移民從事的是服務業工作。
從國際移民的年齡構成看,25~44歲的核心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從1990年的38.3%、2000年的39.3%提高到2010年40.5%,進而提高到2017年的40.8%,而0~14歲少年兒童移民的占比則從1990年的12.4%降到了2017年的9.8%,65歲及以上老年移民的比重則維持在11%左右,說明國際移民的主體是青壯年勞動力。圖7直觀地展示了1990—2017年世界移民的年齡構成。盡管隨著時間推移,國際移民各年齡組的構成狀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并未改變其分布規律。

圖6 勞務移民分布情況(按發展水平劃分)[4]
總體而言,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移民的總量一直在上升,其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也在逐步攀升。與低收入經濟體和中等偏下收入經濟體相比,居住在高收入經濟體和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的國際移民數量也一直在攀升,其中,高收入經濟體國際移民數量的增長最為明顯,而且高收入經濟體的國際移民人口比重依然在增加。這種演變態勢持續了數十年,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短期內發生逆轉的可能性不大。
(二)留學生和技術移民的基本情況

圖8 2017年高等教育階段留學生十大生源國資料來源:筆者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統計數據繪制
隨著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教育合作的日益繁榮,留學已成為國際移民的主要方式和有效途徑。不少學生遠離祖國、前往東道國求學進修,有助于深入了解東道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畢業后也相對容易留下工作并融入當地社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數據顯示,2012年全球高等教育階段的在讀留學生人數是405.83萬人,2017年則超過了508萬人,顯然,近些年來高等教育階段的留學生增長較快。
中國、印度、德國、韓國、法國、哈薩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亞、越南、烏克蘭是高等教育階段留學生十大生源國(圖8)。2017年上述10國高等教育階段的海外在讀留學生合計191.77萬人,占全球高等教育階段留學生總數的37.75%。其中,中國海外在讀的高等教育留學生數量達86.94萬人,占全球的17.11%。印度緊隨其后,總數為30.60萬人。中、印兩國的海外留學生數量長期處于世界前兩名。從發展水平看,高等教育階段的十大生源國中,德國、韓國、法國、沙特阿拉伯是高收入經濟體,其他國家是中等收入經濟體。總體而言,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經濟體的留學需求較大,2017年這兩類經濟體的高等教育在讀留學生數量占到了全球的82.15%。
表1列示了主要經濟體高等教育階段的留學生比重。由表1可知,2016年英國、新西蘭、瑞士、澳大利亞、奧地利、盧森堡、比利時、加拿大、捷克、丹麥、荷蘭等國家高等教育階段的留學生比重皆超過了10%,盧森堡最高,達到47.00%,新西蘭為19.84%,英國為18.10%。美國留學生的規模雖然很大(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留學目的國),但由于學生基數大,其高等教育階段的留學生比重只有5.04%,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OECD—歐洲平均比重為8.70%)。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韓國高等教育階段的留學生比重不是很高,這在高收入經濟體中屬于比較特殊的情況,這一方面跟其所在的“冷門留學區域”大環境有關[注]傳統上,相對于歐洲、北美、大洋洲,東亞、東南亞、西亞、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屬于“冷門留學區域”。這種狀況近些年來有所好轉,特別是中國政府通過獎學金和更加靈活的資助政策降低留學成本,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際留學生。,也和學生基數較大有關。

表1 2016年主要經濟體高等教育階段國際學生比重 %
資料來源:OECD (2019),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Indicator)
從新興經濟體看,盡管近年來留學生比重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與發達經濟體相比,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留學生比重還處于較低水平。在金磚國家中,南非和俄羅斯高等教育階段的留學生比重相對較高,2015年南非高等教育階段留學生比重為4.12%;俄羅斯的表現更出色,其高等教育階段的留學生比重從2013年的1.84%快速上升到2016年的4.04%;中國國際留學生的比重雖然也在攀升,但由于初始水平低,到2016年該比重也只有0.31%;印度、巴西的留學生比重則大致分別穩定在0.13%、0.24%(圖9)。

圖9 金磚國家高等教育階段國際學生比重資料來源:OECD (2019),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Indicator)
總體而言,國際留學生數量和比重較高的國家仍以高收入經濟體為主,且留學生的分布有進一步集聚趨勢。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2017年全球508萬名高等教育留學生中,有380萬是在高收入經濟體留學;2016年高等教育階段在讀留學生最多的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法國、德國、俄羅斯、加拿大、日本、中國、安哥拉等10個國家的留學生總量高達319.63萬人,約占全球高等教育階段留學生總數的63%。其中,美國高等教育階段在讀留學生人數為97.14萬人,遠遠超過排在第二位的英國(英國為43.20萬人)。
技術移民也是人才跨境流動的一大方式,通常是根據文化程度、職業技能、語言能力等綜合實力來申請移民。但當前還缺乏全球范圍的技術移民統計數據,只能從部分國家和地區的零星統計一窺堂奧。從實踐看,技術移民目的地主要是經濟發展水平高、人居環境好的發達經濟體,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是熱門的技術移民目的地。澳大利亞移民局數據顯示,2015—2016財年,澳大利亞共為海外移民提供19萬個永久居民名額,其中包括12.85萬個技術移民(含雇主擔保、普通技術移民及商務移民);2016—2017財年,澳大利亞共為海外移民發放18.36萬個永久居民名額,其中包括12.35萬個技術移民;2017—2018財年,澳大利亞共為海外移民發放16.24萬個永久居民名額,其中包括11.09萬個技術移民。由此可知,在永久居民名額的分配中,技術移民往往是最主要的部分(技術移民通常占澳大利亞國際永久居民名額的70%左右),是東道國所看重的群體。
(三)難民等特殊移民的基本情況
雖然絕大多數人進行國際移民是出于工作、家庭和學習的需要,但也有許多人是出于其他迫不得已的原因,比如沖突、迫害和災難。因此,由沖突、戰亂、災害等因素引發的全球流離失所和非常規移民現象也是探討國際移民問題不可回避的重要方面。聯合國統計資料顯示,世界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存量已從1990年的1 883萬人增加到2017年的2 591萬人,絕對存量增加了700多萬人。當然,隨著常規移民數量的大幅增長,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占國際移民總量的比重有所下降,2017年約占10.1%,如圖10所示。
難以化解的、未被解決的和持續發生的沖突和暴力事件是導致世界難民人數增加的最主要原因。例如,2011年爆發并持續至今的敘利亞沖突,已造成600多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從難民的構成看,婦女、兒童占了世界難民總數的大部分,他們是極其脆弱的群體,亟須重點救助。而且,難民和尋求庇護者這類特殊移民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經濟體和低收入經濟體(圖11),這是因為難民往往缺乏遠距離遷徙的能力和條件,通常只能前往毗鄰沖突地區的國家避難。例如,聯合國數據顯示,2017年有1 765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分布在中等收入經濟體、405萬分布在低收入經濟體,二者合起來占了世界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總量的83.7%。
分國家和地區看,2017年中東和北非地區收容了全球26%的難民、非洲則收容了全球30%的難民;土耳其收容了290萬難民(主要來自敘利亞)、巴基斯坦收容了140萬難民(主要來自阿富汗)、黎巴嫩則收容了100萬難民(主要來自敘利亞)。非洲的埃塞俄比亞、烏干達收容的難民也比較多[注]2017年,埃塞俄比亞收容難民79.16萬人,烏干達收容難民94.08萬人。,主要來自相鄰地區。聯合國難民署的一大任務是為難民尋求永久的解決方案,比如自愿返鄉、就地融合和重新安置,但要解決好難民等特殊移民問題,需要國際社會付出更大努力。

圖10 世界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存量及占移民比重[注]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2017),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The 2017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database,POP/DB/MIG/Stock/Rev.2017).
二、國際人才的流動分布和競爭態勢
經濟增長理論表明,以人才為代表的優質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依托。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推進,國際人才的流動分布漸次成為備受關注的話題,以人才資源為核心的全球價值鏈也正在形成。
從政策看,各國政府大都將人才視為核心戰略資源,最突出的當屬美國。美國不僅是國際人才的最大輸入國,也是國際人才競爭的最大贏家,其國際人才戰略的核心特質便是不拘一格、網羅世界各地人才。基于這一戰略,從世界各國吸納各領域人才便成為美國移民法的重要原則[注]美國移民法通過設立職業移民類別來吸納國際人才,依技能高低將職業移民分為3類,并給予不同的優先程度,技能越高,優先程度越高。具體而言,第一類優先吸納的對象是各領域的頂尖人才,第二類優先吸納的對象是高技能人才,第三類優先吸納的對象則是技能雖一般,但卻是美國雇主急需的人員[6]。。據統計,就職于硅谷的科研人員和工程師中大約有1/3是國際移民;1901—2010年,每4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科學家中就有一人是外國移民[6]。
盡管可供使用的數據資源較之前豐富了不少,但依然缺乏國際人才流動分布的確切統計,只好用相近的指標來刻畫相關事實。目前比較理想的資料主要有兩個:一是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人力資本報告2017》(The Global Human Capital Report 2017[7]),二是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也譯作“英士國際商學院”)發布的《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2019》(The 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9[8])。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人力資本報告2017》通過構建系列指標,測度了130個經濟體的人力資本指數。該指數由4個一級指標、21個二級指標加權而成。以“能力(Capacity)”一級指標為例,它基于4種常見的受教育程度,按勞動年齡組進行分類測度,這些數據分別反映了至少完成過初等、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以及具備基本識字和算術水平的人口比例[7]。
眾所周知,人力資本體現了個人擁有的能夠創造個人、社會和經濟福祉的知識、技術、能力及素質,人力資本水平高的群體更容易適應新技術、創新和在全球范圍內競爭。與此相關的人力資本指數則是勞動力素質、人才集聚及發展水平的綜合測度,人力資本指數高往往說明了勞動力素質、人才集聚及發展水平高。
表2列示了2017年人力資本指數排名前40位的經濟體,排在前面的都是美歐等發達經濟體,挪威、芬蘭、瑞士、美國、丹麥、德國、新西蘭、瑞典、斯洛文尼亞和奧地利占據了人力資本指數排行榜的前10名,新興經濟體中只有俄羅斯(第16名)、馬來西亞(第33名)、中國(第34名)和泰國(第40名)能躋身前40名榜單。在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中,越南人力資本指數為62.19,排在第64位;墨西哥人力資本指數為61.25,排在第69位;土耳其人力資本指數為60.33,排在第75位;巴西人力資本指數為59.73,排在第77位;南非人力資本指數為58.09,排在第87位;印度人力資本指數為55.29,排在第103位。

表2 2017年人力資本指數前40名經濟體[7]
資料來源: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Human Capital Report 2017:Preparing people for the future of work
可見,發達國家和地區是世界人才的主要集聚地和流入地,廣大發展中經濟體和落后地區則往往經歷著人才匱乏、智力外流及其帶來的弊端。上文剖析國際移民的流動分布態勢時,移民隊伍里其實已包含高人力資本的人才群體,人才流動及分布的特征事實也可以從大的移民態勢中捕捉。這里以人工智能人才的分布情況作為具體例子。據估算,截至2017年6月,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大約有30萬名,主要分布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人工智能新興企業、科技巨頭及其他領域。從國別看,美國1 078家人工智能初創企業約有78 700名人才,中國592家公司中約有39 200名員工,中國人工智能人才數量只有美國的一半,其后分別是英國、以色列、加拿大等國[9]。
相對于綜合測度勞動力素質、人才集聚及人才發展水平的人力資本指數,《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2019》(The 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9)則是專注于人才競爭力的指標體系,它涵蓋了125個經濟體,可以較好地測度全球人才競爭的基本態勢。國家層面的人才競爭力指數是由“稟賦條件(Enable)”“吸引力(Attract)”“成長性(Grow)”“可留住(Retain)”“職業與專業技術技能(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kills)”“全球化知識技能(Global Knowledge Skills)”等6個一級指標加權而成[注] 指標中的“稟賦條件(Enable)”包括監管環境、市場格局、商業與勞工狀況等。,城市層面的人才競爭力指數則是由“稟賦條件(Enable)”“吸引力(Attract)”“成長性(Grow)”“可留住(Retain)”“全球化(Be Global)”等5個一級指標加權而成[8]。一級指標權重的確定和二級指標的選取都經過嚴密論證,具有權威性和代表性。
測算結果表明(表3),2019年全球人才競爭力排在前40名的國家和地區大都屬于發達經濟體,只有馬來西亞(第27名)、哥斯達黎加(第34名)等極少數中等收入國家的人才競爭力能躋身世界前40名,瑞士、新加坡、美國、挪威、丹麥、芬蘭、瑞典、荷蘭、英國、盧森堡囊括了全球人才競爭力前10名,除新加坡外,都位于歐美。主要新興經濟體中,中國人才競爭力指數為45.44,世界排名第45位;俄羅斯人才競爭力指數為43.47,排在第49位;墨西哥人才競爭力指數為38.00,排在第70位;南非人才競爭力指數為37.94,排在第71位;巴西人才競爭力指數為37.57,排在第72位;土耳其人才競爭力指數為37.44,排在第74位;印度人才競爭力指數為35.98,排在第80位;越南人才競爭力指數為33.41,排在第92位。顯然,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新興經濟體總體上還不具備明顯的人才競爭優勢,人才隊伍建設任重道遠。分區域看,北美、歐洲的人才競爭優勢仍在強化,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人才競爭基礎在逐步弱化。

表3 2019年全球人才競爭力前40名經濟體
資料來源:INSEAD,The 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9
全球企業家人才競爭力指數的地區分布也表明,歐洲、北美洲、大洋洲的高收入經濟體在該指標上的表現非常出色,非洲、拉丁美洲、南亞、中亞等地區多數經濟體的企業家人才競爭力較弱。這說明,當涉及更廣泛的創業人才角色時(企業家精神),僅僅關注一個或幾個方面是不夠的,必須采取更全面的行動。由于這種人才很可能是跨境和跨部門的,因此,圍繞創新,培育發展強大而充滿活力的經濟系統,打造更加開放包容、宜居宜業的環境依然是各國提升國際人才競爭力的重要“抓手”。
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金磚國家自然備受關注。但從2013—2019年人才競爭力指數的演變情況來看,金磚國家在人才隊伍建設和人才制度設計等方面還有大量工作要做,特別是印度、巴西和南非,人才競爭力指數呈現出下滑跡象,中國和俄羅斯的人才競爭力指數雖有波動,但總體上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圖12)。在人才競爭領域,中國和俄羅斯是離發達國家最近的新興經濟體。

圖12 金磚國家人才競爭力指數的演變資料來源:INSEAD,The 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9
當前,數字化和全球化正在增強創業人才的作用。2019年的人才競爭力報告特別側重于創業人才——如何在全世界鼓勵、培養和發展創業人才,以及這如何影響不同經濟體的相對競爭力。為了激勵企業家和企業內人才,新辦法正在出現,例如努力發展自下而上的創新、賦予雇員權力,這種變化在城市尤其明顯。分城市看,2019年全球人才競爭力20強城市全部位于發達經濟體(表4),美國城市占了1/4,華盛頓是全球人才競爭力最強的城市。華盛頓位居榜首可歸因于其穩定的經濟、充滿活力的人口、卓越的基礎設施以及高技能的勞動力和世界一流的教育。總體上,排名靠前的城市往往對人才最開放,而且“智慧城市”生態系統正越來越多地發揮“人才磁鐵”作用。

表4 2019年全球人才競爭力20強城市
資料來源:INSEAD,The 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9
從趨勢看,城市正擔負起更強大的人才中心角色,這對重塑全球人才競爭格局至關重要。可以說,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與最美好的希望,它們使人類社會變得更加富有、智慧、綠色、健康和幸福[10]。這是因為,城市有更大的靈活性和適應新趨勢、新模式的能力,城市能讓觀察、傾聽和學習變得更加方便,是創新的發動機,其對人才特別是企業家人才也更具吸引力。
三、中國的出國留學、外來移民和專家引進
某種意義而言,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也是中國日漸融入全球體系的過程,包括全球人力資源競爭體系。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就已注重派遣留學生前往發達國家深造。從每年的出國留學人數看,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已從1978年的860人大幅增加到2018年的66.21萬人,和現在以自費留學為主有所不同的是[注]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的66.21萬人中,國家公派3.02萬人,單位公派3.56萬人,自費留學59.63萬人,自費留學已占出國留學總數的90%。,40年前留學基本上是國家和單位公派,自費留學的較少,留學生的規模也比較小。
21世紀以來,中國海外留學生的增長非常明顯。從1978年到2018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585.71萬人,其中,2000—2018年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552.21萬人,占整個時期的94.28%,圖13直觀展示了這一過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585.71萬名出國留學人員中,有432.32萬人已完成學業,365.14萬人在完成學業后選擇回國發展,占已完成學業留學生群體的84.46%。
如前所述,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留學生生源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日本、韓國、瑞典、新西蘭等國的外國留學生中,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數量排在第一位。例如,中國是加拿大最大的國際學生來源國,2017學年達20.8萬人,約占加拿大國際學生總數的30%[注]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教育處:《中國和加拿大教育合作交流情況(2018版)》, http://www.eduembca.org/publish/portal55/tab3729/info138868.htm.。

圖13 1978—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和學成回國人員[注]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整理繪制。
“中國奇跡”的吸引和感召,使得越來越多的移民前往中國大陸工作或生活,絕對量從1990年的37.63萬人增加到2017年的99.95萬人,占中國人口的比重也從1990年的0.032%上升至2017年的0.071%(圖14)。中國香港地區和韓國是中國大陸最主要的移民來源地,2017年二者合計占中國外來移民總量的46.72%,巴西、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越南、美國等經濟體也是中國大陸主要的移民來源地(表5)。但也應當看到,中國的外來移民無論規模還是比重都很低,跟統籌利用國內國際兩種人力資源的現實需求并不相稱,還有較大的提升和改進空間。

表5 2017年中國大陸移民主要來源地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2017),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The 2017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database,POP/DB/MIG/Stock/Rev.2017)
盡管在人才培養方面中國某些領域可以比肩一流經濟體,這得益于中國完備高質的基礎教育體系[注]例如,2015年的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結果顯示,在閱讀、數學和科學方面的平均分數,中國為82.46分(加權分數),排在世界第7名,超過了德國、荷蘭、瑞士、新西蘭、挪威、丹麥等發達國家。,但總體而言,中國的國際人才競爭力還比較薄弱。《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2019》顯示全球人才競爭力100強城市中,中國大陸城市只有北京(第58名)、上海(第72名)、杭州(第82名)、廣州(第87名)、西安(第92名)、成都(第93名)和深圳(第94名)上榜,只占全球百強城市的7%,且排名較為靠后。以人工智能領域為例,中國存在著嚴重的人工智能人才缺口,不得不大力引進海外留學生和人工智能人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和日本是中國海外人工智能人才的主要供給來源,來自這5個國家的人工智能人才占到了中國海外人工智能人才總量的83.80%[9]。毋庸置疑,借助“外腦”、大力引進境外專家是中國國際人才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境外專家對中國發展的貢獻也得到了經驗證據的支撐[11]。

圖15 境外來中國大陸工作專家總量情況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歷年《境外來中國大陸工作專家統計調查資料匯編》整理繪制
國家外國專家局數據顯示,境外來中國大陸工作專家總量已由2002年的35萬人次增加到2015年的62.35萬人次,個別年份雖有波動,但總體趨勢是在增長(圖15)。從專家類型看,經濟技術專家是境外專家[注]境外專家是指中國境內除國際組織以外的各種類型企業、事業、行政單位、社會團體以及大型建設項目聘用的外國和中國港澳臺地區專家。根據境外專家聘用單位或所在單位的行業性質和國家外國專家局的有關規定,境外專家包括兩種類型:一是境外經濟、技術和管理專家(簡稱境外經濟專家),二是境外教科文衛類專家(簡稱境外文教專家)。的主體,2001—2015年中國大陸共引進經濟技術專家513.30萬人次,占引進境外專家總量的69.33%。盡管經濟技術專家的數量隨年度略有波動,但總體保持在30萬~40萬人次/年。
目前,在中國大陸工作的境外專家仍以短期工作居留為主(3個月以下),長期工作專家的比例只占總數的46%左右。大部分的境外專家來自亞洲(占52.24%),來自歐洲(22.04%)和北美(20.24%)的境外專家比重近年來有所提高。從來源地構成看,中國港澳臺地區(19.73%)、美國(16.27%)、日本(11.49%)、韓國(10.90%)、德國(5.31%)、英國(4.50%)、加拿大(3.82%)、法國(3.12%)和澳大利亞(2.34%)是中國大陸主要的境外專家來源地。
隨著中國相關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持工作簽證入境的專家比重大體穩定在53%左右,持訪問簽證入境的專家有所增長,比重大致占27%左右。但是,境外專家在中國大陸各地區和行業間的分布還很不均衡,80%以上的境外專家分布在東部地區,廣大中西部地區的境外專家人數較少。例如,2015年中部地區聘請經濟技術類境外專家總數為0.83萬人次,僅占全國總量的2.51%,西部地區聘請經濟技術類境外專家1.11萬人次,只占全國總量的3.37%。
分行業考察,國家外國專家局數據顯示制造業和教育業的專家在境外專家總量中占據絕對優勢,2015年二者分別占比36.44%和38.00%,其他行業的境外專家數量和比重大都比較低。特別是從事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的境外專家比重偏低。以2015年為例,從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境外專家數量為1.45萬人次,只占經濟技術類境外專家總量的4.40%,從事金融業的境外專家為0.39萬人次,只占經濟技術類境外專家總量的1.19%。
四、研究結論和啟示
本文通過對聯合國、世界經濟論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國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國專家局等機構數據的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近50年來,國際移民總量一直在上升,其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也在逐步攀升,國際移民主要是流向高收入經濟體,這種演變態勢持續了數十年,短期內不會改變。第二,外來務工人員約占全球國際移民總人數的2/3,且大部分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主要從事服務性工作,移民年齡結構的年輕化趨勢也并未改變。第三,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高收入經濟體是技術移民的熱門目的國,技術移民是高收入經濟體永久居留移民的主體。第四,受戰亂、沖突和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難民和尋求庇護者是國際移民中相對特殊的群體,他們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非洲和中東地區尤其明顯。第五,發達國家和地區是世界人才的主要集聚地和流入地,廣大發展中經濟體和落后地區則往往經歷著人才匱乏、智力外流及其帶來的弊端,人才隊伍建設任重道遠。第六,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新興經濟體的人才競爭力還不具備明顯的優勢,北美、歐洲的人才競爭優勢在強化,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人才競爭基礎有所弱化。第七,與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發達經濟體相比,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在內的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國際學生比重還很低,教育國際化程度有較大提升空間。第八,21世紀以來,中國出國留學生的規模快速增長,已成為主要發達經濟體國際學生的最重要來源國,留學形式也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以公派留學為主轉變成以自費留學為主,超過八成的留學學成人員選擇回國發展。第九,中國是世界主要移民來源國,但來中國工作或生活的國際移民規模還很小,其比重還不到中國總人口的0.1%,跟統籌利用國內國際兩種人力資源的現實需求還不相稱。第十,來中國大陸工作的境外專家以短期工作居留為主,經濟技術類專家是主要的引進對象,但境外專家在行業和地區間的分布還很不均衡,80%以上的境外專家分布在東部地區,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的境外專家比重偏低。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謹就新時期我國國際人才戰略談6點認識。
首先,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新時期國際人才競爭的局勢,立足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實際需要,適時改革涉外就業和移民的政策規定,適當擴大外來移民規模。盡管勞務移民、就業與創新一直處于移民政策爭論的中心,但對于高端人才和特殊人才,主要發達國家始終持歡迎態度。典型的如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的移民政策雖然以驅逐非法移民為主,兼顧提高了移民門檻,但卻特別制定了吸引企業家移民的政策;加拿大移民政策在收緊的同時,增加了高素質移民的數量;日本近年來頒布了一系列移民新政,旨在吸納來自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高端人才。
其次,加強國際人才戰略的頂層設計,可以在部分地區試點建設“國際人才先行區”。當前,自由貿易試驗區在中國上海、廣東、天津、浙江、福建、海南等地全力推進,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國務院在新時代推進改革開放的一項戰略舉措,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可以借助自由貿易試驗區(或自由貿易港)建設的契機,試點打造“國際人才先行區”,在理念、制度、框架等方面實現重大突破,吸引境外人員“來華逐夢”“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設人才強國。
第三,做好境外專家引進工作的同時,推動技術移民的立法工作,實現技術移民、工作管理、永久居留等制度的配套化。可以借鑒國際慣常做法,根據移民的文化程度、職業技能、語言能力等綜合實力來調配工作和居留名額,改變以往過于注重學歷的政策取向,拓寬人才外延,對特殊技能人才開設綠色通道。與此同時,對境外人才實施分類管理,加強對重點行業、高新技術領域境外人才的扶持,鼓勵、支持境外人才前往中西部或落后地區開展服務和工作。比如,在“外籍高校畢業生在華就業實行配額管理”前提下[注]具體規定請參見《關于允許優秀外籍高校畢業生在華就業有關事項的通知》(人社部發〔2017〕3號)。,增加中西部地區和落后地區的配額數量。
第四,推進職業資格互認和部分行業執業許可,提高跨境執業的便利度。職業資格互認是互信基礎上的制度共建,其適用范圍取決于各方開放服務貿易市場的具體承諾。目前,職業資格互認領域尚未達成普遍性多邊協議,雙邊或多邊經貿協議中的倡導性條款或專門性資格互認協議是職業資格互認實踐的主要法律表現形式。鑒于此,可率先與臨近的中國香港和澳門地區及韓國、日本、新加坡等經濟體推進相關領域的職業資格互認,在部分地區開展準入類國際職業資格認證試點。
第五,加強教育和文化等軟實力建設,提高教育國際化程度,支持境外人才來華創新創業。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生源國,但來中國留學的境外學生比重還很低,教育國際化程度還有很大提升空間。需進一步加強教育和文化等軟實力建設,不斷提升高等教育質量,在擴大出國留學規模的同時,也吸引更多的境外學生來華留學,縮小高等教育服務貿易逆差。在創新創業方面,可以比照“雙創”政策體系,鼓勵和支持境外人才來華創新創業,特別是鼓勵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專業的外籍高校畢業生來華創新創業。
第六,提高境外人才服務保障和管理水平,加強科技創新和成果保護力度,打造境外人才評價、使用、激勵與服務的完美流程。影響人才跨國流動的因素有很多,最為重要的是政策提供的人才流動能力、經濟發展前景和國家整體管理水平。在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同時,需進一步完善人才簽證、工作簽證審批服務配套,解決境外人才子女上學、配偶就業和醫療保障等問題。加強科技創新與成果保護力度,制定實施境外人才科技成果轉讓、科研成果獎勵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