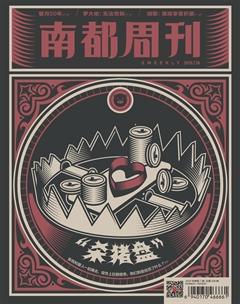刁亦男:我完全是排斥說話的一個導演
Lorenzo

在采訪刁亦男導演半小時不到的時間里,我被他身上獨有的—種文人氣質所吸引。“中國第六代導演代表人物”的標簽在他身上漸漸褪下,—種現代、知性以及圓融的韻味油然而生。我說不清這種感覺到底是來自他的外表還是他說話的方式,然而它不徐不疾,就讓我沉浸其中。
刁亦男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穿著一身黑西服,接近50歲的他給人一種莫名的親和力,仿佛一位學者。2014年他憑借作品《白日焰火》摘得第64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項金熊獎,這是華人導演里少有的殊榮。然而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絲驕傲,言談中他甚至表示幸運。當聊到電影的創作風格,我原本擔心會聽到一些空泛的言談,卻沒想到刁導深入地和我聊起了電影的美學。從昆汀到北野武,再到三尺崇史,刁導對于海外導演的熟知,印證了他與時俱進、博聞強識的學者氣質。“平常心”,或許是我對他的最佳解讀。
在《南方車站的聚會》首映會結束后,與其他導演起身享受戛納媒體和觀眾熱烈的掌聲不同,刁亦男首先起身對華語觀眾道歉。由于影片故事發生地在武漢,電影中的演員都講武漢話,對于大多數中國觀眾來說都聽不懂,而電影只有英文字幕,觀眾要光看字幕可能會有一定的理解偏差。他對字幕的不完整表示歉意,并表示電影在國內正式上映時將配有中英雙語字幕。這樣的真誠與恭謙,與戛納這座電影最高藝術殿堂的信仰竟不謀而合。
我有幸在戛納電影節第一時間觀看了《南方車站的聚會》并采訪了刁亦男導演,試圖了解他創作的初衷和電影背后的故事。
南都周刊:我們想了解您這部電影創作初衷是什么樣的?為什么當時要把這部電影的地點選在湖北?
刁亦男:因為電影里面有很多湖水,還要有不同樣態的湖水。那么湖北湖北,第一個字就是湖,武漢就是百湖之城。但是我們開始選景的時候并不是想選在武漢,而是想去廣東那邊,可廣東其實沒有那么多湖水,只是我個人的想象他有,而且湖水很少,有的話也都是在市中心,那一個逃犯那也不可能躲在市中心去藏身吧,所以到了武漢發現它有很多湖是和城中村是有關聯的,那很自然是選擇武漢了。
南都周刊:電影的劇本也是您自己的構思吧,您在創作的時候當時是怎么樣的一個初衷呢?有什么樣的想法?
刁亦男:在創作的時候,我本來開始是完全坐在沙發上聽著音樂,然后就產生了這么一個想法,就是我想象自己被通緝,身負了幾十萬的賞金,然后我就跑,想象我會跑到海邊的小城市。
在拍完《白日焰火》以后我看到一個新聞,說的是東北有一個監獄的犯人越獄了,他在村里小賣店看到了自己的通緝令。這個新聞和我當時想象的那個故事是一樣的。所以我覺得我構思的故事在現實生活當中也是真實存在的,把它拍出電影來是有一種可能性的。
南都周刊:電影有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創作的結合,我們覺得很好。
刁亦男:在我在寫劇本的時候,就把它改編成一種更開放的關系,主人公成了萍水相逢的男女,存在感更強一點,不是那么封閉,閉合。
南都周刊:關于選角,這次您選用了胡歌作為男主角。我們想知道您選用胡歌的原因是什么呢?
刁亦男: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明星,可能大家會覺得他就是偶像,是都市青年,不可能有別的角色塑造的潛力了。但是我恰恰想反著走,不選一個大家約定俗成的悍匪的形象。可能我覺得我的這個悍匪的這個氣質需要憂郁一點,需要沉默寡言一點,甚至你感覺他還有點弱弱的,有些敏感的氣質在里面,所以就我覺得用胡歌也未嘗不可。而且很多國際上的偶像明星他們也經常和一些藝術片的導演拍很嚴肅的電影,這也沒有妨礙電影所傳達的東西,影響電影的氣質,所以我就當機立斷選擇了胡歌。
“類型片會非常難,但是只有去進攻難的地帶,讓自己在創作上跳出安全區,去冒險。不怕失敗,才有可能去收獲新的改變。”
南都周刊:所以是一個比較創新的一種嘗試,您是希望用他的這種氣質來詮釋電影的感覺。
刁亦男:當然也有挑戰了,我還是很喜歡這種挑戰的,選一個你們都認為不合適的。我不想從一個純現實主義的角度來選擇演員。
南都周刊:您的這部電影和您上部電影《白日焰火》區別非常大,這部電影里面有很多的槍戰戲,甚至有些暴力血腥的鏡頭,有很多風格的東西在里面。這樣的一種創作風格的轉型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考慮呢?
刁亦男:一般警匪片都會有槍戰戲,只不過大家拍攝方法不一樣。那么我的拍攝方法可能是強調風格化,像你所說的,這種風格化建立在鏡頭的分切、或是長鏡頭的情況下,形成一種硬朗的氣質,這也是我一貫拍攝的方式。
南部周刊:有些觀眾覺得這部電影有些像昆汀的風格,甚至像尼古拉-溫丁一弗雷恩,那個丹麥導演的風格。
刁亦男:其實也沒有,因為昆汀的電影,昆汀是話癆嘛,他的電影永遠是在說話,但我完全是排斥說話的一個導演,我是讓我的演員少言,盡量用行動展現。所以胡歌在拍戲的時候,他說這整部戲對白都不如他電視劇一場戲多。還真是,他的電視劇一場戲三頁對白,我這個全片才兩頁。所以我的演員很少說話,而昆汀是比較愛說話的導演。
但是昆汀對暴力的呈現可能和我相似。不過對暴力的呈現所有的有風格追求的導演都會這樣,比如說杜琪峰導演,比如說更早的佩金帕,拍《日落黃沙》的那個,他也是極端的風格化。其實日本的一些的導演,比如說深作欣二,三尺崇史,北野武,他們是會拍風格化暴力。所以說這個也不是說誰和誰像,其實它是一種美學,如果你在這個美學的體系里面,大家可能會覺得這些導演是一家人,在這場戲里你們是一個派對的,一個沙龍的人。
南都周刊:我個人特別喜歡的一場動物園的戲,拍的很夢幻,有一種身處于叢林之中的玄妙。那一段我覺得特別出彩。那段戲您是怎么構思的?
刁亦男:那這場戲是因為一則新聞,西安有個逃犯越獄了,全城的警察都在追捕他,—直沒有抓到,最終把他抓到審問他你藏在哪里了,他說我就藏在動物園的大象館里。這個片段一直在我的記憶里,我覺得拍出來一定會很好看。而且人和動物是平等的,人就是動物,公安就像是獵人一樣去捕獵嘛,燈光照亮在動物的眼睛上的時候它們會僵硬在那里,然后那時候你開槍,往往命中率很高。

南都周刊:對,這場戲既有現實的部分又感覺很魔幻,很出彩。另外,這是您第一次來戛納進入主競賽單元,受到了非常多的關注,您對這次戛納之行有怎樣的感受,有怎樣的期待昵?
刁亦男:戛納不像十幾年前或者更早的時候那么繁榮,大家都面臨同樣的困難。資金、市場、觀眾對藝術片的欣賞,不像以前那么充沛了,市場也沒有以前那么大了,我感覺很多公司都越變越小。這給我們一個信息,我們可以把電影拍得好看一些,同時可以把作者的表達揉進去,而不是說,我一定要拍一個博物館般的電影,這個電影只能在博物館里放映,或者這個電影只有非常小的受眾。我覺得完全拍給更多的觀眾看,也就是說作者電影、藝術電影可以拍的更加成熟,更加開放。
南都周刊:其實您剛才說的這些話和戛納主席福茂觀點比較類似,戛納也在轉型,力圖海納百川。
刁亦男:其實從我個人的感受來講,拍類型片是更難的。拍一些散文化的電影,只是需要個人的情懷和體驗,操作起來會相對容易。類型片會非常難,但是只有去進攻難的地帶,讓自己在創作上跳出安全區,去冒險,不怕失敗,才有可能去收獲新的改變。
南都周刊:最后一個問題,您現在有沒有新的拍片的計劃呢?
刁亦男:暫時還沒有新的拍片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