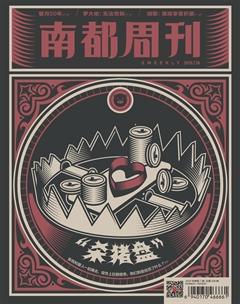各種段子橫飛,垃圾分類考驗(yàn)上海人
張豐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guó)各大城市都將開(kāi)展一場(chǎng)垃圾分類運(yùn)動(dòng)。上海是這場(chǎng)運(yùn)動(dòng)的橋頭堡,作為中國(guó)城市管理最好的城市,上海能否真正在垃圾分類上取得進(jìn)展,也決定了這一次能否在全國(guó)有效推廣。
這段時(shí)間,“垃圾”已成為上海人的口頭禪,產(chǎn)生了很多讓人發(fā)笑的段子。最經(jīng)典的是這樣的:早上去倒垃圾的時(shí)候,最怕阿姨問(wèn)這一句:你是什么垃圾?
還有那個(gè)經(jīng)典的教育難題,小朋友經(jīng)常問(wèn)父母自己是從哪兒來(lái)的。父母往往會(huì)回答:“垃圾桶里撿來(lái)的”。過(guò)去,小朋友聽(tīng)到后可能會(huì)難過(guò),未來(lái)則有可能接上一句:“是干垃圾還是濕垃圾?”
一個(gè)未驗(yàn)證的橫幅上則是這樣的內(nèi)容:“未按時(shí)間地點(diǎn)亂扔垃圾,你就是人群中的垃圾。”這個(gè)橫幅暗示出真正實(shí)現(xiàn)垃圾分類之后可能存在的人與人之間的沖突。
這些段子的流行,其實(shí)表明了上海人對(duì)這次垃圾分類的重視。在不少小區(qū)的業(yè)主群里,垃圾分類也成為爭(zhēng)論的熱門話題。不管將來(lái)成效如何,這一次最起碼在輿論上已經(jīng)做好了準(zhǔn)備,至少是擁有房產(chǎn)的中等收入人群,大多都意識(shí)到這場(chǎng)行動(dòng)一定和自己相關(guān)。
中國(guó)城市經(jīng)過(guò)了20年迅猛的、粗放式的發(fā)展,確實(shí)到了要解決垃圾問(wèn)題的時(shí)候。所有人都反感垃圾,但是大多數(shù)人對(duì)“垃圾分類”能否推行,仍有猶豫。2018年7月公布的“2017年度北京市民公共行為文明指數(shù)”,“垃圾分類”處理這一欄非常刺眼,它比上一年下跌了9.4%。
意味深長(zhǎng)的是,就在2017年,北京剛剛開(kāi)啟了新一輪“干濕分離”的垃圾分類推進(jìn)工作,五花八門的試點(diǎn)措施在各條胡同和街道里輪番上演。這個(gè)調(diào)查表明,如果方法不當(dāng),“垃圾分類”反而會(huì)帶來(lái)更嚴(yán)重的垃圾問(wèn)題。
中國(guó)人到了日本,往往會(huì)不知所措,因?yàn)楦静恢廊绾翁幚碜约寒a(chǎn)生的生活垃圾。日本街頭看不到垃圾桶,自己產(chǎn)生的垃圾要帶回家,進(jìn)行分類,然后再被運(yùn)走,據(jù)說(shuō)很多日本家庭的墻上,都貼著垃圾運(yùn)輸車到來(lái)的時(shí)間。厚厚的垃圾分類指南,成為每個(gè)日本人都必須掌握的現(xiàn)代分類知識(shí)。
我有一個(gè)朋友居住在大阪,她到京都去學(xué)習(xí)茶道。大家品嘗點(diǎn)心,也吃點(diǎn)花生。等學(xué)習(xí)結(jié)束,她會(huì)用紙把垃圾包起來(lái)收好帶回自己在大阪的家,這種行為,已經(jīng)內(nèi)化為大多數(shù)人的習(xí)慣。
這很讓人羨慕。但是,我們也必須知道,日本人也不是一個(gè)月甚至一年就能達(dá)到如今的水平。日本的垃圾分類從上世紀(jì)70年代開(kāi)始,那時(shí)候的日本剛剛經(jīng)歷了戰(zhàn)后長(zhǎng)時(shí)段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城市高度繁榮,也產(chǎn)生了相當(dāng)數(shù)量的垃圾。日本政府下定決心解決垃圾問(wèn)題,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四十多年,才達(dá)到了今天的文明程度。
說(shuō)到底,垃圾分類并不僅僅是居民的事,它是一個(gè)系統(tǒng)性工程,也是一個(gè)“產(chǎn)業(yè)鏈”。垃圾分類之后,還要進(jìn)行運(yùn)輸和專門的處理。《人行道王國(guó)》一書(shū)寫(xiě)那些紐約第六大道上擺攤的人,他們所賣的雜志大部分是從垃圾桶里撿來(lái)的,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從垃圾桶找出來(lái),這也得益于有效的垃圾分類。
最終,在社會(huì)層面,垃圾分類需要一個(gè)成熟的分工和處理體系;而在人的層面,則需要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我們可以稱之為“成熟社會(huì)”,一個(gè)國(guó)家在經(jīng)濟(jì)到了一定階段之后,必然要面臨這個(gè)問(wèn)題。
某種程度上講,中國(guó)的當(dāng)下和上世紀(jì)70年代的日本很像,崛起了一個(gè)以擁有房屋為標(biāo)志的城市中產(chǎn)階層,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達(dá)到一定水準(zhǔn),開(kāi)始想擁有“更美好的生活”。這包括生活習(xí)慣的改善(從肥胖轉(zhuǎn)向節(jié)制),也包括每一個(gè)人都要承擔(dān)屬于自己的責(zé)任(文明的水準(zhǔn))。
這樣對(duì)比,并不是要暗示中國(guó)解決垃圾分類還需要40年時(shí)間。中國(guó)的優(yōu)勢(shì)在于,社會(huì)分工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都要比上世紀(jì)70年代的日本更好,大數(shù)據(jù)和人工智能都可以用到垃圾處理上,獲得更佳的方案。疑問(wèn)在于,中國(guó)人需要多久才能養(yǎng)成一個(gè)“成熟社會(huì)”的好習(xí)慣,不再專注于“膨脹”,而是專注改善自己的生活細(xì)節(jié)。
這需要各方面的耐心。人們最擔(dān)心的,并不是接下來(lái)可能到來(lái)的嚴(yán)厲處罰,而是像過(guò)去一樣,這一次又是“一陣風(fēng)”刮過(guò),那只會(huì)留下新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