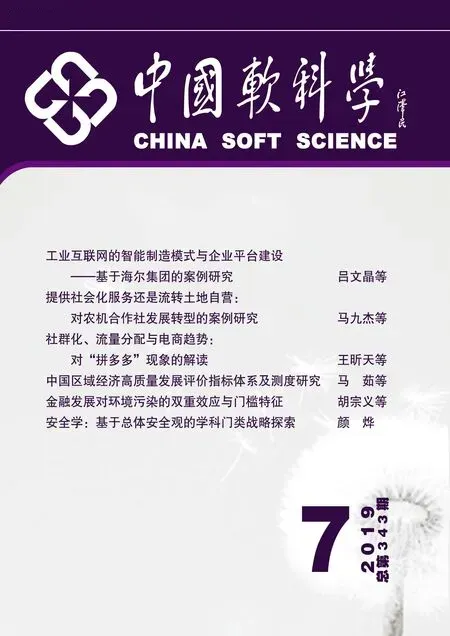變革型領導力與員工創新行為模式:基于促進定向的中介作用
李 淵,曲世友,徐 峰
(哈爾濱工業大學 管理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
一、引言
中美貿易戰持續發酵,各行各業都高度關注著這場國與國之間的較量。尤其是此次美國的七年禁令暴露出的中國缺“芯”之痛,一度成為輿論風口。貿易戰本質上是科技戰,再一次表明國家之間經濟的競爭,歸根結底是科技實力的競爭。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無縫持續的科技創新是保持競爭優勢的唯一途徑[1]。組織創新始于員工的創造性思維與主動行為。員工創新指在組織情境下員工產生的新穎而有用的想法,根據創新想法新意程度的不同,創新行為可以細分為漸進性創新和突破性創新[2]。突破性技術創新有助于企業在短期內取得行業領先地位甚至是壟斷地位,形成新的核心競爭力。因此,研究如何更好地促進突破性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當前我國制造業大多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從低端產品起家,向高端產品發展,只有立足于自主創新,才能夠加快制造業轉型升級。中國缺“芯”之痛再次提醒產業界需要將產業自主創新擺在十分重要的突出位置,始終把科技創新作為應對市場挑戰的戰略支點。當前形勢下,我國創新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正處于從數量級向質量升級的關鍵時期。目前,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總量居世界第二位,重大科技成果不斷涌現,創新性國家建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發布2017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國際排名從2016年的25位升到第22位,成為唯一一位進入前25名的中等收入國家。推動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支撐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最終還要推動“三個變革”,即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變革型領導力一直被認為是影響創新的關鍵組織因素之一[3]。學術界對于變革型領導力與創新之間的關系十分重視,研究成果也比較豐富,但是元分析結果卻并沒有表明變革型領導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有鑒于此,有學者質疑“變革型領導力——下屬創造力”這一簡單化模型的有效性[3]。創造力是創新的基本前提,因此,我們需要研究變革型領導力通過何種更為復雜的機制影響下屬創新行為。
創新作為人類智慧的高級表現形式,要求個體進行一系列復雜的、高強度的認知加工過程。如果員工進行獨立思考與探索,便可能會創新。但如果員工追求某種目標(例如安全、生產效率),便不會參與創新尤其是突破性創新。因此,員工本人的創新定位是員工參與創新的基本條件之一。目前,還沒研究結合變革型領導力理論與調節定向理論對員工創新行為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
二、理論與假設
(一)變革型領導力與創新行為模式
領導力行為是指領導者引導、激發下屬對組織目標負責的能力,我們也可以把領導力理解為一種組織內的人際關系和影響力[4]。根據全方位領導力理論[5],領導力行為主要包括:第一,交易型領導力,以獎勵為基礎的交易行為從而實現激勵目的。第二,變革型領導力,內在地激勵下屬從而實現員工的自我監督自我管理,使下屬發自內心的意識到組織目標的重要性,激發他們高層次的精神需求,這將促進團隊努力,激發個人創造力和組織變革,并促使管理層持續探索成功領導者所需要的素質,如溝通能力、鼓舞力和感染力。
Bass[6]認為,變革型領導力行為由四個維度組成,即理想化的影響力、感召力、智力激發、個性化關照。一般來說,在企業的規章制度中很難體現變革型領導力的這些維度,其主要體現了下屬與領導層之間的情感聯系。Rubin等人[7]認為,變革型領導力行為代表著最有活力、最有效的領導形式,從而有助于實現創新。研究表明,變革型領導力行為旨在改變現狀,實現組織的變革,徹底的改變原有的基礎架構和資源組合,可以明顯地促進創新[8]。總體上,我們認為變革型領導力將在以下幾個方面促進突破性創新和漸進性創新。
首先,變革型領導通過意識形態感召力建立集體認同感,從而影響下屬的價值觀[9]。與外部激勵相比,變革型領導通過意識形態的解釋使得下屬的價值觀接近集體價值觀,這使得下屬能夠清楚地了解組織的戰略目標并建立集體認同感[10]。此外,研究表明,內在動力足、組織認同度高的員工更可能主動找到實現組織目標的新方法[11]。基于這些研究基礎,我們認為變革型領導力在情感層面促進了突破性創新和漸進性創新。
其次,在實踐層面上,變革型領導通過改變下屬已有的觀念來改變下屬的思維方式,同時引導下屬反思自己的思考過程,這就是變革型領導的智力激發方式。變革型領導鼓勵下屬從新的角度思考舊問題并樹立榜樣。個性化關照是指變革型領導以獨特的方式照顧他們的下屬,同情、贊賞和支持,從而讓下屬們勇于大膽地嘗試驗證新的想法[12]。研究表明,變革型領導通過引導和鼓勵可以顯著地提高下屬對于實現長久目標的承諾和保證[11]。
此外,我們認為變革型領導在組織文化和團隊工作的層面上同樣影響了組織創新。一種支持組織創新的文化氛圍會鼓勵科研人員在團隊內部發展新的知識和創意[13]。因此,變革型領導同樣會影響到下屬的風險定位。此外,變革型領導的個性化的關照行為會致力于為下屬的發展提供信息和資源,促進他們的學習和互動。因此,下屬更有可能形成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且進行創新。當組織文化支持創新行為時,下屬會在預期風險內傾向于從事更多的創業行為。Nielsen等人[14]認為創業行為包括四個要素:積極性、風險性、自主性和競爭性。他通過五家企業的案例研究發現,積極性、風險性、自主性和突破性創新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競爭性與突破性創新之間的關系并不明顯。Waldman[15]認為,變革型領導力在面臨創新需求的高強度研發領域這種不穩定的環境下能夠顯著地提升員工創新行為。
鑒于上述論點,我們認為,變革型領導有助于促進創新行為,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1:變革型領導力對員工突破性創新行為有積極的影響。
H2:變革型領導力對員工漸進性創新行為有積極的影響。
根據員工所提出創新想法新穎程度的不同,創新行為可以細分為漸進性創新行為和突破性創新行為[2]。突破性創新的技術范式和商業模式都與過去完全不同,這種新的范式破壞了原有的生產和管理模式,以及現有的資源組合,因此這種創新也被稱為破壞性創新。在成本投入和回報周期上,突破性創新的不確定性高于漸進式創新[16]。與突破性創新相比,漸進式創新是基于現有資源和能力,具有持續進步的特點。突破性創新會破壞現有資源組合和市場規則,具有不連續特征,因此可能會影響到一些利益相關者(政府,投資者等)的收益[17]。
對于漸進性創新與突破性創新的關系,Beck等[18]的研究認為,漸進性創新并不會影響到突破性創新。科爾曼認為,這兩種類型的創新是在不同的層次上進行的,因此,不會產生資源爭奪等沖突。而漸進性創新所帶來的改進進化過程,使得產品的成本與績效得以提高,為企業帶來了利潤。企業的績效改善,能夠有更大能力進行突破性創新。
企業創新的核心能力是不斷改變以適應需求的能力,因此我們認為,漸進性創新的累積,有助于企業突破性創新的實現,而且Ortiz-Villajos[19]通過對創新管理的文獻研究發現公司的經驗對于創新成功至關重要。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3:漸進性創新行為有助于促進突破性創新行為。

圖1 模型1:變革型領導力與創新模式的關系
(二)促進定向, 突破性創新行為,漸進性創新行為
Higgins的調節定向理論[20]區分了兩種在實現目標過程中的自我調節方式。其中,“促進定向”源于個人的理想導向,主要與員工本人提升自我的需求相關。“預防定向”源于個人的責任導向,主要與員工本人的安全需求有關。促進定向體現出了個人對自身成長、進步提高、取得成就的關切,而預防定向是對獲得保障、安全感,個人責任的關切。
促進定向與想要取得的成果密切相關,預防定向與竭力避免的后果相關。研究表明,懷有強烈的促進定向的個人對新成果的取得或者失去都會十分敏感,同時能夠謹慎識別機會,并且采用逼近的、迫切的戰略向著目標邁進[21]。當人們處于促進定向時,他們會盡力實現自身的成長與發展。在內在動力的驅動下,他們會追求代表自己信仰與理想的目標。因此,當出現的情況對目標構成影響時,促進定向的人會立即產生警覺性。
因此,員工的促進定向與事業心、風險承擔密切相關,因此會影響到員工創新的行為方式,尤其是突破性創新。促進定向型的員工會更愿意承擔失敗的風險,更愿意嘗試創新的方法,也更愿意把創造性的想法付諸實踐。在實驗室環境中,促進定向有利于創意的產生以及形成創造性的視野[22]。在現場研究中, Neubert等[23]表明員工的促進定向與創造性行為正相關。因此我們提出:
H4:員工的促進定向促進了的員工的突破性創新行為。
H5:員工的促進定向促進了的員工的漸進性創新行為。
個體的調節定向由固定部分(本質構成)和情境部分(外部塑造)兩個部分所構成[24]。其中固定的部分體現了一個人可能的促進定向或者預防定向的基本趨勢。這個基本的趨勢通常由童年時期的教育所塑造。例如當父母鼓勵孩子去追求理想與抱負時,當孩子成年以后,更有可能會成為促進定向型的人。另外,實驗的研究也證明了情境變量塑造了一個人調節定向的情境的(狀態)部分。因此一個人所處的環境會導致特定的調節定向。當一個人所處于的環境能夠引導促進定向時候,那么此人在工作中會更有可能成為促進定向型的人。有研究認為[22]與組織內領導的日常交流是一個人調節定向形成的重要源頭。變革型領導力鼓勵下屬個人成長與發展,更可能引發促進定向。與領導有著共同愿景的員工更可能發展與完善自己,而與變革型領導理念一致的員工則更加關注積極的結果。類似的,Wang等[25]認為變革型領導提供了一種讓員工專注于任務和目標而非安全擔憂的工作環境,因此我們認為變革型領導會影響到下屬的調節定向形成。Collins等[26]認為員工的促進定向有可能在變革型領導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起到了中介作用。因此我們認為:
H6:員工的促進定向在變革型領導力與創新行為之間起到了中介作用。

圖2 模型2:變革型領導力、促進定向與創新行為的關系
三、研究方法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采集
這些數據來自上海、北京的9家企業、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產學研合作創新團隊。接受調查的人員所在單位創新文化氛圍濃厚,員工需要積極地進行創新,因此本研究選擇的組織背景適合于考察變革型領導力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的關系。對于變革型領導力行為的評價、促進定向水平評估都是來自于員工本身,而員工的創新行為則由員工的主管評定。我們的問卷通過線上與線下同時進行,同時盡可能地采用電話方式聯系以便快速溝通。本研究的樣本主要來自產業技術領域,由于受訪者所從事工作性質的特殊性,我們保證問卷調查的保密性。通過三輪的發放共發出300對問卷,回收到了215對,其中有23份問卷包含空白項,因此我們最終確定的數據集包括了192對有效回復,有效回收率為64%。
(二)測量指標
本文的待測量變量指標包括變革型領導力、促進定向、漸進性創新、突破性創新。為了更好地完成測量,本研究采用學術界成熟的測量量表,同時由兩名雙語專家分別完成翻譯-回譯工作以確保量表內涵的一致性。作為解釋變量變革型領導力,我們采用測量領導力最常用的MLQ問卷[27]。MLQ在測量變革型領導力時候,總共包括四個維度。對于促進定向的測量,我們采用了Lockwood等人[27]的測量量表,測量項目共9項。漸進式創新行為和突破性創新行為的指標選取參考之前研究成果[28],各包含三個項目。以上量表的評分標準均采用七點Likert式量表,從1(非常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
(三)控制變量
在模型中存在一些可能會影響到模型關系的變量。例如,下屬的感知變革型領導力可能會受到上下級共事年限影響,一般來說共事年限越久,下屬對領導的行為方式可能越了解,我們用年數作為衡量標準,本項研究中上下級平均共事年限5.21年(SD=4.20)。其次,研發人員的性別可能也會影響到對變量的衡量,在測量時,用0代表男性,1代表女性,其中參與調查的男性科研人員比例為74.6%,女性為25.4%,平均年齡為35.14(SD=8.21)。此外,團隊規模也是學術界研究關系層面時常常參考的控制變量,其中團隊規模用所在團隊人數來衡量。在本項的研究中,我們把這些變量作為外生變量來研究它們可能對模型關系造成的影響。
(四)估計方法
為了驗證所提出的模型與假設,我們采用了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結構方程模型來驗證假設。Smart-PLS擅長處理非正態分布數據、小樣本數據、形成性測量模型、單一測量指標的處理。此外,SmartPLS對于結果的輸出也有獨特之處,例如可以直接生成內部一致性信度、組合信度、AVE、區別效度等。因此,用來處理我們的樣本數據是合適的[29]。
四、結果
運用PLS-SEM方法對模型的分析和解釋的主要包括兩個步驟[30]。首先,對測量模型的效度與信度進行了分析。其次,對結構模型的進行了系數的估計,以驗證本文的假設。
(一)測量模型
在本文的模型中包含反映性指標和形成性指標,其中,測量變革型領導力與促進定向的指標是反映性指標,測量創新模式的指標屬于形成性指標。
對于反映性指標變革型領導力與促進定向,我們通過標準化因子載荷系數,構念的信度以及AVE數值來衡量其收斂效度。在本項研究中,變革型領導力與促進定向指標標準化因子載荷系數都超過了0.80,并且在0.01水平上顯著,因子載荷系數滿足標準。在顯著性檢驗方面,我們采用Bootstrap方法,樣本數量設定為500個[31]。
對于構念的信度與效度,我們通過計算綜合信度值CR以及平均提取方差值 AVE ,結果顯示,CR與AVE指標均高于閾值0.6與0.5[32]。對于每個構念及其子維度的CR與AVE數值參見表 1。
對于反映性指標的區別效度,我們采用交叉因子載荷的方法。結果顯示,每個測量項對于本身構念的因子載荷高于其他構念。其次,我們進一步檢驗了潛變量各維度間完全標準化相關系數與所涉及各維度自身AVE的平方根值大小,結果顯示前者小于后者,表明各維度間存在足夠的區分效度[28]。對于各構念的交叉因子載荷系數在表2中有詳細顯示。

表1 反映性指標的收斂效度
注:α= Cronbach’sα,CR=Composite reliability,AVE=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

表2 反映性指標的交叉因子載荷


表3 形成性指標的多重共線性測量
(二)結構模型
對于結構模型的分析包含驗證文中假設所提出的因果關系以及對路徑系數的估計。在對模型的結構估計時,圖3顯示了本文對模型1路徑參數估計的主要結果,包括變革型領導力與創新模式的關系。圖3的路徑系數展示了模型變量之間的關系。對于結構方程路徑系數的評價,我們參考Chin[32]的評價標準。

圖3 模型1的路徑估計標準化參數注:**p < 0.01,n = 192。
從圖3的structural coefficient我們可以看出,變革型領導力對于兩種創新的作用都是很強,而且影響強度比較相近,并且都超過了0.2(β=0.236,β=0.258)。相比較之下,漸進性創新對于突破性創新的作用關系最強(β= 0.319)。在0.01水平上,這些作用關系都是顯著的。對于R2值,都超過了15%,其中突破性創新27.1%,漸進性創新18.3%。因此,突破性創新得到的解釋力要強于漸進性創新。控制變量對模型的影響有所差異,上下級共事年限和性別對模型關系的作用相反,但是不顯著,而團隊規模對于模型關系的影響呈負向。
為了對我們的結果的顯著性進行驗證,我們采用了非參數的Bootstrapping方法[33],從原始樣本中抽取了1000個,在95%的置信區間中,所有的路徑估計都是顯著的,證明了研究結果的魯棒性。結果見表4。

表4 模型2 Bootstrap 結果
注:**p < 0.01,*p < 0.05。
為了驗證促進定向的中介作用,我們引入了潛變量調節定向。對于路徑估計的標準化參數以及R2值,參見圖4。

圖4 模型2的路徑估計標準化參數注:N = 192, **p < 0.01, *p < 0.05。
從圖4可以通過路徑系數看出變量之間的關系強度,其中變革型領導力對于兩種創新類型的作用由于個體層面的促進定向作用發生了變化。對于突破性創新的作用仍然是正向的(β=0.106),但是已經不再顯著,而變革型領導力對于漸進性創新的直接效用相對于模型1有所減弱(β=0.217)。其中促進定向的中介作用明顯,結果表明變革型領導力對促進定向顯著正向相關(β=0.463),而促進定向對于創新模式的影響更為明顯(β=0.586,β=0.474)。由于潛變量促進定向的引入,漸進性創新對于突破性創新的作用有所減弱(β=0.247)。與模型1相比,控制變量的影響性質沒有發生改變,團隊規模的影響程度有所增大。
此外,與模型1相比,R2值顯著變大,因此,可以說明加入促進定向的調節作用之后,模型的解釋力更強了。其中,在具體數值上,突破性創新的R2值達到了0.573,而漸進性創新的達到了0.421,促進定向的R2數值為0.336。對于模型結果的Bootstrap分析,見表5。

表5 模型2 Bootstrap 結果
注: n = 192,**p < 0.01,*p < 0.05。
五、結論
(一)討論
通過對結構模型的結果分析,我們驗證了本文假設的有效性。在模型1中,變革型領導力對員工突破性創新行為與漸進性創新行為,都是呈正相關的關系,因此假設1和2都得到了支持。相對于突破性創新行為,變革型領導力對于漸進性創新行為的作用更為明顯,盡管這種區別不是很大(β=0.236,β=0.258)。在這些關系中,關系最強的是漸進性創新行為對于突破性創新行為的作用,假設3也得到了支持,說明創新需要一個過程,員工的突破性創新行為,不僅僅需要團隊層面的領導力配合,更需要自己本身的長期投入和積累。
在模型2中驗證了促進定向的中介效應。由于促進定向的中介作用,變革型領導力對突破性創新行為的效應變的不再顯著,因此變革型領導力對于突破性創新行為的作用被促進定向完全中介,說明變革型領導力對突破性創新行為的影響,需要依賴于個人層面的促進定向因素發揮作用。同時由于促進定向的引入,變革型領導力對于漸進性創新的直接作用減弱,但是在0.05的水平上仍然顯著,說明變革型領導力對于漸進性創新的影響力更強。
促進定向對突破性創新行為與漸進性創新行為的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效應(β=0.586,β=0.474),充分說明員工的促進定向對于員工創新行為的重要作用。而變革型領導顯著提升促進定向的關系說明促進定向在變革型領導力與創新行為的作用中間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同時,由于促進定向的存在,漸進性創新行為對于突破性創新行為的作用有所減弱,而突破性創新的R2值顯著增大,說明了促進定向與漸進性創新行為對于突破性創新行為的重要意義。在模型2中,漸進性創新行為與突破性創新行為的R2值相比于模型1明顯增大,說明引入促進定向的中介效應以后,模型的解釋力增強了,同時也說明了促進定向的重要性與模型的有效性。同時,通過對控制變量的分析表明,隨著團隊規模的增大,會負面影響到團隊關系,因此在規模較大的團隊中,尤其應當關注管理層與員工的聯系。
(二)理論貢獻與管理實踐意義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創新行為不僅僅是知識加工與認知處理的行為,組織層面的非技術因素如領導力以及個人層面的創新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創新需要依靠雙輪驅動,即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或者說科技創新與全面創新,變革型領力建設即是體制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變革型領導力在對員工創新行為起到的作用顯著,培養、構建管理層變革型領導力對于組織取得突破性創新、實現動力變革、效率變革、質量變革,努力打造先發優勢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研究了員工的促進定向在變革型領導力與創新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促進定向在變革型領導力與突破性創新行為之間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在變革型領導力與漸進性創新行為之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前者的完全中介作用說了調節定向對于突破性創新行為的重要作用,加之后者的部分中介作用,充分說明了促進定向的中介作用顯著。因此,基于被管理者的視角,我們研究了感知變革型領導力與調節定向對于不同創新行為的復雜作用機制。關注、培養科研工作者的促進定向調節有助于知識型員工協同合作,可以更好地激發研發人員的創造力從而促進突破性創新。
變革型領導力對促進定向的正面作用表明,我們不僅需要從情境的角度去理解個人促進定向養成,還要從變革型領導力的角度去理解促進定向理論,發展戰略領導理論。對于漸進性創新行為對于突破性創新行為的相關性,進一步豐富了創新行為理論,有助于我們理解創新行為的漸進與突變的關系。學術界目前對于突破性創新行為的研究還有待于豐富,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漸進性創新行為與突破性創新行為的內涵不應被割裂開來。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科技創新在我國現代經濟體系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逐步增強。其中大數據、智能化為引領的創新行動帶動了產業的轉型升級,推動了經濟發展的質量變革、效益變革和動力變革。本文的研究契合了當下科技創新的發展潮流,為創新模式注入了新的發展理念。
在管理實踐方面,本文的研究結果將給我們帶來以下啟示。
首先,員工創新不僅僅需要資金的支持,知識管理機制的構建,更需要從組織層面加大變革型領導力的建設,從而激發組織活躍的創新思想與建設理性懷疑、挑戰權威、敢為人先、寬容失敗的創新文化。變革型領導力對于促進定向,創新行為的作用顯著。因為本文是基于被管理者視角開展的研究,因此我們更要關注科研發人員的感知變革型領導力,做好管理層與研發人員的溝通交流工作,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促進知識資源高效配置。其次,人力資源是最寶貴的資源,人是最重要的載體。促進定向的顯著的中介作用表明,更加努力地關注、培養科研員工的促進定向調節,可以顯著的影響到員工創新行為。同時,組織應該盡可能的通過相關檢測,選拔出促進定向水平更高的員工參與創新。最后,突破性創新往往能快速帶動產業升級,但是學術界普遍認為突破性創新的難度高于漸進性創新。我們不應當將突破性創新與漸進性創新的內涵割裂開來。通過重視漸進性創新行為,會促進突破性創新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