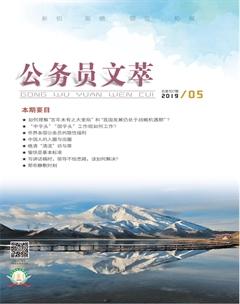清代的上訪
杜君立
如果從“三代”算起,中國古代政治堪稱早熟,很早就設有各種“直訴”制度。也就是說,有案情重大、冤抑莫伸者,可越過一般受訴官司和申訴程序,直接向最高統治者陳訴。作為一種讓底層民眾伸冤訴苦的司法救濟制度,直訴制度源于周朝,隋唐時代臻于完善,明清時代發展到巔峰,最后終結于清朝“京控”。
清朝將上訪分為上控、京控和叩閽。凡審級,直省以州縣正印官為初審。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訴者笞。上控是對地方衙門的審判不服,向上一級衙門申訴的制度;而“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軍統領衙門呈訴者,名曰京控”。京控就是上京城告狀。《清史稿·刑法志》說:“其投廳擊鼓,或遇乘輿出郊,迎擊駕申訴者,名曰‘叩閽。”“叩閽”的主要方式就是告御狀。京控是在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通政司等處投遞呈詞,而叩閽則是直接跪拜宮門,或是叩謁皇帝車駕。相對于京控,叩閽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比如康熙皇帝對叩閽尚屬寬容,乾隆皇帝對叩閽處罰卻很重,即使得實也可能獲罪;相反,京控得實者可以得到“免議”的結果,即使誣告,有時候獲罪也不重。因此,上訪者大多選擇京控而不是叩閽。
京控承繼的是兩千年來歷代王朝的直訴制度,其創建指的是清代將京控制度的呈告、受理、奏交、咨交、發審的整體流程完備。在明代,叩閽并非訴訟常態,清代已經是一個常態,甚至可以說是呈控者啟動案件重審的主要方法之一。
一
韓非的《忠孝》說:“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中國古代以忠孝治天下。在中國歷史的帝國語境中,告御狀本身就是以小犯上的大逆不道之罪,因此很難獲得帝國實質的同情和支持。皇權時代的中國統治者要向臣民顯現“青天”形象,讓人相信問題出在地方官員身上,皇帝還是英明的,所以要給臣民一個來京告狀的合法渠道。但事實上,皇帝也未必相信并同情這些京控的呈控者。
二
古代政府對上訪戶越級控告,事情屬實的,給予改判;如若虛假,就要懲罰。到了清代,“京控”不實的話,將以越級上訴為由,加等治罪,誣告者反坐。此外,清代法律在認可平民上訴上訪權利的同時,又制定律法,不許民眾“假地方公事聚眾聯謀、約會抗糧、聚錢構訟”,以及“代人捏寫本狀、教唆扛幫赴京”。這些預設性的罪名,幾乎成了地方官吏和豪強截訪抓人的最佳借口。
清代對于京控的處理流程有明確規定:都察院接受上訪后,認為情節較重的向皇帝具奏;情節較輕的,受理之后再轉回各省總督、巡撫辦理。都察院和步軍統領衙門,每年兩次催告各省逾期未結的案子,并向皇帝匯報。相對而言,將案件發交地方督撫審理是最為便利的方式。但有些皇帝比較重視民間控告,乃至直接委派欽差審案。嘉慶皇帝不許官員限制百姓京控,甚至稱自己有時間的話會審閱每起京控案的卷宗;道光皇帝曾這樣要求各省督撫將軍都統,“遇有京控事件,務須親為聽斷。冤抑者立予伸理,刁誣者從嚴懲治。其有任意延宕不結者,即將提解逾限之員、先行參辦”。京控數量在乾隆年間逐年增長,嘉慶皇帝親政初期,銳意振興帝國,廣開言路,使京控如潮水般涌來。
三
中國傳統社會一直以官民對立為最大矛盾;用馬克思的觀點,就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階級斗爭。在這種背景下,皇帝不信任官吏、中央不信任地方、官吏不信任民眾;當然,民眾更不信任官吏。一物降一物,有時候,這種“不信任”跟“老虎—棒子—雞”的游戲一樣,會出現民眾不得不“信任”皇帝的吊詭結果;但實際上,即使皇帝,也還得依靠官吏來解決問題。因此,無論任何形式的上訪和京控,都無法打破“官官相護”的困境,正如李典蓉在《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一書的最后所說:
上控成功與司法正義得到伸張,并不能畫上等號。表面上,清朝中央建立的京控制度,保護的是允許百姓上控的傳統;在地方的實際操作里,主要保護的卻是官僚的烏紗帽。
日本學者寺田浩明認為,中國不像西方有“權利”的概念,中國人訴訟的內涵是“伸冤”。上訪和京控是官方對當事人向地方官權威提出質疑的制度安排,最終目的是為了追求“天下至公”;換言之,京控制度本身有著德政的寓意,也有預防官吏為非作歹、借百姓申訴以監察官員的意圖。
四
自古以來,“無訟”一直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所追求的“治世”。
這個美好理想在現實中,卻扭曲變成對訴訟的壓抑與打擊。“無訟”“息訟”和“終訟”的背后,其實是“惡訟”“畏訟”“禁訟”和“壓訟”。不少地方官員一開始,就認定京控原告“有罪”,甚至為了“息訟”,而不惜“截訪”——古代叫“截拿”,結果“這些進京上控伸冤的原告往往處于最不利的地位”。
就京控制度而言,其象征意義遠遠大于實際意義。百姓來告御狀,無疑表達了一種對最高權威的承認和信任。但當京控者紛至沓來,案件堆積如山時,皇帝又難免心生厭煩。
清朝前期,大多數京控案件尚能到達皇帝面前。乾隆時期,則多交大臣和有關部門處理,或派欽差大員赴地方審理京控案件。嘉慶后,直接將京控案件交由地方督撫大員審理的情況越來越多。
五
與康熙朝相比,乾隆時代京控、叩閽的數量大為增加,而且花樣迭出。
乾隆帝的一生,對官僚組織的營造和管理堪稱中國皇權模式的典范。在君主—官僚制度下,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種權力沖突:即君主所代表的專制權力與官僚代表的常規權力之間的矛盾。在這一種體制下,專制權力與常規權力其實是共生關系,皇帝認為自己是整個官僚體系的主人,而非只是其中的一個齒輪,即管官的“官”,而不是最大的官。為此,皇帝一方面要制定更多的規則來制約官僚,另一方面則是采用特殊渠道(如一些例外和偶然的事件等),來反復驗證自己對官僚體系的操縱力。對官僚組織來說,他們希望一切都確定在自己權力控制之內,而上控事件導致的結果則是非常規的、不確定的、不可控的,也是最令官僚體系不安的。對任何皇帝來說,太多官僚體制外的非正常訴求,必然會使整個官僚體系陷入混亂,所以皇帝不得不在鼓勵上控與打壓上控之間,謹慎地尋求微妙的平衡。
中國古人認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官不貪,則民無冤;民無冤,則天下安。傳統禮法社會要求的是“和諧”和“穩定”,而不是正義和公正,任何打破這種和諧穩定的舉動和聲音,無論正當還是不正當,有理還是無理,都會被視為“不安分”的、“好訟”的“刁民”。幾乎在所有的京控案件中,被告不一定會獲罪,但原告一定會獲罪,這常常是由京控者的身份決定的。
在清代的司法審判活動中,平反的冤獄和實際存在的冤獄比較起來,實在是微乎其微。
(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