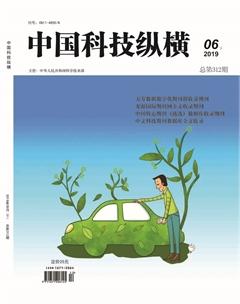網絡直播用工關系的勞動法思考
汪東澎
摘 要:伴隨著互聯網和智能移動終端的不斷發展,網絡直播已經成為全民性的活動。而網紅、主播等也成為了名利雙收的高收入群體,但是必須要正視的問題是,在網絡直播行業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形式背后,是網絡主播尋求勞動法保護基本勞動權益的漫長過程,對于勞動關系的認定難度較高。本文主要討論網絡用工困局,通過分析原因以及國外先進的經驗,從而探討網絡直播用工糾紛問題立法的未來走向,以供參考。
關鍵詞:網絡直播;用工關系;勞動法
中圖分類號:D92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2064(2019)12-0232-02
0 引言
進入信息時代,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對于傳統的社會生產模式產生沖擊,催生了更多新型行業,網絡直播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在信息時代到來后,生產方式和工作模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遠程工作模式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因此催生了網絡直播行業,用工者與勞動者聯系程度弱化,對于這種新型用工關系,我國現行勞動法并沒有很好的規范和保障,因此應當如何平衡網絡直播用工方和雇傭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成為當下亟需解決的問題。
1 勞動法在網絡直播用工方面面臨的問題
在信息高速發展的當下,第三產業獲得了長足發展,工作模式不再依靠固定的場所進行生產運營,用工者與勞動者之間的聯系相對較弱。現行勞動法對于新型行業不能做到全覆蓋,因此在網絡直播用工方面面臨著一定的困境,具體表現如下:
1.1 網絡主播與經紀公司之間用工存有爭議
由于網絡直播工作方式的特殊性,主播與經濟公司的合作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經紀公司向其他平臺輸出主播,另一種是經紀公司自行簽約主播[1]。無論是哪種模式,雙方通常都會限定直播時間、人氣、底薪,甚至是關于考勤和出勤率等的規定,而這些規定卻沒有相關法律進行規范和保障,因此成為雙方爭議的焦點。
通常勞動者也就是主播認為雙方無論哪種合作模式,都屬于勞動法調整的范圍之內,而其中對于出勤率等要求是體現了公司對于勞動者進行管理的規定,而不能私自去其他平臺直播則體現了勞動關系從屬性,最主要的是單位盈利來源于主播工作收入提成,因此理應在勞動法調整范圍之內。但是對于經濟公司來說,認為主播工作模式靈活度高,因此勞動管理規章不適用于主播,而且主播薪酬由粉絲打賞決定,單位只是從中抽成,因此不適用于勞動法調整范圍。因此很多經濟公司在與主播簽約時,都會注明不按照勞動關系計算工資等條款,來規避勞動法的管轄,否認勞動關系也就造成了后期主播維權無路的狀況。
1.2 傳統勞動關系與網絡直播用工之間存在差異
“互聯網+”的時代背景之下催生的新型產業與傳統產業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生產方式和勞動關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就網絡直播用工來說,與傳統用工主要有幾點不同:
(1)給付方式不同。在傳統工業時期,集體化的勞動方式是勞動者集中在固定的工作場所,由用工者提供生產資料,在統一時間內勞動者提供勞動的方式,被稱為從屬勞動。而網絡直播用工則是由主播自行確定勞動地點、設備,經濟單位提供平臺,與傳統的勞動方式有著本質性的差別。(2)對于單位從屬性的區別。在傳統的勞動關系中,勞動者的工作方式和地點、內容受用人單位指派,用人單位對于勞動者有一系列的制度進行管理,對于勞動者的職務高低、薪酬高低有決定權,勞動者對于用人單位的從屬性較強[2]。但是在網絡直播這種新型的勞務關系中,主播對于工作有很強的決策權,經濟公司除了前期包裝培訓需要對主播進行一定管控之外,其余工作內容和時間都可以由網絡主播自行決定,勞務報酬按照主播引流能力決定,主播對于經紀公司的從屬性相對較弱。
2 網絡直播雇傭群體尋求勞動法維權困難的原因
網絡直播行業的興起勢頭較猛,同時行業穩定性相對較差。從經濟公司方面來說,為了牽制主播避免跳槽,以違約責任條款作為約束的重點,這在很多糾紛中也有所體現,但是如果套用勞動合同法,如果沒有服務器性質條款作為前提,那么主播跳槽行為是不用付違約金的。反過來從主播方面來說,網絡直播行業工作強度較大,近九成主播都患有職業病,但是經紀公司卻沒有如五險一金等保障措施,這也是雙方糾紛的重要原因之一。主播群體維權困難,主要原因總結如下:
2.1 現行勞動法對于新工種兼容性差
我國現行勞動法對于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有兩種定位,符合勞動關系標準的從業人員稱之為勞動者,對其保護適用于勞動法所有的規則;對于不符合勞動關系標準的從業人員與單位之間的關系則被籠統的定義為勞務關系,由合同法進行裁定,一切按照合同條款進行判斷[3]。但是就當下用工市場而言,非標準化特征日益明顯,非標準化就業方式也越來越多,但是現行的勞動法卻與多元化的用工方式難以兼容,其主要原因總結如下:
(1)單一調整模式忽略了用工方式的差異化。所謂單一調整模式的意思就是一種判斷標準,這種標準的指定背景是工業時代集體化勞動時期。而此前勞動法在國企改制期間曾做過改動,將用人單位放在了較為強勢的地位上,因此只要是勞動者自行決定工作,那么就不符合勞動法調和不平等的用意,從而不適用于勞動法。現行勞動法忽略了當下用工方式的差異化特點,依然是非黑即白的判斷方式,只判斷有無從屬性,而沒有對于從屬性強弱的判斷,因此當下網絡直播的用工方式由于從屬性較弱,實質上是游離于勞動法保護之外的。(2)對于勞動關系做不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現行勞動法單一的調整模式對于所有形式的勞動關系都是同等對待,劃分方式按照工作時間、工作內容,很難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4]。符合從屬標準的籠統的適用于《勞動法》,不符合從屬標準的則粗放的歸類于《勞動合同法》管轄范圍,造成當下網絡直播用工所采用的合作協議,有意規避勞動法的管轄以減少用工方面的成本,侵害主播的權益。
2.2 標準界定不清,勞動關系認定難度較高
由于我國對于新型用工方式并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因此將其置于傳統勞動關系的法律體系內進行審視,用勞動法傳統標準涵蓋非典型的用工關系,強行用抽象標準分析具體的個案,如不符合則將其排除。這樣的做法限制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余地。由于網絡直播在實際的用工中其特性偏離勞動關系的標準,因此不用勞動法作為衡量標準,這其中也有很多的弊端,具體總結如下:
(1)抽象性規則并不具有普遍性。在信息時代的影響下,彈性化工作成為當下主流工作方式之一,而勞動法相關規定逐步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現行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有一定的滯后性,其相關的標準和規定在新興行業、新興工種之下很難有放之四海皆準的抽象性規則[5]。(2)對于法律抽象概念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釋,法律并沒有嚴格的界定,而且由于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存在一定的滯后性,與當下新興行業發展不相符,因此抽象性規則并不能徹底解決網絡直播用工的問題,保障主播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3 網絡直播用工糾紛立法方面未來的走勢分析
如上所述,網絡直播用工的相關立法并不健全,而是套用勞動合同法進行裁定,因此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建設法治社會,要與時俱進,法律的規定要跟上時代步伐,結合國外的相關立法經驗,因此對于網絡直播用工糾紛立法方面未來走勢分析如下:
3.1 順應新型用工方式,重修 《勞動法》
伴隨著改革開放,國家逐漸減少對市場的把控和干預,而彈性化的用工方式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誕生的,窺一斑而見全豹,網絡直播只不過是這種新型用工方式的縮影,因此重視主播的權益,規范網絡直播用工的法律關系,是時代的要求。而且已經有很多國家在立法方面走在了前面:
德意兩國采取的勞動法是三分結構,不同的是德國在勞動法立法之初就采用的三分結構體系,而意大利則是經歷了從二分到三分的轉變過程。所謂三分結構體系,就是在勞動關系中,更加傾向于勞動者、自主勞動中平等對待雙方、不完全傾斜保護類似勞動者三種。三分結構體系的優勢就在于判定標準是以從屬性強弱來區分保護不同用工關系中勞動者,相比于國內單一的調整模式,覆蓋面更廣,對于新型產業的用工關系有較為明細的法律界定。美國采取的是用雇傭關系來闡述勞動關系的《公平勞動標準法案》,與德意兩國的三分結構體系不同,美國的標準整體來說是給法官造法的空間以適應社會新工種,靈活性較強。在美國,泛化認定勞動關系需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要與實際中個案相結合,也就是說同一個類型的非典型勞動關系在不同的案子中,結合實際情況可能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6]。
相比較之下,美國的泛化認定勞動關系的模式不需要對勞動法進行整體的修改和調整。但是結合我國實際情況而言,德意兩國的三分結構調整法更有參考意義。將勞動關系按照從屬性強弱進行劃分,覆蓋面相對較為廣泛,不但可以應用于當下,甚至對未來出現新型工種的勞動關系界定也相對較為容易。
3.2 制定下位法規范網絡直播用工關系
規范網絡直播環境,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勢在必行,相比于全面修改勞動法這種“傷筋動骨”的方式,制定下位法調整網絡直播用工方式則更加柔和有效。也就是說,《勞動法》目前的體系不用做更改,規范網絡直播通過頒布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的辦法來執行。就比如此前網約車領域所做出的的調整,交通、工信、公安等七部委發布了對于網約出租車經營服務管理的暫行辦法,對于駕駛員和網約車平臺的用工關系做出了規定,根據雙方簽訂的合同不同來界定雙方勞動關系,從而由不同法律進行調整,也就是上面所說的為抽象的標準提供了具體的參考案例。網絡直播也可以采用這種模式進行調整,二者均屬于從屬性弱的勞動關系類型,因此可以允許這種新型工種按照從屬性強弱來選擇建立勞動關系還是合同關系,這樣對于勞動者不但能夠起到保護作用,同時也可以促進新興行業的發展和穩定。
4 結語
總而言之,在網絡蓬勃發展的當下,網絡主播與經紀公司之間的糾紛是當下靈活就業中自治性勞動的縮影。本文通過探究網絡直播用工關系之間的法律性質,目的就是為了改變我國勞動法單一而固定的模式,彌補非傳統、非典型性勞動關系,規范當下存在的空白,對于新興的行業和工種應當有相關的法律明確用工關系,鼓勵新型行業的發展,為我國經濟穩定發展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 馬瑞霞.互聯網平臺與網約工關系的法學思考[J].法制博覽,2018(33):64-66.
[2] 穆童.網絡直播的無序現狀及其行為規范的研究[J].沈陽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4):494-498.
[3] 譚峰藝,趙冠旭,徐恭平,王啟善.網絡打賞性質及主體間法律關系研究——以斗魚直播平臺為例[J].采寫編,2018(5):172-174.
[4] 潘建青.網絡直播用工關系的勞動法思考[J].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18(4):70-77.
[5] 王全興.“互聯網+”背景下勞動用工形式和勞動關系問題的初步思考[J].中國勞動,2017(8):7-8.
[6] 楊云霞.分享經濟中用工關系的中美法律比較及啟示[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5):147-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