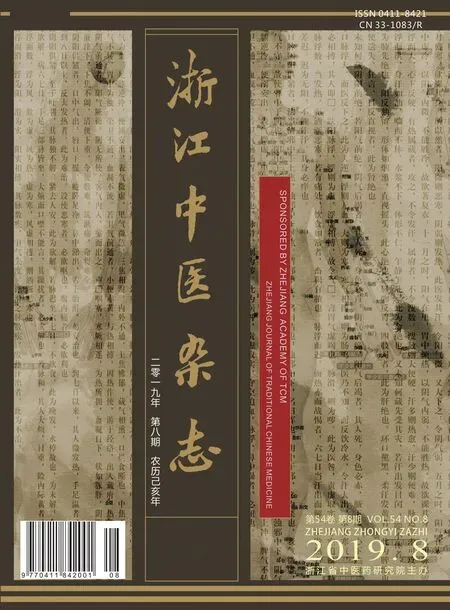民國時期浙籍醫家中醫文獻分類舉要*
焦 陽 凌 天 狄碧云
浙江中醫藥大學 浙江 杭州 310053
民國時期(1912—1949)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中西文化交匯,社會動蕩,內憂外患。因“新文化運動”的廣泛傳播,有關當局奉行“出版自由”的理念,對出版業有一定扶持,雖經歷戰亂,整體而言出版業仍是興旺的,各類民辦、公辦書局、醫家競相出版各類醫書,中醫文獻出版空前繁榮,研究活躍,成果豐碩。發掘和整理這些醫籍,對于民國時期浙派中醫學術研究,繼承和弘揚中醫科學有著寶貴的價值和意義。
1 民國醫籍分類概況
中醫古籍浩如煙海,但因種種原因,大多數已散佚[1]。《中國中醫古籍總目》(2007年)(以下簡稱《古籍總目》)收錄了1949年以前出版的存世中醫圖書書目13455種,為迄今收錄中醫圖書最權威之書目。近代以來著述立說者甚多,其中民國時期(1912—1949)出版中醫藥著作(以《中國中醫古籍總目》為主)約4790種,占到全部中醫存世書籍的35.6%。本研究以《古籍總目》中記載的中醫書目為主要數據來源,并參考《古籍總目》的分類方法,結合近代學科分類法,以民國時期歷史年代劃分,進行歸納梳理。由于原書目中醫家的籍貫并未標注,需要考證,在研究中,參考了《民國時期總書目·醫藥衛生》《中醫人名辭典》《浙江醫籍考》及浙江地方志眾多工具書以及部分學者的研究,對文獻中浙籍醫家、籍貫、著述進行考證、篩選,做到書名、著者、名號、出版年代一致,剔除了原著補正、校注等非原著者、審定者、無法考證者、著者佚名及外籍著者書目,最后結果顯示民國時期浙江籍醫家著作346部,研究內容廣泛,涵蓋了中醫中藥幾乎所有門類;涉及醫家100位,這些醫家有很多懸壺于中西文化交匯與碰撞的上海、江蘇等地或者早年求學于此,其著述基本體現了民國時期江浙地區醫學發展的基本脈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為了方便對比,在制圖時采用了次坐標,如圖1所示。

圖1 民國浙籍醫家醫籍分類概況
由圖1可見,民國浙籍醫家著述豐富,研究內容廣泛,涵蓋了中醫中藥幾乎所有門類,在民國存世醫籍中所占比例為7.2%,其中有關醫案醫話醫論的著作比較多,52部,其次是內科、本草、方書、溫病,都超過了20部。這五個門類也是醫家普遍關注的門類,著述分布集中,在《古籍總目》總共有2001部,占了41.8%。另外,臨證各科類(臨證綜合、溫病、內科、女科、兒科、外科、五官科、針灸推拿、傷科)著作有150部,占比43.4%,相比基礎理論類(基礎理論、醫經、傷寒金匱)著作只有37部。可以看出,臨證醫學各科研究成果豐碩,已成為民國時期中醫學發展的重要特征。本文將嘗試對民國時期出版的浙籍醫家346部醫籍文獻分類整理,參考相關文獻考證和《古籍總目》中館藏部門收藏的醫書版本及文獻數量,遴選出有影響的醫籍文獻目錄,并簡單舉要,分析其特點。
2 中西醫論爭及匯通類著作
2.1 中西醫論爭:自西醫傳入中國后,便開始了中西醫論爭,真正公開與激化的論爭始于1916年余巖的《靈素商兌》,文中直接抨擊了中醫理論,一時間中西醫陣營者紛紛發表論爭性文獻著作,參與論爭的浙派醫家主要有楊則民等[2]。余氏是主張廢止中醫派的代表人物,其曾對近代醫學知識傳播、近代醫學教育有一定貢獻,但其廢醫存藥的錯誤觀點,給民國時期中醫藥的發展帶來消極的影響。對余氏觀點和言論反擊者多達百余家,其中最有力者當屬楊則民,其《內經的哲學檢討》一文,運用唯物辯證法思想研究中醫內經,注重與自然科學內容融匯貫通,對中西醫論爭和中醫未來等重大問題做了精辟的分析,駁斥了廢止中醫派的各種錯誤觀點。
2.2 中西醫匯通:中西醫匯通思想也是近代中國醫學出現的重要特征,是中醫受西方醫學影響而出現的融合。早期醫家通過對中西醫比較研究之后,逐漸出現了中西醫匯通思想和學派,開啟了中西醫匯通的學術研究和實踐,這其中有中西醫匯通代表人物祝味菊,提出匯通要立足中醫,借鑒西醫,主張用西醫知識來解釋中醫理論的嘗試,力圖達到中西醫匯通,如祝味菊在《傷寒新義》(1931年)中即用西醫知識來解釋病證、用藥機理、組方原則,還有王慎軒的《中醫新論匯編》(1932年),潘澄濂的《傷寒論新解》(1936年),皆是如此。主張中西醫匯通的還有劉受祖、張若霞、陳滋、朱國鈞、楊則民等人,有關于中西醫比較研究的,如劉受祖的《醫庸新語》(1935年)中比較一些常見病的中西醫病癥異同;有主張中西醫取長補短,各取所需的匯通著作,如張若霞的《通俗內科學》(1916年)和陳滋所著的《中西眼科匯通》(1932年),兩書均先以西醫闡明癥狀,后介紹古方。另外,朱國鈞在《國醫生理新論》(1934年)中以《內經》為宗,論經絡、臟腑、氣血、津液等生理功能,并融入西醫理論,寫成一部中西合璧的生理學專著[3]。總體來看,這些醫家中西醫匯通的思想和實踐,存在“廢醫存藥”之嫌,但其中也有很多值得肯定、借鑒之處,其著作同樣是浙派醫家醫籍的重要組成部分。
3 臨證各科類著作
根據《古籍總目》的分類,民國時期浙籍醫家所撰寫的臨證醫著,有臨證綜合、內科、溫病、女科、兒科、外科、五官、傷科、針灸推拿類,研究內容廣泛,幾乎涵蓋了臨證所有門類,存世醫籍150部,也是最多的,占浙籍醫家醫籍總量的43%。在此類中,名醫朱振聲和曹炳章撰寫了大量的臨證醫著,一共有57部之多。朱氏早年師從滬上名醫丁濟萬,主編多家醫報,著作甚多,涵蓋臨證綜合、內科、外科、女科、五官科,內容多為中醫藥類科普著作,如《家庭醫藥常識》(1929年)、《百病治療大全》(1931年)、《百病自療叢書》(1931年)等35部,為中醫藥普及傳播,做了大量工作。曹氏是“紹派傷寒”代表人物之一,重視對于中藥的研究與應用,著作涵蓋內科、溫病、外科、五官科,臨證代表作有《喉痧證治要略》(1917年)、《秋瘟證治要略》(1918年)等。臨證各科中有對前人臨證醫學實踐的總結,同時還注重借鑒西醫之法。如內科方面葉橘泉的《近世內科國藥處方》(1935年),對內科病癥以西醫之法進行分類,中醫之法治療,載方856首;兒科方面有名醫何廉臣的《兒科診斷學》(1918年),該書針對兒科診斷特點,參酌西醫診療辦法,擴四診為六診[3];也有本人親自臨證心得的體會,如女科方面比較著名的有嚴鴻志的《退思廬醫書四種合刻》叢書(1921年),其中輯有三部女科著作;針灸推拿方面有張俊義的《針灸醫學大綱》(1939年),收錄論文9篇,流傳較廣[4]。
4 方藥類著作
4.1 方書類:《古籍總目》中收錄民國時期浙籍醫家方書類著作26部。該類著作主要是醫家本人或他人的單方、驗方、秘方的整理與編纂,但重點不再是對古代方劑的理論研究,而在于“古為今用”上,內容以實用性為主。比較有代表的是吳克潛編的《古今醫方集成》(1936年),吳氏對上古至近代的方書170部,進行系統整理編成書,收錄醫方萬余種,并進行增補說明。另外書中還保存了160部已佚方書的部分內容[2]。另外還有名醫沈仲圭的《中醫經驗處方集》(1944年),記載了沈氏運用經方和對古方靈活加減運用的體會。還有沈煥章的《臨癥處方學》(1933年),列方258首,編成歌訣,以便于初學者誦讀,簡單實用[5]。
4.2 本草類:《古籍總目》中收錄民國時期浙籍醫家所著本草類著作34部。內容上看,除了一般中藥研究著作以外,有介紹藥性的著作,吳克潛編的《藥性辭典》(1922年),錄藥物六百種;有作為當時的中醫學校教材,如何廉臣的《實驗藥物學》(1924年)是當時浙江中醫專門學校的教材之一;有關注食療的著作,如程國樹的《疾病飲食指南》(1938年),還有單味藥研究的著作,如張拯滋的《貝母之研究》(1934年)。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曹炳章的《增訂偽藥條辨》(1901年),該書是一部藥物鑒別真偽的著作,由曹氏在前人著作基礎上,將藥物分類,逐條集注,重訂成四卷,增補編寫的集大成的醫籍[6]。再就是張拯滋的《草藥新篡》(1932年),張氏對草藥頗有研究,書中所收錄的草藥皆經過實地考察,臨床驗證,保證準確無誤[7]。
5 中醫規模化教育教材著作
民國時期的“漏列中醫藥案”和“中醫廢止案”兩次事件的影響,中醫發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在中醫界的積極抗爭之下,開啟了近代中醫民間辦學之路。浙江作為近代民辦中醫教育的主要發源地之一,創辦了許多新式中醫學校,如民國時期建立的“浙江中醫專門學校”“蘭溪中醫專門學校”“杭州中國醫學函授社”,培養了大批中醫人才[3]。雖然當時倡導全國統一編寫中醫教材教學,但實際上仍以各校自編教材為主,學校創辦者及任課教師編寫了大量教材著作,這些教材內容全面,涵蓋中西醫各科知識,體現了中西醫匯通的思想,如“浙江中醫專門學校”首任校長傅崇黻所編教材《外科要旨講義》(1938年)、《嬾園醫話》(1921年)等,杜士璋也為該校編寫了許多教材,如《病理學講義》(1933年)、《藥物學講義》(1919年)等,還有馬湯楹的《雜病學講義》(1938年)、《診斷學講義》(1938年)、《處方學講義》(1938年),與其他各科課程一起,后來編成《浙江中醫專校講義三十三種》叢書,叢書中涵蓋中西醫基礎知識、中醫臨證各科、方藥類、診法以及中醫名著選讀等著作。另外該校還輯有《浙江中醫專校講義八種》。函授教育方面,當時“杭州中國醫學函授社”是我國較早從事中醫函授教育的教育機構,在當時圖書資料極端匱乏的情況下,創辦人何任自編教材《實用中醫學》(1947年),該書是一套由淺入深的具有現代概念的函授教材,影響深遠。所有這些教材著作凝聚了浙籍中醫教育界人士的拳拳之心,為中醫學術傳承做出巨大貢獻。
6 中醫基礎理論與醫經研究著作
6.1 中醫基礎理論及診法:近代以來,由于西醫的傳入,影響了中醫固有的基礎理論體系。中醫學發展過程中,融合了部分西醫知識,產生一些新概念,如生理、病理、解剖、診斷等術語,出現了一些包含這些術語的著作。《古籍總目》中民國時期浙籍醫家關于中醫基礎理論的研究有11部,內容涵蓋理論綜合、生理與病理、病因學說、運氣學說等內容。在理論綜合方面有葉勁秋的《中醫基礎學》(1933年),葉氏懸壺滬上,對中醫基礎理論、時證方面頗有研究,該書采用西醫診療步驟,從生理、病理、診斷、治療四部分,闡述中醫理論[8]。運氣學方面有傅崇黻編寫的《運氣學講義》(1938年)教材。有關病因學說的有吳克潛所撰的工具書《病源辭典》(1936年),收錄各種病名4000余條,按病名排序,為古今成方;另外還出現了以“病理”命名的書籍,如祝味菊的中西醫匯通之作《病理發揮》(1931年)等。民國時期有關中醫四診的研究已經趨于成熟,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曹炳章的《(彩圖)辨舌指南》(1916年),該書內容豐富,圖文并茂,中西并舉,參己以驗,是曹氏對一些舌診文獻的保存、整理和發揮,是一部具有較大影響的舌診專著[9]。
6.2 中醫經典著作研究:《古籍總目》中民國時期浙籍醫家中醫經典著作的研究中,醫經類的研究有13部,傷寒金匱類的研究有17部。近代中西醫論爭激烈,民國時期的醫經研究不再側重于經典考證、校勘,重點變為闡明其學術價值,旨在捍衛中醫理論體系。如楊則民的《內經講義》(1925年)與余巖的《靈素商兌》(1916年)即是內經領域中西醫論爭的正反兩派。另外為了適應中醫教育需要,還有一些著作是基于傳統內經研究的節錄精要和注釋講解,如傅崇黻編的《眾難學講義》(1921年),該書作為浙江中醫專校講義,參考了眾多醫家闡注精要而成。民國時期對《傷寒論》的研究,也有沿襲古代條文考證之作,如周歧隱的《傷寒汲古》,而多數著作則結合西醫知識加以闡述,注重臨床應用,力圖闡述《傷寒論》之新義。葉勁秋在《傷寒論啟秘》中認為在中西醫論爭之時,對《傷寒論》的研究應該有正確的態度和方法;近代醫家祝味菊對《傷寒論》研究具有獨到見解,祝氏首提“八綱”,重釋六經,《傷寒新義》(1931年)、《傷寒方解》為其代表著作[6]。另外,還有陳無咎的《傷寒論蛻》(1925年),亦是以個人臨床體會來闡述《傷寒論》的佳作。
7 醫案醫話類著作
民國時期的醫家的醫案、醫話圖書,注重中醫臨床經驗積累,具有很高的價值,也是當時的醫家與“廢止中醫”政策作斗爭的有力武器。據《古籍總目》記載,民國時期浙籍醫家著有醫案醫話類著作豐富,其中醫案20部,醫話類著作32部,包括臨證心得、讀書體會、雜論等。這些醫案有收集前人有效案例的,其中大多數是醫家自己的臨證案例,為后人繼承其學術思想的第一手資料,是近代醫學發展的重要特點之一。醫案方面比較著名的屬何廉臣的《全國名醫驗案類編》,匯集了全國80余醫家,300多案例,按照固定的程式記錄病案,并附個人看法和自己的臨證心得。該書反映了近代中醫的臨床水平,在當時影響很大[5]。另外還有葉勁秋的《現代名醫驗案》(1930年)。其中個人醫案有陳無咎的《黃溪大案》(1926年)等。醫論醫話類著作,比較著名的是曹炳章的《(增訂)醫醫病書》(1915年)、陳無咎的《中國醫學通論》(1923年)、許勉齋的《勉齋醫話》(1937年)。在《(增訂)醫醫病書》(1915年)中曹氏對吳鞠通的《醫醫病書》進行整理,依其先后,分上下兩卷,增加5篇,一共81篇,并加按語,闡吳氏之意,去其紕漏。陳氏的論著是其為入丹溪學社學生講授的通論課程,該書以西方科學的視角來闡述中國醫學之本體、派別、定義、范圍及其它諸多問題,簡明扼要[10]。
8 綜合性工具書及醫史類著作
民國時期大量的中醫藥綜合性叢書匯編類著作、工具書、醫史文獻等的出版,其中有出版社組織的,也有個人發起的。在《古籍總目》中,浙籍醫家編纂叢書匯編類書籍16部,書目類工具書7部,醫史類著作12部。叢書的出現使得大量的醫書得以保存和廣泛流傳,影響深遠。叢書匯編類著作中貢獻最大的當屬裘吉生、曹炳章,二人一生整理出版了大量中醫文獻,而且在版本、內容方面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和實用價值,如裘吉生的《三三醫書》(1923年),分三輯,收錄99種醫書,保存大量江浙一帶的名醫方論,內容涉及醫學理論、臨證各科、針灸、方書、醫案、醫話等。其中有些書籍已是孤版,價值很高。裘氏還輯錄了《珍本醫書集成》(1936年),醫書90種。除此之外,曹炳章的《中國醫學大成》(1936年)收錄醫書128種,收集了歷代具有代表性的書籍。為方便醫家閱讀這些大部頭工具書,裘氏為其叢書編了《三三醫書書目提要》《珍本醫書集成總目》兩部目錄,曹氏亦編有《中國醫學大成總目提要》,介紹了所錄醫書的基本內容[2]。另外,醫史類著作著名的是范行準的《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1942年),該書是《醫學史叢書》之一,歷經8年始成,被譽為研究中西醫學與科技交流史的典范之作[5]。綜合性史學工具書類著作為現代研究近代醫學發展提供珍貴史料和寶貴經驗。
9 總結
民國時期浙籍醫家的重要醫籍,雖不及以前,但也數量眾多,精品迭出,呈現出新的特點和趨勢:首先,醫家們創新中醫理論,發揚中醫“辨證論治”之精髓,吸收部分西醫觀點,所著醫書注重對經典的現代詮釋和發揮,倡導中西醫匯通,與西醫知識的結合更加緊密。醫書出版類型趨于多樣化,出版了很多中西醫論爭及匯通類著作、大部頭的醫學工具書及中醫規模化教育教材著作等;其次,有關中醫臨證醫學的著作成為民國中醫文獻的核心內容,文獻中體現了“古為今用”的思路,注重臨床實踐,以證中醫之科學有效;最后,在“新文化運動”推動下,民國出版醫書文獻多采用白話文體記載,較之前世古書,內容更易于理解,推動了中醫薪傳。總之,民國時期浙籍醫家醫籍書目研究,對于現代中醫藥學術及中醫教育的發展無疑有著積極的啟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