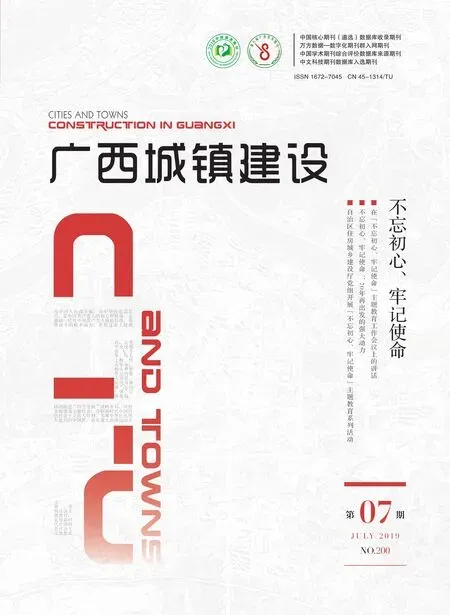枕水烏鎮:夜聽夢里搖櫓聲
文/圖 蒙涓(本刊特約記者)

行走在烏鎮街狹窄巷弄里,仰頭是粉墻青瓦的馬頭墻,叩著青石板路,密密麻麻地記錄成長的腳步與過去的光影。

人家的后門外就是河,站在后門口(那就是水閣的門)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夢回,可以聽得櫓聲欸乃,飄然而過……—— 茅盾《大地山河》
烏鎮,這座位于浙江嘉興桐鄉,有著7000多年文明史和1300年建鎮史的江南古鎮,因水而流動,與水相生相融。水,萬物之源的水,生長萬物的水,成就了烏鎮,承載了烏鎮內外的交會故事……
隸屬于太湖流域沖積平原的烏鎮,湖沼水系眾多。有著南北大動脈之稱的京杭大運河,從它的西側流過。古鎮以河為街,以岸作市,臨水構屋,被流水分隔,卻又與水相傍。十字形的內河水系將全鎮劃分為“東柵、南柵、西柵、北柵”,烏篷船搖櫓穿水而過,一眼相望,便勾勒出“人家盡枕河”的畫卷。
烏鎮人借助水運,從宋代起逐漸發展成為江南的貿易重鎮,積累了大量財富的當地人選擇臨水構屋。沿河的條石街道劃分為“上岸房子”和“下岸房子”。上岸房子多為深宅大院,臨街的只有兩三間門面,縱深的卻有四、五、六進。行走在烏鎮街狹窄巷弄里,仰頭是粉墻青瓦的馬頭墻,叩著青石板路,密密麻麻地記錄成長的腳步與過去的光影。出生于烏鎮的文學巨匠——茅盾先生,對烏鎮獨特的建筑形式——水閣,情有獨鐘。他在《大地山河》一文中這樣描述故鄉的水閣:“人家的后門外就是河,站在后門口(那就是水閣的門)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夢回,可以聽得櫓聲欸乃,飄然而過……”古鎮下岸沿河的民居,居室的一半延伸至河面,下面用樁木或石柱打入河床中,上架橫梁,鋪上木板,打開屋中的蓋板,便可汲水洗滌。屋內三面均有木格子窗,窗格精雕細刻,飾有紗窗、蠣殼窗和玻璃窗等。憑窗覽市,既能觀河風光,也方便臨河的居民吆喝購買搖船上的蔬果、家畜等新鮮食材。小小水閣,在讓烏鎮人過著熱氣騰騰生活的同時,還為其提供閑情逸致的場所。

古鎮下岸沿河的民居,居室的一半延伸至河面,下面用樁木或石柱打入河床中,上架橫梁,鋪上木板,打開屋中的蓋板,便可汲水洗滌。
精巧別致的建筑與河道上的波光相映。遠眺是遇水而搭、風格各異的各式橋梁。鼎盛時期,烏鎮橋梁最多達到150座。后因風雨侵蝕、城鎮改建,有的古橋早已消失。但現今烏鎮仍存有數量可觀的古橋,僅西柵就有72座古橋。烏鎮的古橋多為石橋,有簡便的石平橋、古樸的石拱橋、精巧的磚石橋等。搖櫓的烏篷船穿橋過岸,水聲不絕。小橋、流水、人家……如此這般的詩畫美景,亦種下了烏鎮人思鄉的病根。烏鎮東柵東大街的一頭住的是茅盾,而另一頭則住著后來在海外漂泊半生的木心。
“從前的日色變得慢
車,馬,郵件都慢
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從前慢》木心
一首《從前慢》,是木心先生筆下的少年時光,亦是曾經的烏鎮最好的寫照。以少年姿態離開烏鎮的木心,從烏鎮到杭州到上海,再到紐約,輾轉經年,于1994年回到了家鄉。久違的孫家花園,廳堂破敗;故鄉那最熟識的地方,卻已經模糊。“地名,對的;方言,沒變,而此外,一無是處……永別了,我不會再來。”幸而烏鎮有陳向宏,東柵、西柵、烏村,他遵照“修舊如舊”的原則,從鄰近鄉里收集舊料,對烏鎮日復一日地精心保護與開發。陳向宏托人轉告木心:“他的故鄉在找他。”2006年,已經79歲高齡的木心回來了。在烏鎮昔日的孫家花園——晚晴小筑(木心紀念館),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后五年。木心走后,留下了一座美術館(木心美術館)。全館坐北朝南,一只盒子連著一只盒子,跨越烏鎮元寶湖水面,與水中倒影相伴隨。一生追逐美、挑剔美的木心,在見到美術館草圖時,曾說:“風啊,水啊,一頂橋”,為木心美術館做了最為詩意的描述。這道烏鎮西柵寧靜而美麗的風景線,應該就是木心生前期待的那個樣子了。

_ 木心美術館

不一樣的烏鎮,傳統與現代融合。無論時代如何變幻,留在人們心中的,是茅盾先生筆下那夜聽夢里搖櫓聲的烏鎮;是木心記憶中那慢而深情的小鎮時光,是『這里剛剛落呀,烏鎮是雪白雪白了』的感嘆。
不僅木心美術館建成了木心想要的樣子,原本沒落頹廢,河道臭氣熏天、雜草叢生的烏鎮,在陳向宏的畫筆下,重塑美麗容顏。拆掉與古鎮風貌不符的房屋,用舊料恢復故居,修舊如舊;重新整理水系,疏通填掉的河道……死過一輪的烏鎮,又活了過來。烏鎮重新成為文人墨客向往的夢中天堂。烏鎮戲劇節為古鎮賦予了新的文藝氣息;世界互聯網大會落戶在此,則讓烏鎮成為世界名片。
不一樣的烏鎮,傳統與現代融合。無論時代如何變幻,留在人們心中的,是茅盾先生筆下那夜聽夢里搖櫓聲的烏鎮;是木心記憶中那慢而深情的小鎮時光,是“這里剛剛落呀,烏鎮是雪白雪白了”的感嘆。穿水而過,烏篷船搖櫓,在靜謐中回味沉淀的歲月,感受似水年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