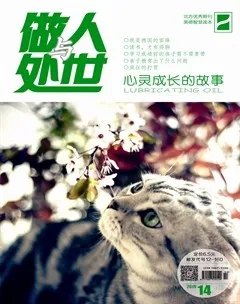巴黎圣母院大火中的劈啪聲
黃鶴權(quán)
著名的巴黎圣母院突遭大火,《人民日報》發(fā)文表示:“塔尖倒塌的那一刻,太心痛了!”然而,在大火尚未撲滅之際,國內(nèi)大量不堪的評論和聲音就蜂擁而來,有的以百年前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做對比,稱這次文明之殤是圓明園的輪回,叫囂“燒得好”,對這場災(zāi)難拍手稱快;有的覺得因西方文明被毀而難過的人在瞎操心,炫耀著自己的輕率和無知。原來,靈魂的墮落是比火災(zāi)更悲傷的事。
雖然這場災(zāi)難過后,兩座被視為巴黎圣母院門面的鐘樓依然佇立,圣母院的大部分主體結(jié)構(gòu)幸免于難,就連圣母院內(nèi)最重要的文物——耶穌受難荊棘冠也被搶救下來,并沒有讓人感覺到最為深刻的絕望,只有辭別之意。
惻隱之心人人有之,文化的魅力不分國界。巴黎圣母院對全人類而言,是雨果筆下的“石頭交響樂”,是真善美的化身,是共同的文化財富與瑰寶。這里有過繽紛的多彩和絢爛,有最丑陋的敲鐘人卡西莫多,教我們光明磊落地去愛。它也曾被多樣的表達(dá),出現(xiàn)在數(shù)不清的書籍、詩歌和電影里。它與圓明園被燒毀的可惜是一樣的。這是法國的損失、藝術(shù)界的損失,也是每個人的損失。
其實(shí),在這件事中難過不難過都是一種選擇,我們都該尊重選擇。但拿圓明園說事就愚蠢了。圓明園遺跡的存在是“為了讓所有人記住懦弱的代價,不是讓我們在今天面對這顆藍(lán)色星球每一寸誕生不易的人類文明瑰寶消逝時發(fā)出冷嘲熱諷”。燒圓明園的人不是建巴黎圣母院的人,他們之間整整隔了700年。1163年的法國封建割據(jù),根本不是現(xiàn)代意義的法國。冤有頭債有主,憑什么要讓巴黎圣母院承擔(dān)火燒圓明園的責(zé)任?
那些叫囂“燒得好”,談著天道輪回,暗中幸災(zāi)樂禍的人,局限在一室之內(nèi),毫無共情能力。在他們眼中,那些被毀壞的屈指可數(shù)的倒塌建筑本身就是死物,與隨處可見的水泥墻沒有什么不同,更談不上歷史與文化。這種行為,就跟美國發(fā)生911飛機(jī)撞樓、日本發(fā)生大地震的時候,鍵盤俠們奔走相告彈冠相慶是一個性質(zhì),太惡劣了,如此愚昧的“愛國”雙重標(biāo)準(zhǔn)正是阻擋在文明長河中的絆腳石。
如果我們現(xiàn)在還抱著活該的心態(tài)看那些被毀壞的瑰寶,那我們和當(dāng)年那些可恥的侵略者有什么區(qū)別?在歷史上,有罪的一直是人,不是建筑,不是藝術(shù)和文化。所以,與其尖酸刻薄,打著歷史的幌子和愛國主義旗號發(fā)泄私憤,不如銘記歷史,珍視文明,拒絕野蠻。不如把這份感性的仇恨轉(zhuǎn)移到平日的購物行為中,堅決支持國貨。這才是正解,才是國人對自強(qiáng)和愛國的共識。
“正如當(dāng)時譴責(zé)燒圓明園的那個雨果,也正是熱愛著巴黎圣母院的那個雨果。”仇恨不會讓這個世界更美好。美與缺憾總是如影隨形,但正因?yàn)槿焙叮覀兤诖蟮拿篮谩R环矫妫@個時代的體溫,不應(yīng)該是百年前的冷血與敵視。歷史建筑是文化符號的重要一部分,所有美麗的藝術(shù)品都應(yīng)該得到珍惜和尊重,不該承載國家和戰(zhàn)爭的重量。
巴黎是座可愛的城市,巴黎圣母院是她的一只眼睛。我相信,時間會是最好的建筑師。智慧的法國人一定能夠完美修復(fù)、重建巴黎圣母院,讓人們再次在憂郁的云彩下仰望鐘樓、玫瑰花窗、怪獸石像,感受到小舞臺上唱詩班唱出的空靈歌聲,然后再從圣母院緩緩踱步到左岸去。盼望那一天早日到來。
另一方面,“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優(yōu)秀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需要傳承人和守護(hù)者,而這傳承人和守護(hù)者不僅僅是法國人,而是地球人。除了緬懷以外,其實(shí)此刻值得我們深思的不是歷史也不是文明,是抓住眼前,是馬上行動起來去看看世界的美好。余生很短,別遲疑,別猶豫,把握每一次日出和黎明,見想見的人,做想做的事,讓生活愛得劈啪作響。
(編輯/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