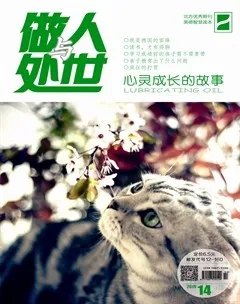比爾·蓋茨怎么花錢
比爾·蓋茨,大家都知道他把很多財富捐了出來做慈善。我2015年加入了蓋茨基金會,做北京代表處的工作。
我有3個孩子,老大8歲了,他也知道比爾?蓋茨是首富,他也大概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說:“媽媽,我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我說:“是什么呀?”他說:“你每天都在辦公室包錢,然后寄錢。”我說:“那寄給誰呢?”他說:“寄給非洲的小孩。”這算是一種理解。我曾經在麥肯錫,那兒的同事跟我講,你現在太幸福了。我說:“為什么?”他說:“你看,以前我們在公司每天掙錢多辛苦啊,你現在每天花錢,每天辦公室門口肯定是很多人等著你,你看哪個順眼就給一點。”我腦補了一下這個畫面,的確比較幸福。這是第二個版本。第三種理解是,世界上有錢人沒一個好人,做慈善全是煙幕彈,肯定是避稅。
既然大家有這么多猜測和理解,那我就跟大家講一講比爾·蓋茨到底是怎么花錢的。
先來看一個數字,12000000。這是2000年,全世界5歲以下兒童死亡的數字。但是大家可能也沒有概念這到底有多大。我給大家做一個類比,世界上客運量最大的客機是空客A380,坐滿了有550個人,如果今天有一個新聞說有一架滿載著兒童的A380失事了,上面的乘客全部死亡,肯定會是驚天大新聞。 那這1200萬如果對應成每一天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世界上每一天有60起這樣的事故。而且更讓人心寒的是,其實這1200萬孩子里面,有2/3的死亡是可預防的,就是他們不是得了絕癥或者活不下去。這個預防靠什么呢?答案是靠疫苗。
在2000年,全世界有3000萬的孩子打不到疫苗。為什么打不到疫苗呢?首先看需方。這3000萬孩子在哪兒?他們分布在80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一方面他們財力有限,另一方面他們整個的疫苗體系非常破敗。而且疫苗有個特殊的問題,就是它需要冷鏈,必須儲存在2到8度之間才能保持活性。大家看到這個圖,南美洲的2個衛生員,在騎著馬跋山涉水去送疫苗、打疫苗。這里面就是一個隔熱箱。我訪談過一個一線工作人員,他當時指著山說:“你看,我翻過這座山要一天一夜,村子里面有3個孩子需要打疫苗,如果我今天偷懶了,不想翻這個山了,把疫苗往旁邊河溝里一倒,沒有人知道,這無非是一個良心的問題。”所以從需方來說,雖然很多孩子需要,但是很難找到他們,很難把疫苗打到他們身上。再看供方。實際上這些疫苗大部分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你是疫苗企業的總經理,你要把疫苗賣到這80個國家去,它們貧窮、落后、市場分散,沒有經銷體系。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寧愿不掙這個錢。而且就算是有人愿意賣,有人能買,這中間還有一個巨大的鴻溝,錢從哪里來?誰要去花錢買這些疫苗去送給這些國家呢?所以這就造成了我們當時在2000年的時候面臨的巨大的困境。 這個數字也是蓋茨成立基金會的時候看到的數字,所以他當時成立的時候做了第一筆捐贈,成立了這樣一個組織,叫GAVI,全球疫苗免疫聯盟。
其實在2000年之前,全世界范圍里對疫苗相關的捐贈也有,大概是幾百萬美元的樣子,所以當時GAVI成立的時候,有很多從事公共衛生的人員特別興奮,你們看世界首富要捐錢了,能捐多少呢?有人說能捐5千萬。結果當時第一筆捐贈:7億5千萬美元。所以當時公共衛生界喜大普奔。現在回頭看當年那筆捐贈,確實改變了整個全球健康的面貌。
蓋茨做了什么事情呢?其實就是解決剛才我們提到的幾個問題。首先他去跟供方談,他說我知道賣到這80個國家你們不樂意,那這樣,你就賣給我一家,但我有個要求,價格要低,但是高于你的成本價。這對于企業來講是可以的,所以就欣然答應。因此他們有特別強大的議價能力,比方說,如果在座的有當父母的話,都知道五聯苗,五聯苗在私營市場上,大概是100美元的價格,GAVI能夠拿到它的采購價,不到1美元。然后又去找需方說,你們這80個國家得組織起來放在一起。通過跟聯合國、跟世界衛生組織溝通,把它們分了3類:如果你最窮,那我就一分錢不要免費送給你疫苗;中間窮的,就用半價來買疫苗;如果是這里面最上面的國家,那你就用采購價全價來買疫苗,所以就有一個采購體系。
剛才我講到中國乙肝在2000年之后,西部的14個省份是得益于GAVI的捐贈的,我們是用采購價買的乙肝疫苗。后來也成了一段佳話,就是因為我們乙肝防疫做得很好,我們的國力也增加了,我們就從第三梯隊畢業了。所以到2015年的時候,咱們中國又給GAVI捐贈了一筆錢,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循環。
剛才還提到冷鏈問題,它很麻煩。要是在城市里面,有冰箱、有電,很容易解決,但是在農村怎么辦?特別是在非洲沙漠里面怎么辦?所以蓋茨又做了一個捐贈,非常有意思。他在西雅圖成立了Global Good公司,這個公司召集了一幫科學家,去研究這些真實的巨大挑戰。他說你們給我解決這個問題,沒有電,沒有能源,還需要保溫,需要時間長,需要夠大。結果科學家還真有了一個方案,這個方案出來之后他們挺興奮,但是需要有人來生產。當時中國科學家郭自紅,就跑到青島,找到制冷企業澳柯瑪。他就問你們能不能把這個造出來,當時工人一看說,這挺簡單,我們就干這個的。結果后來真做的時候,發現其實非常復雜。長話短說,做了1年,終于把這個東西做出來了。這個東西極其神奇,它能做什么?它能做到在沒有電、沒有任何能源的情況下,就靠物理的隔熱,你只要放上冰,就能讓它的內膽保持在10攝氏度以下,并且長達35天。
還有剛才我講的大鴻溝,誰出錢啊?你們說蓋茨出錢,的確,出了7億5千萬美元。但是大家想一想,這是80多個國家啊,個人再有錢對這個需求來講也是海洋里的一滴水,所以蓋茨經常出現的一個形象是這樣的:他在各個場合去要錢。大家可能聽起來不可思議,世界首富主要的工作居然是要錢。這幾個事情做成了就差不多了,所以講到GAVI的成績,其實真的是了不起的成績。從2000年成立到2018年,由于GAVI這個組織的存在,全世界有6.4億孩子打上了疫苗,而且根據測算,其中有900萬孩子避免了死亡。
所以大家問怎么花錢,我想總結一下可能就知道了。其實有三個大的方式,第一個就是類似于剛才講的那個冰桶,那個冰桶的名字叫Arktek。就是說我需要一個東西,這個東西不存在,那我就得花錢做研發,然后雇科學家來做這個東西。這大概是基金會每年1/3的投入。
第二類就是剛才講的疫苗。這個產品是存在的,但是它不可及,不可及我們就要想辦法用一個什么樣的平臺去構造聯系,能讓需要的人用上。實際上世界上已經存在這樣的解決方案,這個大概占到了我們1/2的投資。
最后一個方向是大家一般看不懂的,就是剛才蓋茨要錢那張照片,我們叫做“政策倡導”。因為不管你多厲害,你最終其實只是提供了一個示范,做了一種可能的機制,而要想全面地、大規模地解決這些問題,其實大錢還是在國際社會和政府那里。而且更重要的不僅僅是錢,是公共政策的改變。所以這就是他花錢的方法,我們把它叫催化式慈善。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加入基金會有3年了。我記得當時在2015年年初,我收到獵頭的電話,說你對基金會的工作感興趣嗎?我想也沒想就說,不感興趣。為什么?我說要做慈善,要么你有錢,要么你退休。我說我既沒錢,也沒退休,挺年輕的,我干嗎要干這個?后來他們說,理解理解。過了1個月,他們又給我打了一個電話,一諾,我們知道你對這工作不感興趣,你對見見比爾·蓋茨有沒有興趣啊?我說這個興趣還是有的嘛,所以當時我完全是憑著一個獵奇和窺探首富的心態去了西雅圖。我想,既然有這個機會,那我就問問他,你為什么做慈善?雖然大家可能都理解,慈善是個好事,但畢竟當時他微軟做得好好的,而且當時他成立基金會的時候只有45歲——在2000年,他不是個老人,我想知道45歲做這么大的決定是為什么?當時,他說,1997年的時候,他才42歲。我那個時候對世界的理解是這樣的,我覺得這個世界是人人各司其職的:我是微軟的CEO,那我就把我的公司做大,有回報。衛生問題,不是有世界衛生組織嗎?糧食問題,不是有世界糧農組織嗎?打仗,不是有安理會嗎?大家干大家的不挺好的嗎?他說后來我往前一看才發現,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在影響數億人的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巨大的真空。他當時給我舉例子講瘧疾,咱們很多在座的朋友可能不熟悉瘧疾,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還有將近3000萬的瘧疾病人,現在基本上是零了。去年的時候我們國內病例是零,但是它在全世界范圍里面還是一個讓人頭疼的疾病,每年有大概30億人受到干擾,因為它是蚊子傳播的,每年有2億人得病,有50萬人死亡,而且其中70%是孩子。在瘧疾這個領域,你知道全世界唯一對它研發投入是誰嗎?美國軍方。為什么?因為越戰。后來越戰已經不是美國的concern,所以這個研發就沒了,一日之內清零,所以這個真空好大。他當時舉了一個例子,后來我們開始投入瘧疾研發,投入5億美元。大家覺得可能挺多錢的,但是如果我們對比,男性謝頂每年的研發投入多少?20億美元。所以想想,這個世界是不是很可笑?一方面是2億人得病,這真的是病,能死人的病,只有5億美元;而一方面只是你這個不大好看,卻能有20億美元。
有一個比爾·蓋茨的采訪,問了一個聽起來比較雞湯的問題。記者問:“蓋茨先生,你百年之后希望怎么被記住?”他回答:“我希望我的孫子輩對我有美好的記憶,除此之外,沒了。”記者問:“為什么?”他說:“我現在所有致力于做的事情都是在消除這些東西,我希望這些困擾、給我們帶來那么多痛苦和孩子的死亡的病能夠不再存在。什么瘧疾,什么河盲病,什么象腿病等等,大家沒有聽說過的各種熱帶病,是非常可怕的。我希望以后在跟孩子們提到瘧疾的時候,他們會說,什么是瘧疾。如果那樣的話,我的生命就有意義了,所以沒有必要被記住。”
蓋茨有一句話:“敢于冒險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遺忘的群體需要倡導者。”可能跟蓋茨相比,我們每個人的財富都差得很遠,但是我想在這3句話里,可能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可以共同為一個更加美好和公平的世界而努力。
謝謝大家。
(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一諾演講)
(編輯/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