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的防洪效益是無可替代的
谷寶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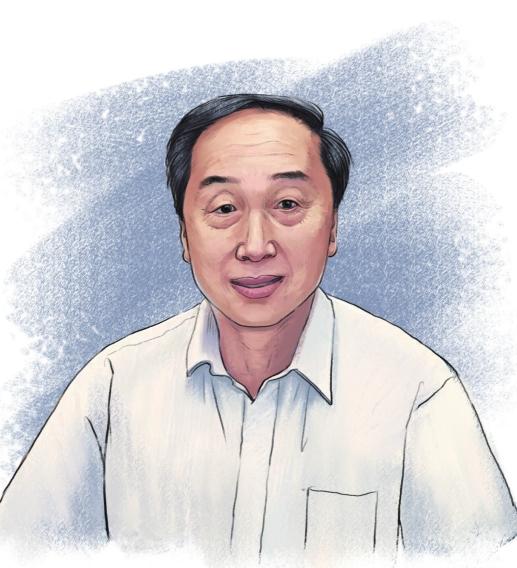
“自宜昌以上……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1919年,孫中山寫成了《實業計劃》一書,首次提出了在長江三峽修建水力發電工程的設想。
在一次演講中,他興奮地說“讓這么大的電力來替我們做工,那便是很大的生產,中國一定是可以變貧為富的。”
100年后的今天,孫中山的設想早已成為現實。
但外界對三峽大壩工程的關心和疑問從未停止,近來有關“三峽大壩變形”的謠言,也惹得輿論一度紛亂。
三峽大壩的功能和實效究竟如何?是否還存在沒有明言的隱憂?
帶著這些社會關心的問題,《南風窗》記者專訪了86歲的陸佑楣院士。他是中國工程院院士、水利電力部原副部長、中國三峽集團首任總經理、中國大壩委員會原主席。
集學者、工程師、管理者、經營者于一身,他的名字已與三峽工程聯系在了一起。
三峽工程的首要任務不會變
南風窗:三峽工程的首要任務是防洪。但有人認為,三峽是為發電而建的,修建三峽的人是看重它的發電功能和經濟利益。
陸佑楣:三峽同時存在多方面的效益,防洪、發電、航運,乃至促進當地旅游業發展等等,但最關鍵的還是防洪。
之所以講防洪效益最關鍵,是因為它是最無可替代的,發電可以有火電、核電,但221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什么其他措施能攔蓄這么多的水量呢?
洪水的本質是人和水爭奪陸地面積,人要有空間來生存和生產,水要空間來容納自身,這就會起沖突。
一種辦法是分洪,20世紀50年代修建了荊江分洪區,相當于洪水來臨時犧牲一些農田來保護武漢等大城市的安全,但每啟用一次就要把40萬百姓安置在面積不到20平方公里的安全區內,一平方公里2萬多人,這是多么擁擠的生存空間!而且分洪一次也必將惡化環境、毀壞作物、誘發多種疫情,這是多么大的人間災難!
另一種辦法就是把上千里長的荊江大堤再加高加固,但顯然經濟上代價更大,技術上也很困難,當時論證認為并不合理,所以只能靠水庫來容納。從三峽工程建成多年來的運行效果看,它能控制荊江河段洪水來量的95%以上,控制武漢以上洪水來量的2/3左右。
截至2018年底,累計攔洪運用47次,總蓄洪量1440億立方米,有效攔蓄了上游洪水,干流堤防沒有發生一處重大險情,這些數據足以證明三峽的防洪效益是無可替代的。
還要特別強調一點,三峽發電的效益也不能簡單說成是“經濟利益”,水電本身不消耗水、不污染水,同相同數量的火電相比,大大減少了溫室氣體排放。
三峽電站歷年累計發電量相當于替代燃燒原煤5.9億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1.8億噸、二氧化硫排放1180萬噸、氮氧化合物排放437萬噸,對減小氣候變化壓力作出了很大貢獻,所以它的發電功能也有生態效益的內容。
南風窗:當年孫中山提出設想時似乎更看重發電和航運效益,而不是防洪。
陸佑楣:孫中山確實是考慮要發電、要改善航運,后來國民黨在重慶時請美國專家薩凡奇去實地考察過,國民黨是希望用三峽的電力生產化肥,用利潤來償還美國的借款。
把防洪任務放在首位的是中國共產黨。剛建國那幾年,長江連年發大水,我當時在南京的河海大學(當時叫華東水利學院)讀書,師生們下課也要到大堤上扛沙袋,防止江堤決口。
1954年那場大洪水奪去了3萬多人的生命,1800多萬人受災,320萬公頃耕地受淹。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的想法,之后歷屆領導人繼承了這樣的理念,并把它變成了現實。
今后三峽的任務還是把防洪放在首位,這不會變,也不能變。
爭議的問題中有些客觀存在,有些則違背科學常識
南風窗:有網友收集了報道三峽的新聞題目,先說“三峽可以抵抗萬年一遇的洪水”,后來又說是“千年一遇”“百年一遇”,仿佛三峽的防洪能力變來變去,三峽的防洪能力下降了。
陸佑楣:之所以有這種報道上的混亂,主要是因為水利專業術語,如果用日常語言描述,就會太籠統,出現概念混淆。關于三峽工程“百年一遇、千年一遇、萬年一遇”的描述分為兩個維度,一個維度是三峽工程的防洪功能,即“救人”的能力,另一個維度是三峽工程自身的防洪能力,即“自助”的能力。
第一個維度防洪功能,即指的是三峽工程保證下游防洪安全的防洪控制能力,即幫助下游防洪的能力。當遇到不大于“百年一遇”(洪峰流量超過 83700m3/s)的洪水,三峽工程可控制枝城站最大流量不超過每秒56700m3/ s,不啟用分洪工程,沙市水位可不超過44.5米,荊江河段可安全行洪。這也就是常說的“三峽工程的建成,使荊江河段的防洪能力從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當遇到“千年一遇”(洪峰流量超過98800m3/s)的洪水,經三峽水庫調蓄,通過枝城的相應流量不超過每秒80000m3/s,配合荊江分洪工程和其他分蓄洪措施的運用,可控制沙市水位不超過45米,從而可避免荊江南北兩岸的洞庭湖平原和江漢平原地區發生毀滅性災難。
之所以講防洪效益最關鍵,是因為它是最無可替代的,發電可以有火電、核電,但221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什么其他措施能攔蓄這么多的水量呢?
第二個維度防洪能力,則是對于三峽大壩本體而言。三峽大壩建設的防洪標準是按照“千年一遇”設計、“萬年一遇”加10%校核,即當峰值為98800m3/s的“千年一遇”洪水來臨時,三峽大壩本身仍能正常運行,大壩各項工程、設施不受影響,可以照常發電;當遇到峰值流量為113000m3/s的“萬年一遇”洪水再加10%時,三峽大壩主體建筑物不會遭到破壞,三峽大壩仍然是安全的,只是個別功能如發電、通航可能要暫停。
理清以上概念我們就能明白,三峽工程不存在所謂“防洪能力下降”的問題。
但也不要走另一個極端,覺得有了三峽,整個長江流域就高枕無憂了。畢竟洞庭湖、鄱陽湖和漢江都在三峽的下游聯通長江,如果這些支流的上游發生暴雨,還是可能引發洪澇。
所以支流也要建立自己的防洪體系—堤防、水庫等等,城鄉建筑的防洪標準也要提高,要修得堅固些。三峽是長江防洪體系的關鍵工程,但不是全部。
南風窗:三峽同時具備防洪和發電效益。要防洪,就不宜把水位蓄到太高,以免洪水無處存蓄;要發電,水位越高效益就越大。有媒體報道稱三峽為了提高發電效益,運行的水位比較高,這是否會占用三峽的防洪庫容,降低防洪能力?
陸佑楣:兩種效益的權衡,就要在調度上下功夫,把防洪調度和興利調度結合起來。其中最關鍵的是提高氣象預報的精度,并把它利用好。
如果能夠積累大量的降雨量數據,并用先進技術進行整合分析,通過降雨量來安排調控量,就可以作出相對有利的調度方案。
當然現在三峽的上游有了向家壩、溪洛渡這些水庫,如果天氣預報精度進一步提高,可以在中下游大雨來臨之前,由上游水庫提前向三峽水庫放水,同時三峽也提前向下游放水,以此保證三峽防洪庫容。
南風窗:有人擔心,由于上游來沙量減少,三峽之水太清了,這會加劇下游的河道沖刷,使下游河槽變深,影響下游的河勢。
陸佑楣:關于下游河床深切的問題,要辯證地看。它有一些好處:河道深切之后,水位下降,行洪能力更強;其次,水更深了,對通航有好處;此外,它延緩了洞庭湖萎縮的進程。
根據河流動力學原理,河床在沖刷到一定程度后會達到沖淤平衡,逐漸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不會無限下切。
南風窗:長江中有些島嶼是泥沙堆積形成的,有人說清水沖刷會使這些島嶼的泥沙被沖走,造成地貌變化,即“淘沙”現象。
陸佑楣:上海崇明島就是長江的泥沙堆積而成,三峽蓄水之后改變了江水的泥沙含量,可能對崇明島會產生一些影響,可以采取一些工程措施來加固,成本是可以接受的。
南風窗:還有人擔心,三峽庫區蓄水后,水體流動速度減慢,自凈能力下降,可能導致污染不能及時排出,水體富營養化程度加大,甚至會引發有害藻類蔓延滋長,即“水華”現象。
陸佑楣:水體污染問題的源頭和要害在陸地上,不在工程本身。幾千年來沿江兩岸的百姓都向長江排污,三峽開工以來國家采取了很多的宣傳和控制的措施,如果各種配套措施落到實處,是有可能減少對水體排污的總量的。
關于“水華”的問題,長江每年通過大壩的水量達4500億立方米,而三峽的總庫容僅393億立方米,水庫的水體不斷地更替,平均每年更替十多次,水質富營養化程度是有限的,水華現象是可控的。
對于三峽工程的環境影響,社會公眾關心的比較多,有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但大部分可以采取相應的工程措施加以解決。
當然也有一些就很荒謬了,比如誘發汶川地震、引發大范圍極端天氣現象、還有最近谷歌地圖搞出的“變形事件”,這些就違背科學常識了。
南風窗: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三峽現在成了“航運瓶頸”,是這樣嗎?
陸佑楣:個別媒體緊盯著三峽的一些所謂的問題,拍照片、寫文章,可千百年來荊江兩岸洪水肆虐、百姓遭殃的慘狀,沒有太多影像和文字資料留存下來。如果大處著眼,權衡利害,那么對三峽的很多質疑就會不攻自破。
對于三峽工程的環境影響,社會公眾關心的比較多,有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但大部分可以采取相應的工程措施加以解決。
把三峽說成是“航運瓶頸”,這完全沒有比較三峽工程建設前后航運能力孰大孰小。
原來峽谷里河道窄、水流湍急,還有險灘礁石,好多都是木船在航行,要靠人力來拉纖,即使后來有了汽船,拉纖不常見了,但夜間還是很難航行,噸位也小。
三峽工程建成以后,萬噸級船隊可直達重慶,航道可以24小時通航,船閘通航能力達到 1 億噸,是建壩前的5.6倍。
船舶的擁堵現象恰恰是因為水運成本大大降低,同時重慶的經濟快速發展,有太多船只穿梭于宜昌和重慶之間的結果,怎么能說是三峽工程造成了航運的瓶頸呢?
以人為本,改造自然
南風窗:三峽確實改變了自然本來的樣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
陸佑楣:認為三峽改變了自然,就是違背自然規律,這種觀念把人和自然對立起來,人改變的就是不好的,人不改變就是好的、原生態的。我不贊同!
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自然界也不是亙古不變的,而是不斷被塑造的。三葉蟲、恐龍,都改變了世界的面貌、留下了痕跡,那么人類對于自然界的改造,本身又何嘗不是自然界漫長的演化變遷歷史的一部分?
難道說洪水滔天、一片澤國的景象就是好的,只因為它是“原生態”的面貌?
要尊重人類的發展權利,發揮人類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能力,當然也要注重永續發展,尊重子孫后代的發展權利,這兩者從根本上來說是不矛盾的。
我非常欣賞中國科學院大學李伯聰教授的一句話,他把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改成“我創造故我在”。人不僅是思想活動的主體,也是實踐活動的主體,應當積極改造自然、利用自然。
所以我說,我們也應當從這樣的高度來認識三峽工程、認識中國的水利工程事業。

